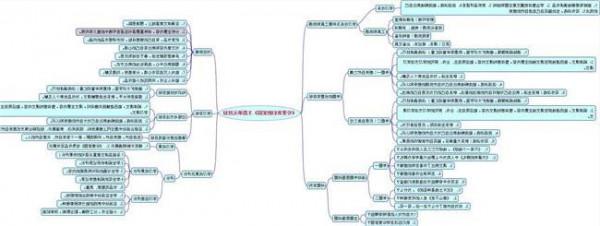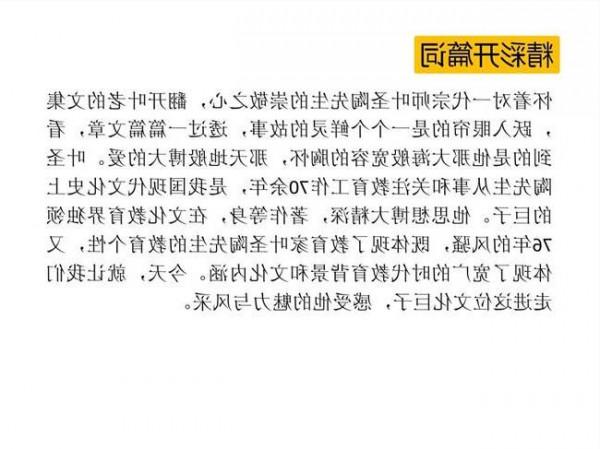冯友兰论风流 冯友兰先生二三事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大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有机会听他讲演,一起开会,有二三事至今印象深刻,难以忘记。
听讲“抽象继承法”
1956年夏天,我提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学习。人大哲学系是新办,我们是第一届本科生。平时除由本校教师授课外,系里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作家给我们作学术讲演。冯友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入学没两个月,在哲学系所在的北京海运仓一座简陋的小礼堂里,冯先生在这里给我们作了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抽象继承法”的讲演。
讲演会由系主任何思敬教授(大家都尊称他为“何老”)主持。何思敬是我国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最早译者,又是延安“新哲学会”的主要人物,后来还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法律顾问”,是一位老资格的哲学家和法学家。

只见他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冯友兰先生来给我们讲演中国哲学。大家知道,冯友兰先生,可说是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老的这后一句话,使在场的人一惊,因为当时冯友兰是公认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怎么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思敬不久就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被免去了系主任职位。

冯友兰先生开讲了,他身材魁梧,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给人印象深的是他留有长长的美髯。大概他也感到何思敬这句话的“问题”,说:“刚才何老的话过誉了,我不敢当。”接着他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哲学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中,有两种意义,一是“抽象意义”,一是“具体意义”。如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具体意义上说,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之类东西,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学这些东西了,不去继承它;但从抽象意义说,孔子这句话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经常温习和实习,这样看,这个命题就是对的,可以继承。
冯友兰还举了大量的古代圣贤先哲的话和命题,来论证他的这一“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讲演时没有讲稿,他带有河南口音的话语娓娓道来,讲得通俗易懂(后来看冯先生文章多了,知道这是他的文字的一大特点,能把深奥的哲学道理讲得浅显而明晰);不过他讲演中随手拈来列举的许多古籍和先哲的话语,一方面使我们这些小大学生开了眼,对冯先生的博学极其佩服;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到很困难,因为毕竟我们许多书还没有读过。
大概领导和冯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开讲后不久,就让人抬上了一块黑板,又上来一位老师配合冯先生讲演写板书。
冯先生讲演中提到的任何先哲和古籍中的话语,这位老师都能很快在黑板上写下。这下,我们除佩服冯先生的博学外,对这位老师的“博学”也十分佩服。事后我们得知,这位老师是我们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杨宪邦讲师。
冯友兰先生在讲演后,就把这次讲演内容整理成文,以《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公开发表了,结果被人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引发哲学界一场大争论。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抽象继承法”又被上纲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屡遭批判;“文革”中更是成为打倒冯友兰先生的“重要罪证”之一了。
请冯友兰开会
1960年年初,我和一些同学被通知提前毕业,分在哲学系各教研室任教。我和罗国杰等四个同学一起,由罗国杰(他学识高、资历老,年龄也比我们大许多)领导,筹建新中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可是我们从没有学过“伦理学”,当时中国也无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书籍可读可借鉴,于是就从查《哲学词典》中的“伦理学”条目开始,一点点积累学科资料。
当时中共虽已和苏共闹翻,但苏联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上还是先我们一步,他们已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纲》公开发表。
于是教研室让我将其译出打印作为蓝本;又经过近一年努力,我们伦理学教研室也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这个《大纲》怎么样,哲学系领导决定开一个伦理学讨论会,请有关专家来对《大纲》提意见。在请的专家中,冯友兰先生是第一位,还有贺麟先生等。
讨论会在196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举行。那天上午,系里突然通知我,让我会前到北大冯友兰先生家去接他一下。那时我年轻懵懂不知规矩,一不知去前要打电话预先联系一下,二不知接冯友兰这样的大专家,是要小车接的,就自己乘上了32路(即现在的332路)车去了北大。
到后按照事先打听到的地址,找到燕南园冯先生住处,冯先生迎了出来,知道我来接他,说:“不用接,我自己可以去。”他请我在客堂坐下,他去取材料。我环顾一下客堂,光线较暗,但古朴,书极多,连走廊都放了书,我平生第一次在一个人家里见到有这么多书,真是开了眼了。很快冯先生出来,我们一起又坐32路车来到人大。
开会后,与会专家基本肯定了这份《大纲》。但也提了些意见。冯友兰先生提了些什么,具体已记不清了,但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中国的伦理学要有中国的材料,和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相衔接。他这一意见今天看还是对的,但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下,有人觉得他又在“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老古董”,准备写文章批判他(后来没有写)。
散会后,系主任张腾霄立即吩咐我去学校叫辆小车送冯先生回北大。我刚要起身,冯先生说:“不客气了,我到隔壁餐厅去吃顿饭。”原来,当时困难时期油水少,人大旁边西颐宾馆开了家高价餐厅,一个菜要十几元几十元,我们这些每月拿56元工资的小助教吃不起,但对冯友兰这样的一级教授(每月有300多元工资)和全国政协委员(听说有100元车马费)就不在话下了。
怎样“保护”自己
当时,已到了“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冯友兰已成了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一个“反面教员”,他讲的任何话语,写的任何文章,不管意思对错,都有人按照相反意思来批判。我就遇见过一次。
那时,人大和北大的哲学系正奉命编一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两系在中央党校开一系列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我有幸参加了一次。这次会冯友兰参加了,参加的除两校中国哲学史的教师外,还有一些有关专家。冯友兰在会上发了言。
他讲的是古代统治阶级哲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只见他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哲学思想也占统治地位。
冯友兰刚说完,立刻遭到与会者的一通批判,只见一位著名左派哲学家关某指着冯友兰说:“冯友兰,你错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怎么成了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呢?古代哲学思想中占普遍地位的永远是代表劳动人民、具有人民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实质是为统治思想辩护,为统治阶级辩护。”
冯友兰在大家对他批判时,摸着胡子微闭双眼,一点不动声色,可是在关某批判发言后,他突然睁眼睛,说:“关某同志,我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可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话。”大家一听愣了,关某马上问他:“马克思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的?”冯友兰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
原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刚翻译出版不久,许多人还未读过,而冯友兰已先读了,并在发言中加以引用,还不作说明。这使关某和其他批判者十分尴尬。
我当时感到冯友兰十分“狡猾”,“老谋深算”;很会“保护”自己,很懂得“战略战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大概是冯先生多年在受批判中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本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