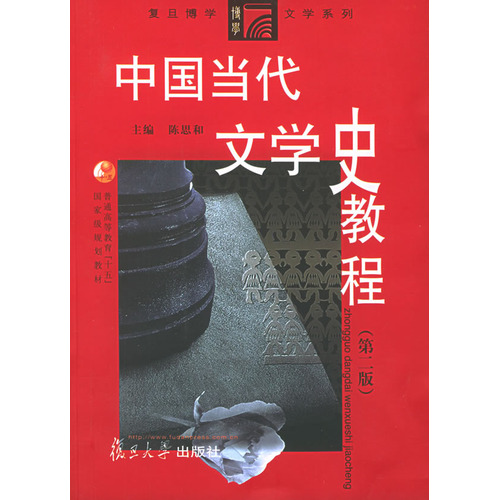陈思和《现代文学史》 陈思和:现代文学史的语言问题
我想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个话题将来会成为显学,越来越被大家关注。文学语言本来是不分家的,但是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语言归语言,文学归文学,各自都有很多研究,现在把这两者重新放在一起来讨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80年以前,老校长陈望道先生就在复旦大学开设了中国修辞学的课,后来形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修辞学发凡》。修辞在西方是有悠久传统的,从古希腊伊索克拉特(Isokrates,公元前436年—前338年)时代就开始,但在中国,能够在高校里开设修辞学,讨论语言问题,是与新文学运动有关。
陈望道先生就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骨干,他在开设修辞课程的时候,就把语言和文学两个学科结合起来了。我们现在虽然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是把语言和文学放在一起,其实这是两个有各自特点的学科,把语言、文学放在一起来研究讨论,这在复旦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复旦大学有很多老师是从人文的立场上关心语言学,包括后来的张世禄教授、申小龙教授,现在到郜元宝教授,他们都关心文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人文的立场,从文学的立场来考察语言的规律,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在复旦有这么一线传统,点点滴滴的积累,语言研究中的人文立场和人文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多,但我是这样想的:明年是2017年,新文化运动已经一百年了,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推动新文学运动,最初新文学运动是白话文运动,推广白话文,后来慢慢地变成新文学运动了。
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五四”这么大的一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起源是在语言,是从语言开始爆发的革命,然后逐渐推动了这样一个影响了整个国民、影响了中国未来走向的大思潮,语言运动借助了文学,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这样一种关系就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了,我觉得这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是有关系的,他是在哲学背景下推动语言的改革,这样一种改革,过去没有过,未来应该也会很难出现。
就在“五四”时候,在一百年以前中国就是突然出现了语言和文学高度结合又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转型和发展的这样一个运动,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新文学运动,如果不从语言开始,总是失去了它最精彩或者说最核心的问题。
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最近正在杀青,元宝教授帮我写了其中最重要的几章,就是讨论新文学运动的语言,我们一起设计了有关章节,从章太炎的古文,到章士钊的逻辑文,再到吴稚晖的那种纯粹的西化白话,这样多种尝试、发展演变到最后就形成了“五四”新的白话文运动,这一章郜元宝教授写得非常精彩。
所以说,讨论新文学,先讨论语言革命,语言隐含一种思维形态,反映了民族的思维形态,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思维形态。
所以,胡适陈独秀们斩钉截铁地要从语言改革着手来发起新文学运动,就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这样一个运动——启蒙运动也好,现代化进程也好——都不是个别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审美问题,而是一个国民改造问题,他们是要推动整个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就是民族再造这样一个重大使命,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只有一样东西是能把全民都联系起来,那就是语言。
语言是一个能够把整个民族拢起来的东西,要推动一个民族的改变,语言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怎么来高评这一百年来的白话文都是不过分的。没有白话文就是没有后来那么丰富的现代汉语,白话文越彻底,就越能掌握中华民族的话语权。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是关于文学运动与语言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语言革命开始发起的,获得了成功。从思维形态的发展来说,白话文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倾向:一种就是胡适提倡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也是黄遵宪所谓的“我手写我口”,就是把这个“言”和“文”完全一致化,胡适在这一点上是有所坚持的,他做得非常彻底,他一直到死了,我记得台湾“中央研究院”边上的胡适墓碑上,还刻着“胡适之先生的墓”,我们一般都是“某某之墓”,胡适墓没有用“之”,而是用“的”,是非常彻底的贯彻言文一致。
这样一种彻底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文形态,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普及,是一种旨在消灭社会等级的文化普及运动,语言是没有阶级的,但是使用语言的人是有阶级的,当知识分子使用高雅的文言文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他就与所谓的下等人(劳动大众)区别开来,那么胡适宁可放弃这些高雅的语言形态,采用所谓“引车卖浆者流”都能听懂的语言来推广他的思想。
我们后来的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整个思路是在朝平民化在发展,后来左翼文艺讨论什么大众语,一直到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等,这一路下来,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基本走向。
这条路线对文化的普及是很有价值、很有作用的,但是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未必就好。文言文是积累了两千年实践传统的中国人情感美学的载体,这个载体在完全被破坏和抛弃以后,它必须要转换为另外一种现代汉语的、现代语言的美感的形态,来满足现代人更加复杂的感情因素的表达。
这是“五四”新文学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没有解决好,但是新文学作家们是在努力解决,这就是我们长期缺乏认识的语言欧化的问题。
当真正“五四”新文学兴起,它的标志性的作品,不是晚清小说,不是晚清白话,也不是传教士翻译《圣经》的白话,而是鲁迅的小说。现在我们学术界很多人都在研究晚清传教士的翻译,也有人研究晚清小说的白话,似乎得出一个结论,白话文不是从“五四”开始的,而是在晚清或者更早的时候就产生了,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在很多年以前指导过一位博士生写论文,她研究1921年以前的《小说月报》,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文学白话文其实不用搞,不搞,民国初年的小说也是写白话文的,而且那么通畅,那么纯粹。
新文学运动恰恰使文学创作受了大量西方文化影响,写出来的白话文都拗里拗口,反而不通俗了,因为原来《小说月报》上的语言都是非常通俗的。
当时那位博士生与我讨论了很久,这个问题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慢慢意识到,恰恰不是晚清以来的白话文,恰恰不是从《红楼梦》和《水浒传》开始的那种传统白话文学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而是来自欧洲的翻译语言,就是我们一直诟病的欧化的语言,这种语言进来,成为我们新文学的主流语言,才是一种具有美感的、能更准确描述现代人审美心理的语言。
鲁迅说得很清楚,人家都批评他,说他硬译直译都不好,读起来不顺,鲁迅就说,我根本就是不要你们舒服么,就不要你们读得很顺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要你们改变自己的脑子,改变你们的思维。
中国人的原来的文言文是一种模糊结构,意义比较笼统,比较朦胧,不利于中国人接受现代的先进思想,中国人缺少的是一种更加严密、精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结构,也就是思维形态。所以他用西方人的语言结构来翻译小说,就是要你知道西方人是怎么理解一句话、怎么表述内心世界的,这样一种语言结构可以导致一个人对内心世界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深刻,更有利于把现代人的丰富感受表达出来。
古代人写文章常常带有一种抒情性,但很少做到清晰、准确,但是现代白话是可以做到的。
我一直引用鲁迅《狂人日记》里的语言描写:“不能想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个段落里这两句是非常经典的欧化语言:“……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这种重叠的双重否定,在中国古代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这句话不用这种双重否定来表达也是可以的。就这么写:“大哥就把妹子的肉和在饭菜里给我们吃,我就无意中吃了妹子的几片肉。
”这么写完全可以,而且更清楚、顺口。但是鲁迅作为文学家他要表达一种更加深邃的心理活动,他就用这样一种双重否定的方法,表达一个狂人根本不想承认自己吃过人但又不得不承认的内心挣扎,他根本不想承认,他是在拒绝,不断在用否定来拒绝,但到最后还是没有拒绝,因为他用了几个否定导致了最后的意思还是吃了人。
这样一种痛苦的、不得不承认的内心世界,如果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表达是表达不出来的,他只有用一种很拗口的、很复杂的欧化语言结构才能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当鲁迅吸收了西方语言的时候,他不是只学了一个西方的语法结构,他是把西方人的思维,把西方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都接受过来了。 这种欧化思维形态,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茅盾小说、巴金小说、甚至叶圣陶的小说里面都有,但我们今天看不到,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解放以后作家出版文集修改过的文本,作家们都认为自己当初的欧化语言是不纯粹的,不通顺的,都把自己的文字改过来,改成我们今天最通俗、给工农兵看的一种语言,所以,我们今天读巴金的小说,读叶圣陶的小说都觉得他们的语言好啊,语言大师啊,但是在最初那个时代,他们的语言都是不规范的,都是用那种拗里拗口的、我们今天说有很多语法毛病的这样一种语言来表现的,但是恰恰是这种不规范的可能有很多毛病的、也可能是生搬硬套的语言,打乱了中国人一直以为唯美啊、纯粹啊、传统的审美习惯,欧化白话把一种让我们感到不习惯的,感到陌生的、惊讶的甚至感到要拒绝的语言结构,或者说是思维形态,慢慢地引进中国,让新文学作家成为具有现代思维能力的人,成为一个现代的作家。
鲁迅是掌握了这种新的思维表达能力的作家,他在小说里嘲笑了说着“多乎哉不多也”的孔乙己的语言,鲁迅也怜悯像中年闰土那样,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欧化语言缺乏历史的、公正的评价,因为我们后来要强调为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似乎是越通俗越好,都写到诗歌里去就觉得是大众化了,所以文学语言不断改变,欧化的因素都慢慢改变掉了,慢慢就改成我们现在都能说的口语。
但是我还是认为,五四时期欧化语言的引进,是白话文取得实质性胜利的根本性原因。可惜这个影响在今天只有部分理论研究中还有所坚持,从鲁迅到胡风,从胡风到阿垅、路翎,再到上世纪80年代刘再复提倡方法论以后,大量的西方文论传入中国,直接影响了许多理论工作者的文风。
虽然这种种文风常常被人诟病,但是我还是想说句平心而论的话,文章写得拗里拗口不通顺当然不足取,但如果作者自己确实是那么感受和思考问题的,也未必就是坏事。
我不认为写得非常流畅的文章就是达意了,非常流畅的文章也可能是作者的思想本来就很浅,一杯白开水,什么都一览无余,自然是很简单,或者就是有了深刻思想却表达不出来,辞不达意。
我觉得一个理论家如果思想很复杂,思维形态很丰富,他思考到某种精微处、复杂处,他自己也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混乱的,这个混乱在语言表达上可能是败笔,但是在思想上,可能是他更加深刻了。
这个对我们通过现代汉语来探索美学高度、探讨现代汉语精深博大的美学形态,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这个今天的研讨会能够取得成果,就是从哲学意义上,从思想意义上,来讨论新文学所获得的语言的成果。 [作者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433)。录音整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王佳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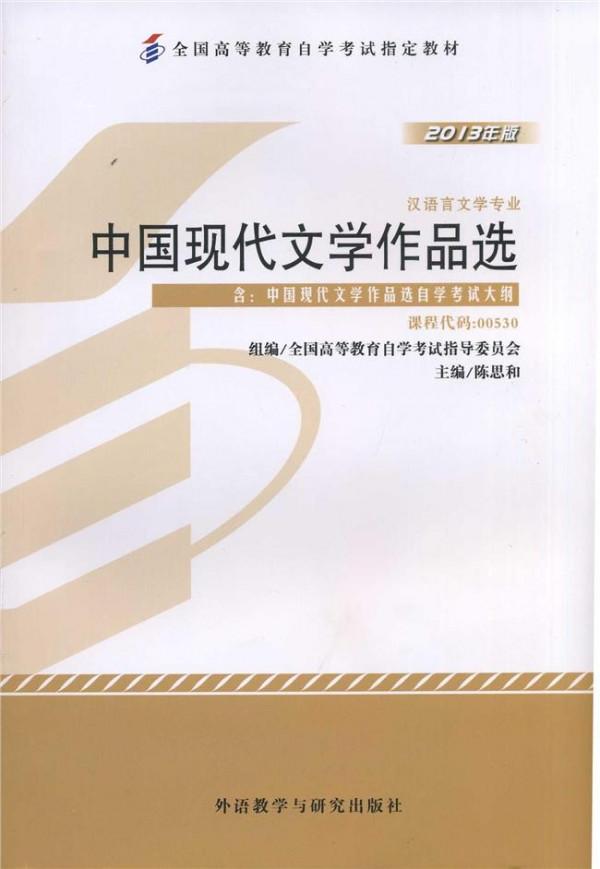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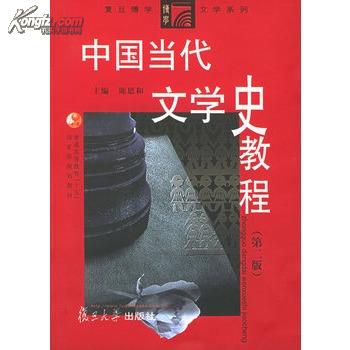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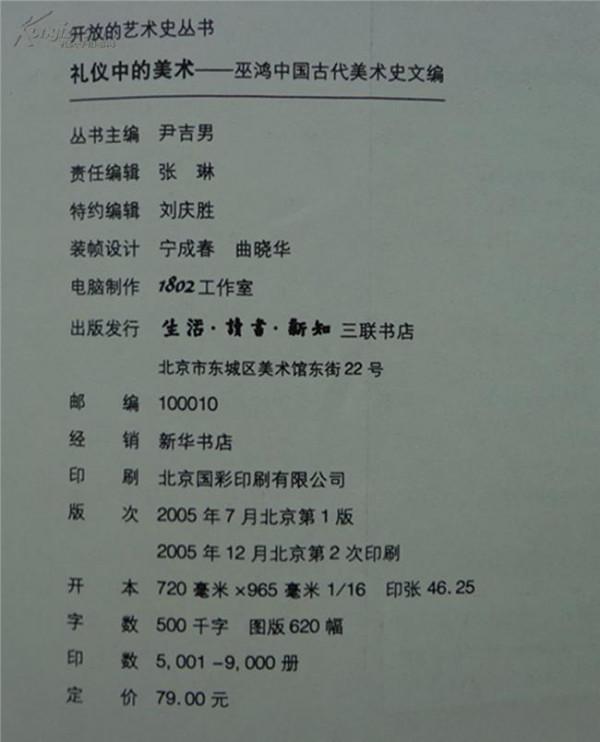

![>[原创]我为什么不喜欢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https://pic.bilezu.com/upload/7/79/7791938d725525f0fa86d29349b9c050_thumb.jpg)
![>陈思琪个人资料:陈思琪art微拍私房照片曝光[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7/d0/7d0abf1d9a663d698f43b8a83c6a4956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