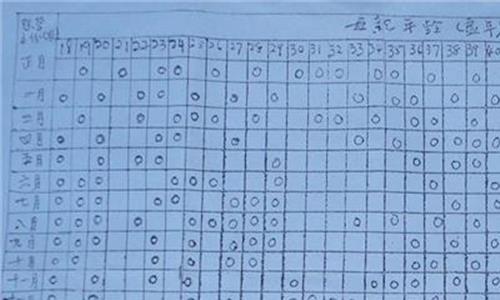玄学的科学依据 玄学再强大也逃不出科学的掌心
一场关于人生观的论战:玄学再强大也逃不出科学的掌心
从1923年2月到1924年年底的近两年时间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科学与玄学展开,被称为科学与玄学论战,同时也被称为人生观论战,此次论战最终衍变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争论不仅涉及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同时还涉及了东西思想文化的对比,为我们了解20世纪20、30年代的东西社会文化提供一次深度剖析的范本。

一、人生观能否与科学分家?
这次论战发端于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此次演讲的主题为人生观,主要是对科学主义中“科学万能”的思想提出批评,演讲词随后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张君劢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截然不同,科学是客观的、是物质的、发起于事物之共象,为因果规律所支配,科学可从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是主观的、是关于精神的、起于直觉,具有人格之单一性,是自由意志的。

在“我”与亲族、异姓、财产、社会、外界物质及信仰关系中皆是以“我”为中心。
从对东西文化的态度来看,张君劢认为中国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需要被颂扬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在张君劢看来,西方的物质文明是有重大缺陷的,以为其未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进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张君劢的演讲词发表后,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撰写《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批评张君劢的观点,此文随后于1923年4月12日发表于《努力周报》,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为了驳斥张君劢的观点,从人生观能否与科学分家、建立在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科学智识论、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三个维度分析,并认为张君劢的人生观逃不出科学的范围,进而指出张君劢对科学、对欧洲文明及对中国精神文明的误解,批评张君劢为“玄学鬼”附身,最后指出根据时代的诉求,要承认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的问题上。

丁文江的反驳随后又引来了张君劢的反击,张君劢再撰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此文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二、激烈的交锋
1923年5月,论战进入了新阶段,双方阵营不断壮大,论战全面展开并逐渐深入,众多学界翘楚逐渐加入论战,首先加入的是梁启超,1923年5月5日,梁启超撰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此时的梁启超表示中立,5月23日,梁启超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正式加入玄学派的阵营,张君劢和梁启超是玄学派的主要代表,除此二人以外还有林宰平、甘蛰仙、菊农、王平陵、范寿康等人。
在科学派一方,继丁文江之后加入科学派的是胡适,除了胡适和丁文江以外,任鸿隽、章演存、朱经农、唐钺、王星拱、陈独秀、吴稚晖等也是科学派的重要力量。
1923年5月11日,胡适完成《孙行者与张君劢》,暗指张君劢为孙悟空,科学和逻辑为如来佛,玄学即使再强大也逃不出科学的掌心。此文随后发表于《努力周报》,以此文为开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强烈的攻势,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从八个方面反驳了张君劢的批评,主要针对张君劢的反进化论、人生观的定义、对科学的误解等进行反驳,并继续宣讲其科学的知识论。
丁文江于6月5日在《努力周报》上又发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此文附有大量书目,主要驳斥玄学就是本体论的观点。除了胡适和丁文江以外,任鸿隽、章演存、朱经农、唐钺、王星拱、陈独秀、吴稚晖等也分别撰文驳斥玄学派的观点,任鸿隽的《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一文主旨是澄清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认为科学可以影响人生观的形成,也可以间接的改变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在《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一文主要驳斥了张君劢在演讲中列出的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的分析,朱经农的《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更是对张君劢提出了诸多疑问,包括张君劢所阐述人生观的是非因果、对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等方面都提出了质疑。
唐钺撰写了五篇文章,其中《“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和《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两篇文章是反驳梁启超提出的关于爱和美是不可分析的论点,唐钺认为爱与美之情感是可以分析的。
《科学的范围》一文认为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并解释什么是现象,什么是科学(比如,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但鱼本身并不是科学),唐钺的《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一文主要是反驳范寿康的论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其他的科学派的代表也陆续发文反驳玄学派的观点。心理学家陆志伟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文章《“死狗”的心理学》一文,指出无论是张君劢还是丁文江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心理学,但其实都不懂心理学。随后王星拱发表《科学与人生观》一文,认为科学的人生观是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是依据科学态度整理思想、构造意见进而指挥行动的原则。
吴稚晖在《晨报副刊》和《太平洋杂志上》分别发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和《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两篇文章,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中吴稚晖指出,中国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并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批判,吴稚晖撰写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洋洋洒洒6万余字不仅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并将宇宙的一切都可以以科学解说的观点解释得畅快淋漓。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发起了反击。张君劢于1923年5月在中国大学又发表了一次主题为《科学之评价》的演讲,他指出审美、意志、理智、行上、身体是人生最重要的五个探索方面,科学主义只注重身体和理智,而对行上和情意无力阐释。
梁启超于5月23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一文界定了人生观的定义,对理智和情感进行了分辨,肯定了科学的作用,指出所有的言论都基于观察,而观察离不开科学程序,自由意志与理智是相辅的,梁启超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但最终文章的结尾充满了对情感和自由意志的歌颂。
玄学派的代表林宰平随后也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全文系统的抨击了科学派的观点,林宰平从心和物的关系角度出发,对丁文江的经验论原则进行批判,认为丁文江所认为的处于根本的经验是靠不住的,否定了丁文江的经验原则,进而抨击了科学神圣的地位,捍卫张君劢的观点,林宰平并不否认科学对人生观有益,但是反对人生观为科学所支配的观念。
菊农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人格与教育》一文,其在东西方文明对比方面的观点与张君劢相一致,认为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结合,个体生命的完善是生命意志的体现,即人生的目的是通过自有意志的创造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以贡献于全体。
屠孝实撰文《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主要表达了玄学绝不可无的观点。
王平陵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科哲之战”的尾声》,此文探讨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甚至将此次的科玄之战称为科哲之战,认为科学想要排斥哲学是办不到的,科学和哲学是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者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论战持续到1923年年底,科学派和玄学派都将自己的观点和成果搜集起来,以出版图书的形式作为论战的重要成果,两派均于1923年12月出版文集,科学派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文29篇,再加陈独秀、胡适两篇序;玄学派出版《人生观之论战》一书,此书收文30篇,再加张君劢序一篇,两本书的体量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观点截然对立。
两派在思想上的交锋吸纳进了新的内容,尤其是科学派的《科学与人生观》不仅表达了科学派的主张,同时还推出了中国现代思想上的另一个重要的派别,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其标志是陈独秀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做的序和与书中所收入的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两篇文章所展开的辩论,可见,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在思想领域的进一步深化。
此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科学派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科学派的影响和力量更加强大。发起于科学派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可以称为是唯物史观派),在论战的后期其实是向科玄两派同时展开了批评,从陈独秀和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撰写的序便可看出,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是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其中,陈独秀批评了张君劢和范寿康的人生观,批评了梁启超情感胜于科学的观点;对于科学派,陈独秀批评了丁文江的唯心论,指出世界的发展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只有物质基础才能支配人生观,才能解释历史。
胡适的唯物史观蕴含于他提出的著名“胡适十诫”中,胡适从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了人生观、心理现象、道德理教等现象。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对科玄两派正式提出批评的是邓中夏和瞿秋白,邓中夏于1923年11月24日在《中国青年》第6期发表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清晰地勾勒了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指出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并分析了唯物史观与科学派的异同,认为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派在根据科学、应用科学方法方面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唯物史观派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上更加彻底和坚决。
1924年1月26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指出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应联合起来迎击玄学派。瞿秋白于1923年12月20日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在此文中,瞿秋白分析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驳斥了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
其第二篇文章《试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于1924年8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3期,此文主要是批评胡适的实验主义,指出,实验主义不是彻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甚至可以说是革命哲学。
1924年5月25日陈独秀撰文《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于1924年8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3期,批评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和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此外科学派的萧楚女于1924年8月在《新建设》第2卷第2期上发表《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一文,指出东方文化派和精神文明派反对科学、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是一种幼稚并落后的观点。
1924年7、8月以后,虽然科玄论战已经接近尾声,但还有一些关于科学论战的论文发表,如谢国磐的《评吴稚晖的人生观》、陈大奇的《略评人生观和科学论争-兼论道德判断的普效性》、张颜海的《人生观论战余评》等等。
四、科学派最终获胜
从整个论战的过程来看,科学派是胜利的一方,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主要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玄学派的方法,认为玄学派的方法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是不可靠的;二是玄学派的来源也是不可靠的,玄学派的观点来源于伯格森,而伯格森的哲学在当时西方哲学家的眼里是不值得一提的;三是玄学派是缺乏可行性的。
科学派所倚重的科学方法包括经验主义方法和逻辑主义方法,科学派对于科学的功能秉承着一种科学万能的观点,包括科学方法的万能和笼统地讲科学的万能,甚至把科学主义神圣到宗教独断的倾向,这一点也是受到玄学派攻击最多的,唯物史观将玄学派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的反动派,主要是因为其在科学和唯物两方面的反动。
唯物史观派承认科学派属于科学的范畴,但认为其科学性是不彻底的。
在西方学者看来,发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就如同17世纪欧洲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抉择时的意识危机一样,只不过中国的这场论战增加了横向的、纵向的、互相矛盾的东西价值和文化选择而更加复杂化罢了。
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科学主义缺少实践的基础,事实上,西方的科学及哲学的科学化经历了几百年的实践,是经得起时代的检验的,正如19世纪中期西方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及实用技术的历史构成的,这些实用的、有效的技术来源于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通过实用技术手段,人们摆脱了赤贫,拥有了舒适和奢侈品,获得了培养高级知识所必需的闲暇。哲学、艺术与自然科学之间也密切地联系着,他们彼此助力,在进步的过程中携手共进,在实际生活中,工厂、实验室和自然哲学家的研究是紧密结合的,没有科学的帮助,技术将是可轻蔑的;没有实践的应用,科学将只是空洞的理论,人们将没有动力去追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的资金、科学、技术的传入,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极大的震动与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的反思,发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由于缺乏科学实践的基础,尽管在西方学者眼中有些肤浅的意味,但对于中国来讲,此次的论战正是科学主义在中国开始盛行的开始,为中国日后的改革和革命提供了哲学上的基础和思想上的准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一场关于人生观的论战:玄学再强大也逃不出科学的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