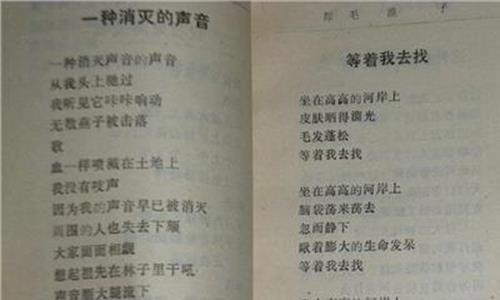钱玄同发现鲁迅 钱玄同说长道短话鲁迅
鲁迅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自己是鲁迅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交往长达二十九年,这个过程被钱玄同总结为尚疏、最密、极疏三个阶段。“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这种交往关系,既能使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鲁迅,又能使他脱离亲疏关系的成见,以一种超然的心境,认识鲁迅,评论鲁迅。

同是章太炎的学生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鲁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章太炎先生处听课,见面机会虽然有了,但却很少说话。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钱玄同读了《域外小说集》,认为“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

他印象很深,鲁迅为使翻译的文章更符合汉字的训释,特意向章太炎先生讨教,“以期用字妥帖。”这样,“《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
回国后,鲁迅在教育部供职,钱玄同则执鞭教学。1917年1月,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由上海带至北平,使它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人刊物。陈独秀早慕鲁迅的大名,很想让他加入《新青年》行列,写写文章,以壮声色。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此时,作为“愿意给它(《新青年》,作者注)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的钱玄同,已在《新青年》发表了很多战斗性的文章,他的文章风格独特,如鲁迅所评:“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文学革命是钱玄同和陈独秀所共同努力的目标,而让这个阵营壮大发展,又是他们的愿望和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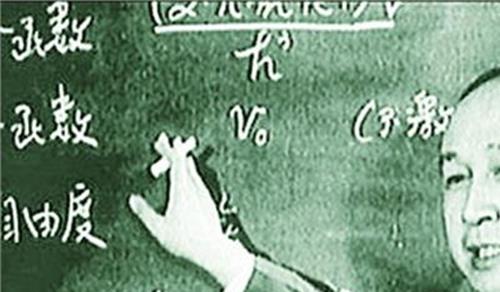
这一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震荡,面临如此多的变故,鲁迅失望了,沉默了,用他自己话说,“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的愿望。”
陈独秀想到了鲁迅,钱玄同更想到了鲁迅,因为,他对鲁迅的了解毕竟要深入的多。他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周作人先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而鲁迅还没有文章送来,钱玄同有些急了,他说:“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了。自此以后,豫才(即鲁迅,作者注)便常有文章送来”。
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据周作人的记忆,钱玄同来绍兴会馆,也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S会馆,时间当在8月,一共来了三次。这天晚上,钱玄同带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来到绍兴会馆,他的微胖的身躯刚一落座,脸上便沁出一滴一滴的汉珠。
钱玄同翻着鲁迅抄的古碑文,以不经意的眼光望着鲁迅,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又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当然清楚,这是他在邀自己“入伙”,为《新青年》写稿件。《呐喊·自序》中记下了他俩当时颇有意味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 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被说服了,再也不抄古碑文,以笔作投枪,锋芒所指,当然是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它的意义就决非是一篇白话文小说,而是周作人所说:“如众所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显而易见,如果不是钱玄同的催促,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多少年,先生也许还会“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继续悠闲、隐默而颓唐着,文学革命的成果也许会是另一种表述文本。
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
多年后的一件事,使他们的关系罩上了黯淡的阴影。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产生轰动,其学术地位突显而上。而这恰是鲁迅、钱玄同两人关系不睦的起始。古史辩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倡导,而顾颉刚成绩最大。顾的年龄比钱小,成名又晚,其才识为钱所赏识,且多得钱的提携。
鲁迅是不赞成古史辩观点的,且又讨厌顾颉刚,故而撰文进行抨击,显然,所抨击的就不仅仅是顾颉刚一个人,自然也包括钱玄同。他们之间也开始少于走动,关系从此罩上了黯淡的色彩。
三年后的一天,鲁迅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不高兴了,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知道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最不喜欢顾颉刚,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的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离开,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鲁迅很不愉快,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不忘描述这次郁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作者注)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钱玄同在《两地书》中看到这封信,对鲁迅给自己的描述,也发了一番感慨: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 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民国)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 让他讨厌吧。”
说长道短话鲁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成为左翼文学之魂,受到青年的爱戴和颂扬,报刊多是溢美颂扬的言论。钱玄同对此不以为然,批评说:“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他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交往,指出鲁迅有三长三短,真的是说长道短了。
他说鲁迅的三大长处是:“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他举例说,鲁迅“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特别推崇《中国小说史略》,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这些著作都体现鲁迅的求真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
还比如:他治学和写作决非沽名钓誉,而是任凭“自己的兴趣”,这样在写作乃至成书后,“总不肯用自己的名字”,《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一例,这本杂集本是鲁迅编辑,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时,“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他著书只求“精善,从无粗制滥造”,这“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
再比如:他的小说抉发的多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大凡他的文章,真“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除此,他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那就是:多疑、轻信和迁怒。多疑往往使鲁迅“动了不必动的感情”;轻信往往使鲁迅在发现自己中了说“好听话”的人的圈套后,与这个曾“认为同志”的人,“决裂而至大骂”;迁怒往往使鲁迅以自己的好恶为准则,他“善甲而恶乙”,甲亦应随之而恶乙,切不可与乙善,否则,“遂迁怒于甲并恶之。”
他还担心由于鲁迅提倡“小品文”和“幽默”文学,那种深刻冷峭的文风,容易将青年引导到“冷酷”和“颓废”的路上去。
钱玄同说他对鲁迅的批评,是基于他与鲁迅交往的事实,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乱说。”这就是钱玄同的独特个性,他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陈独秀、胡适相似,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共允,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 作者简介 -
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 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家级中文类核心期刊《传记文学》和《人物》《百年潮》《炎黄春秋》《名人传记》等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类报刊和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转载。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
本文来自大风号,仅代表大风号自媒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