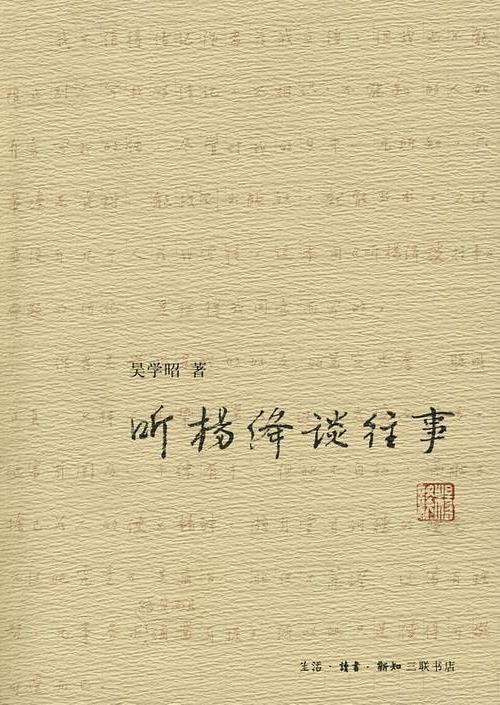费孝通杨绛是我的初恋 杨绛:“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
替别人写传记颇不容易,最要紧在把握作者与传主的距离,有冷静客观的态度才可写出为读者称道的作品。读这类传记很能看出作者功力,因虽为个人往事,总不免要涉及他人,而不甚高明的作者在记述友朋交游,或政要往还时,都有以突出传主而贬损他人的描述,很使读者反感。
尤其我们现在的传记,掺入太多的文学成分,使传记不堪纯粹,难以静心接受。因此我喜欢读个人回忆录,对传记不大热心,主要还在写传记的作者每每不能真实坦白地叙述传中人物。
吴学昭今年79岁,是钱钟书和杨绛大学时代的老师吴宓的女儿。吴学昭作《听杨绛谈往事》,是在杨绛《我们仨》之后,由旁人记述的杨绛个人与家庭——钱钟书、钱瑗的生活往事,并“谨以此书纪念钱钟书先生辞世十周年”。
钱、杨情趣只在自己家庭以内,不大与外人交流,能“听杨绛谈往事”,可见作者与钱、杨二人关系亲密。 《听杨绛谈往事》书前有杨绛《序》:“这本用‘听杨绛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征得我同意而写的。”说明此书所谈往事还兼有个人传记的责任。
杨绛老人业已九十八岁,尚能以毛笔工稳书写书名,且能以这样的高龄伏案写作,足令人心生敬佩。五年前写《我们仨》约九万余字,所记人物事件,叙述简洁妥帖,是一册词句好读的个人回忆录。
去年出版《走在人生边上》,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合起来可看出杨绛、钱钟书的人生大致状态。因而《听杨绛谈往事》,则不免要在这些回忆文字中,重新整理贯连,增入杨绛未曾写出的故事。
以作者与杨绛、钱钟书世交并至交之关系,探得私人往事不难,难在叙述文字的表达与议论的阐发,毕竟私交情感相互间靠得太近,要作冷静与理智地评价最可考验作者。“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
她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为了过于老实而吃亏。她富有阅历,干练有才,但她不自私,满肚子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颇有堂吉诃德的傻气。不过她究竟不是疯子,非但不荒谬,还富有理智,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所以她只是傻得可敬可爱而已。
”这是杨绛对作者所说的几句好话,而作者则在书里通篇铺满赞语,读起来很有点旧戏里小姐丫环相扶携的味道。 是书分十九章记述“听”来的往事,由1911年杨绛出生、童年及至成长,到钱钟书、钱瑗相继离世,九十余年世道沧桑,以约二十八万余字来叙述并不算多,只是作者在传记文字上使用大量小说式场景描写与人物对话,虚构色彩颇浓。
“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
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这话说得未免过于谦逊,大抵越是平常人越渴望不朽,这于风景区里或长城砖墙上“到此一游”的刻字可作证明。 其实杨绛晚年所写散文大多是回忆文字,该说的人和事几乎都已说尽,旁人为她写传除画蛇添足,饶舌评议,靠自言自语以增加人物的分量,也增加文字数量。
这或可视为传记写作之大忌,更不大喜欢传记作者以贬损他人来拔高传主的文辞,而这点尤其容易在传记作品里泛滥。
这里不妨引止庵《如面谈》书里《杨绛的散文艺术》文中一段话:“虚夸、浮躁、雕饰……种种不良的影响在杨绛某些同代人以至于其后的一两代人身上都有所表现,或许今后还不能断绝;大概是长时间以不正为正,结果不知道什么是正了。
”这也是许多传记作家往往以为多一些文过饰非的赞美、多一些夸张拔高的评价,才显出自己的深刻一般,并不清楚读者对此的感受。因此,读杨绛那些回忆文字原本是很喜悦的事,大可不必在这些回忆文字之外,再去写“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样词句怪异的“听谈往事”。
书中有些描述杨绛在“文革”时期的行为,读了感觉似乎与现实不甚符合,譬如:“杨绛是1966年8月7日被‘揪出来’的,对她的劳动惩罚是收拾办公楼的两间厕所。
杨绛不以为意,自己置办了小刀、小铲子等工具,还用毛竹筷和布条扎了个小拖把,带上肥皂、去污粉、毛巾和大小脸盆放到厕所,就埋头认真打扫、细细擦洗。不出十天,原先污秽不堪的厕所被她收拾得焕然一新。
斑驳陆离的瓷坑及垢污重重的洗手盆,铲刮掉多年积垢,擦洗得雪白锃亮。门窗板壁擦得干干净净,连水箱的拉链都没有一点灰尘。定期开窗,流通空气,没有一点异味儿。进来如厕的女同志见了都不免大吃一惊,对杨绛顿生敬重之心。
”读到此处,禁不住要想:若杨绛并不曾这般夸耀赞美自己,那么,“听杨绛谈往事”的真实言辞便大可怀疑。 既然听来的往事并非全面,许多事情当事人也不便随意对旁人谈。
坊间所传费孝通与杨绛的情人故事,在书中借作者之笔来作申明:“杨先生说:‘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不过这话说得颇含糊,亦易生出歧议,作者陷于辩白,实无意义。其实杨绛颇通人情温暖,体贴细心并不只为钱钟书一人,对友朋亦多有关怀。
去年到钟叔河先生家闲聊,钟先生在谈到去世的老伴朱纯病重时,为杨绛得知,写信给钟先生,说自己新近得到一笔稿费约24万元,欲汇寄给钟先生作朱纯老人治病所需。此事虽经钟叔河先生婉谢辞却,仍可见出杨绛之侠义品行,不需大发议论,亦足使人感佩。
此事书中未载,记在这里算作杨绛传记的补遗。 杨绛:与费孝通 只是普通朋友 《我们仨》是从钱钟书和杨绛结婚留学牛津写起,此前的种种读者并不知悉,以致数年前还有“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绛”等传闻。
在《听杨绛谈往事》中以杨绛与费孝通交往的细节澄清了谣言: 这年3月,钱钟书和杨绛初次在古月堂匆匆一见,钱钟书表弟孙令衔告诉表兄,杨季康有男朋友。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在工字厅客厅相会。
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从此书信往返,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爱情生活。 至于孙令衔告诉表兄说杨绛有男朋友(指费孝通),恐怕是费的一厢情愿。
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as an end not as a means);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他后来与钱钟书也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