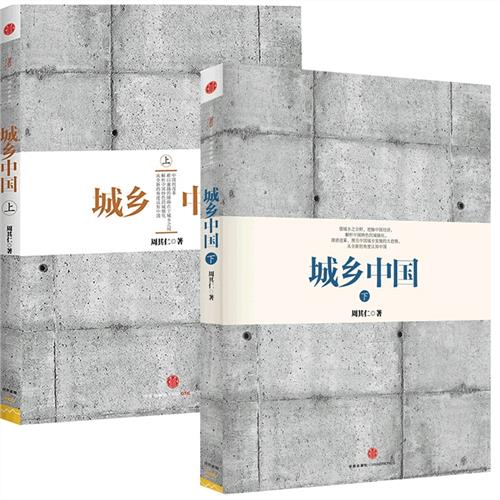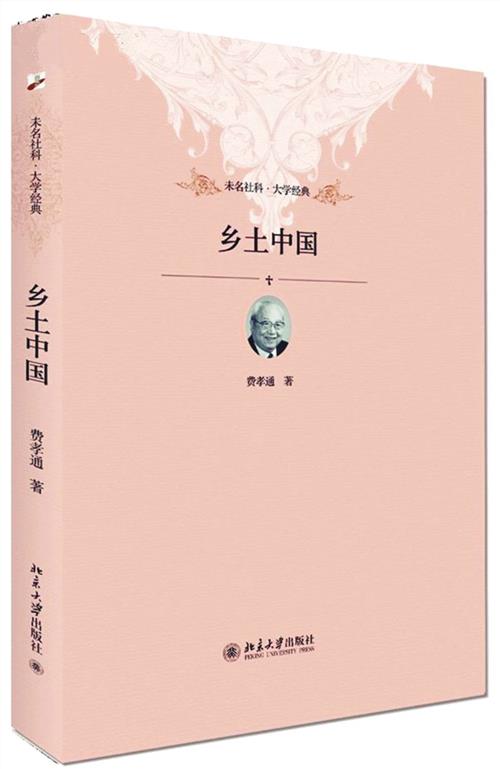费孝通江村经济 吴江当代第一人: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之路
吴江当代第一人: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之路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最近一拨是日本甲南等大学的学者。”开弦弓村村委会主任姚富坤回忆说,除了费孝通来过20多次,几十年来,村里经常有不同肤色的学生、老师出入,村里人对此已习以为常。
让村里最遗憾的是,“江村”早已被人抢注,村里只能沿用自己的原名———开弦弓村。 当时,费孝通身着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丝忧伤,开弦弓村村委会里保存着他当时的照片。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难。听从姐姐劝告,费孝通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 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一切似乎始于偶然,因此有人曾将费孝通的这一过程形容为“无心插柳”。但费的学生邱泽奇驳斥了这一说法:“无心源于有心。
受家庭环境影响,费从中学起就对国家、社会等重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
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 《江村经济》问世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
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
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邱泽奇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
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
重申恢复农村企业 费孝通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费调查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里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
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 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费进一步发现: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
邱泽奇说:费孝通用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费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 邱泽奇介绍,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费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江村经济》里,费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 “直到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一想起现代化,就知道是发展大工业、搞大城市。
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邱泽奇说,可以佐证的是,去年建设部公布的城市规划中,全国有184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 农副关系之辩 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 这一年,费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来华后,提出访问开弦弓;同时,国内政治格局开始难以琢磨: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了,费试图重提和呼吁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
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 费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
费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
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访江村》里,费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
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这一指责使费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的1981年。
在此期间,费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邱泽奇说,费从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书里,费说,自己只能通过家书让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至于荒废。就像老人通过晨练避免自己的腿脚不至于颓废一样。
“乡村工业”之争 乡村工业被认为是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开弦弓村一位老板到上海谈生意,上海人赶到车站迎接,农村人从来没有受到城里人这样的礼遇。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村里人说起的这些情况让他惊奇。
费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10多家,挤在三个大门内,在30年代这里只住了三家人。
费看到了工业和副业的重要区分,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费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
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了。 邱泽奇说,费孝通在经历半个世纪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即将在农民手中实现,他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工业下乡”。
费发现:5年前,回家带回来的都是无法“转”上去的状子,而现在却是要原料、要市场、要工厂的申请。费的讨论开始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延伸: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
此时,费的乡村工业的观点引发激烈交锋: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就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同样的问题甚至被提到全国人大上争论。 费认为,苏南出现的这些“新人新事绝非”是一种偶然。
他这样解释理由:“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
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在随后的九访江村中,费发现: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抢购一空。
开弦弓村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不下60户。 邱泽奇说,费孝通不相信,这样的解释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业化道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费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摆事实、算细账:1991年,费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1990年是59.
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 最喜欢摆事实 费孝通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
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选择后者。从1990年,邱泽奇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
邱泽奇认为,这是费总能发现其他学者未觉察之处的重要原因。 邱泽奇说: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费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费孝通曾告诉邱泽奇: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
费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邱泽奇说:费气质上属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温和,费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费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采写:本报记者 谢言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