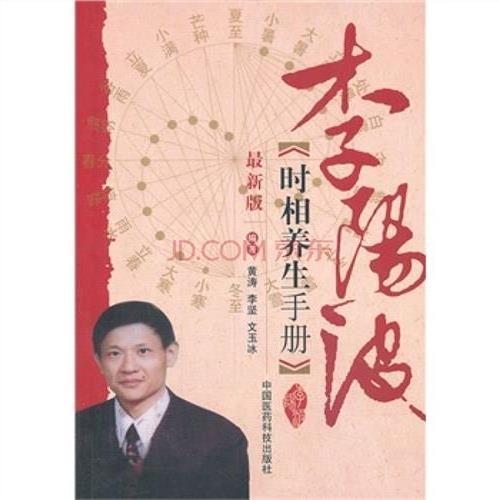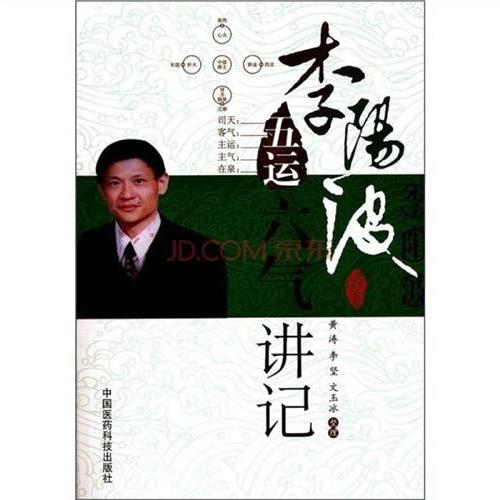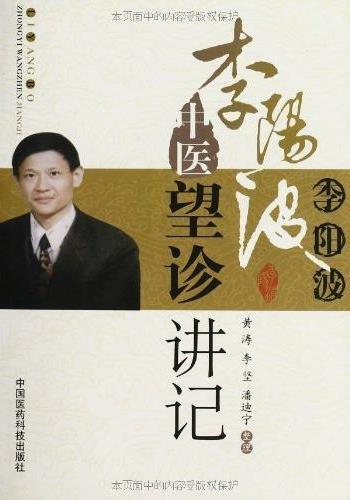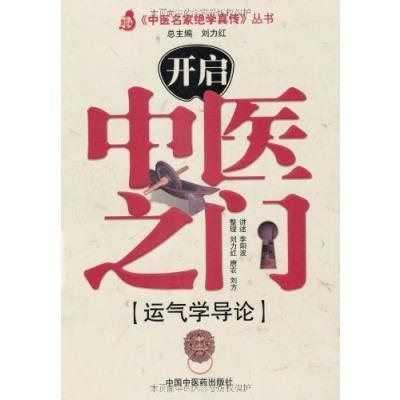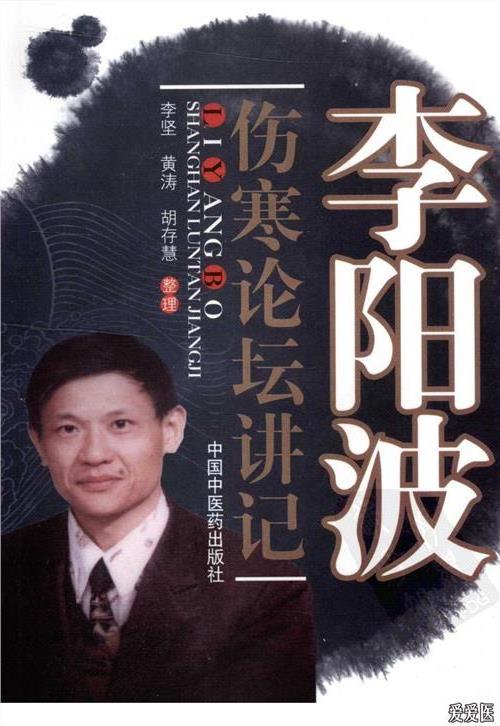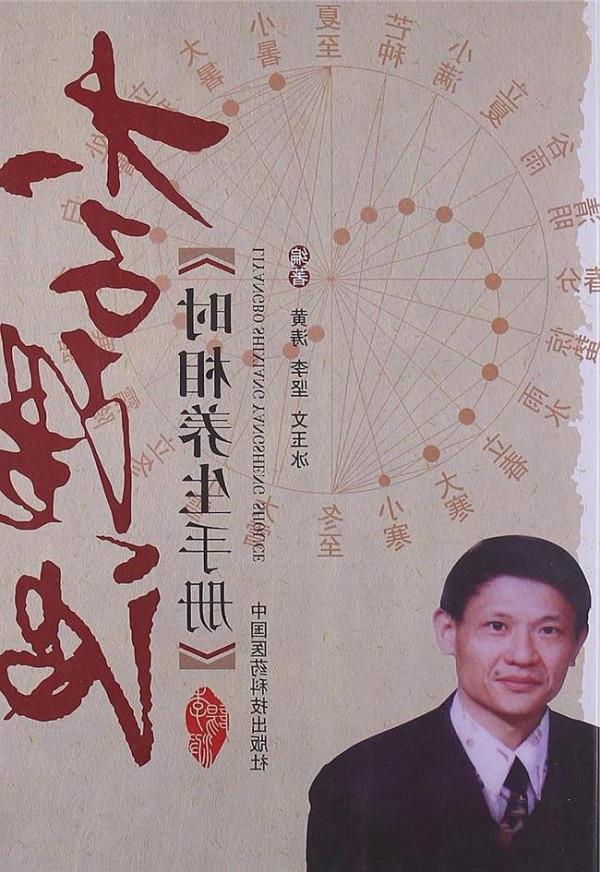辟谷者须读:名医李阳波之死与辟谷
王教授谈李阳波之7--辟谷之害(转帖)
阳波每天打坐入定,修炼气功的事我是知道的。什么布气摩面、意念、夹鼻、划太阳、拉耳、梳顶、拍顶、扣脑、摸大椎、浴手、浴身、浴腿、暖肾、浴肩背、浴丹田、悬照等等,一套下来最少也得半个时辰。以至于科委蒙主任想找他谈话,也得排到早上十点钟之后。
至于后来用气功外气治病、培训诱发特异功能乃至“辟谷”却知之不多,尤其是“辟谷”一事,只能从旁略知一、二。
“辟谷”又称“却谷“、“断谷”、“绝谷”、“休粮”、“绝粒”等即不吃五谷,是古代的道家方士当做修炼成仙的一种“内丹术”方法。道教认为,人食五谷杂粮,要在肠中积结成粪,产生秽气,阻碍成仙的道路。
《黄庭内景经》云:“百谷之食土地精,五味外羙邪魔腥,臭乱神明胎气零,那从反老得还婴?”同时,人体中有三虫〔三尸〕,专靠得此谷气而生存,有了它的存在,使人产生邪欲而无法成仙。因此为了清除肠中秽气积除掉三尸虫,必须辟谷。为此道士们模仿《庄子·逍遥游》所描写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行径,企求达到不死成仙的目的。
辟谷术起于先秦,大约与行气术同时。集秦汉前礼仪论著的《大戴礼记·易本命》说:“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是为辟谷术最早的理论根据。
《淮南子·地形》也有类似的记载。而《淮南子·人间》还载有实例,如记述春秋时鲁国人单豹避世居深山,喝溪水,“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是为史籍所载最早之辟谷实践者。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去〔却〕谷食气篇》,是现存汉前辟谷服气术最早的著作。有云:“去〔却〕谷者食石韦。……首重、足轻、体轸,则昫〔呴〕炊〔吹〕之,视利止。”意谓初行辟谷时往往产生头重脚轻四肢乏力的饥饿现象,须用“吹呴”食气法加以克服。这里将辟谷与行气联在一起,和《庄子·刻意》将行气与导引联在一起一样,似皆表明此三术在先秦时最初存在的状态,即表明它们之出现是大体同时的。
道教创立后,承袭此术,修习辟谷者,代不乏人。《汉武帝外传》载,东汉方士王真“断谷二百余年〔是“年”是“日”?应为“日”之误吧!〕,肉色光美,徐行及马,力兼数人”。
《后汉书·方术传》载:“〔郝〕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曹植《辩道论》载郗俭善辟谷事,谓曾“躬与之寝处”以试之,“绝谷百日,……行步起居自若也”。曹操招致的方士群中,甘始、左慈、封君达、鲁女生等皆行辟谷术。
东晋道士葛洪却反对单行辟谷可致仙的观点〔主张择仙术之善者而兼习之,尤其必修金丹〕,认为单行辟谷可成仙是行气家“一家之偏说”,但并不怀疑辟谷术的健身延年效果。
他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说:“余数见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并举出具体例子以证之:三国吴道士石春,在行气为人治病时,常一月或百日不食,吴景帝闻而疑之,“乃召取鏁闭,令人备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余,春颜色更鲜悦,气力如故。”又“有冯生者,但单吞气,断谷已三年,观其步陟登山,担一斛许重,终日不倦。”
《魏书·释老志》载,北魏道士寇谦之托言太上老君授以导引辟谷口诀,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又谓东莱道士王道翼隐居韩信山,断谷四十余年。《云笈七签》卷五载,孙游岳“茹术却粒,服谷仙丸六十七年,颜彩轻润,精爽秀洁。
”《南史·隐逸传》载,南岳道士邓郁“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陶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北史·隐逸传》称陈道士徐则“绝粒养性,所资唯松术而已,虽隆冬冱寒,不服棉絮”。
《旧唐书·隐逸传》载,唐道士潘师正居嵩山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而已”。其徒司马承祯亦传其辟谷导引服饵之术。
《宋史·隐逸传》载,宋初道士陈抟居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宋史·方技传》载,赵自然辟谷“不食,神气清爽,每闻火食气即呕,唯生果,清泉而已”。柴通玄“年百余岁,善辟谷长啸,唯饮酒。”
辟谷之术,史籍、道书所载,不胜枚举。从汉至宋,辟谷术在道教内一直十分流行。
史书记载辟谷之人如此之多,辟谷时间或几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其中难免有夸大不实之处,但也似非纯属子虚。
1988年1月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就曾以《麻城农家女十年粒米未进言行自如》为题,报道湖北省麻城市熊家铺区月形塘村二十五岁姑娘熊再定,十五岁时突染重病,生命垂危,脱险后即不复进食水,至今已十年粒米未进。令人惊异的是,她染病卧床八年后,竟能独立行走,谈笑自如,且能做些家务。可谓人间奇迹。
2004年3月20日,来自四川泸州的一名老中医陈建民走进吊在碧峰峡的一座悬空玻璃房中,开始他绝食49天的挑战之旅,5月7日,他离开了这座玻璃房。这一举动引发全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各种质疑的声音也不断响起。经过49天的坚持,陈建民挑战成功,从而成为世界上目前忍耐饥饿时间最长的人。
以上两例,可谓现代版的“辟谷之术”,与历史版的所谓“辟谷之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是假是真,勿庸赘言,读者自可判定。
古人辟谷之术归纳起来,不外“服气辟谷”与“服药辟谷”两大类。阳波后来要发放外气为人治病,同时又要用气功诱发别人的特异功能,身体的消耗是很大的。他从只吃糯米饭到吃糯米稀饭,后来据姨婆所说吃得更少。我曾发现其大量嚼服人参,用杞子泡水喝。估摸着阳波的辟谷是“服气辟谷”与“服药辟谷”二者兼而有之。
我曾跟他说过,你不是说人就像个“煤气罐”嘛,用完了就没了,“煤气罐”总得补点气啊,否则没气就点不燃。吃喝可是人的本能,也是生存的必须,人要是不吃不喝,不是病了,就是快要没了。
人类繁衍至今选择每日三餐是最佳的进食方式,年轻身体健康没病可能还扛得住,但积累到一定程度,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到那时可真的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哦。飮食均衡适量是应当的,但不食不喝可不行,缺乏起码的营养,没了物质的代谢,就没了根本。“低血糖”、“低血钾”……可是要人性命的。可知道,那煤气将来可是管道化犹如自来水般的啊。
他只是笑而不语,琢磨着他似乎是在寻求某方面的突破,想达到某种崇高的境界,存思神往,酬躇满志,充满着自信。还来不及琢磨个透他真实的想法,就闻其病倒了。
记得,那年农历正月初六〔新历2月20〕,我曾到过他家,他说“感冒”多日,身体不太舒服。我说不少病都是以“感冒”症状开始的哦!并说了句要注意身体的安慰话。
后来就听说是住院了,待我赶医院看他时已是农历二月十三〔新历3月28〕。明显的肝肾综合症、功能性肾功能衰竭了,目睛黄染、呕吐、说全身酸痛软困。化验报告单上表明严重的肝功能损害、氮质血症,非旦白氮严重超标,二氧化碳结合力偏低。估计还有原发的基础疾病。我说不行!得马上转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或自治区人民医院。
他说还是这里好,可以自己开点药什么的,“五办”的同志也说这里好。实属无可奈何!他嘱咐李坚妹妹叫始宁前去,似是有什么要事。临走时我还说,明天我跟曾老师、黄老师一起再来看你。
不料第二天天还没亮,始宁翻爬学校大门墙头而入,拍开我的家门,全身瘫软地坐在门口说道,小明半夜跑来告诉他,阳波已张口呼吸,十分困难了,待他赶到医院,人却走了。呜呼!哀哉!刚过四十五啊,惜哉!斯人已去,英年早逝啊!
阳波逝去,快二十年了,坊间传闻不少,我等本不应多说,如今说来似有不恭。当年尽管我们为学术上的事,有时爭得脸红耳赤脖子粗,也有为能有共同的见解而欢欣鼓舞,往事并不如烟啊!李坚妹妹曾嘱我写点东西,但由于近年来父母年迈有病,得在家操持,一直无法静下心来,何况我们观点相左,写出来的东西,不知其家人及弟子们是否高兴,所以一直没敢动笔。
其实,师生之间的不同观点,没有什么不可说的。正如阳波所说,我们是“亦师亦生”、“亦生亦师”,是“谢本师”、“谢本生”的事儿。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那国学大师俞樾先生无法说服其学生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也无法说服得了其弟子余云岫先生,不照样是师是生的,是弟是子。
大家所要服从的是道理而非师道尊严,学生与老师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爭辩,此仍“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使然也。可大家都忘却了该服从的可是“德先生”与“赛先生”哦,否则学术就没了个准绳,爭来论去始终无法得出个结果来啊!
近年来,退休在家,除侍候老人之外,稍有余暇,思绪万千,萌发了把“我这一辈子”都写下来留给后人的念头。其实,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过,与其皱眉头,不如偷着乐,冬天别嫌冷,夏天别嫌热,有钱别装穷,没钱别摆阔,闲暇养养身,每日找找乐。
酸甜苦辣都尝过,才算没白活!选对职业,成就一生;选对老师,智慧一生;选对伴侣,幸福一生;选对环境,快乐一生;选对朋友,甜蜜一生。
恕我直书,於是一口气写下了《初识阳波》、《烧香看病》、《迷于“河洛”》、《气功治病》、《误入“灵学”》、《辟谷之害》以及之前所写下的《陈李交恶》〔该篇应算本系列的第三篇,排在《烧香看病》之后〕等七篇愽文,以纪念我们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光阴。
后来是始宁以“病理解剖检查”为由,瞒过了护士长的严格盘查,由学校车队廖司机将其送回家,才得以入土安葬。后事是由存慧、始宁、和福等同学协助良珍母子及李坚夫妇办理,存慧与和福为其择的墓地,郑医生为其准备棺木,连夜冒雨送上了山。弟子们当时都不在,好在后来个个成才,为纪念阳波,将其当年讲稿整理成《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一书付梓出版。
我想,其家人及弟子们若有所知,我写了这么一些东西,大抵不会有所怪罪吧。他们也知道师傅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也从不迴避,一再承认孺子可教,不堪造就,更没“干一行爱一行”的决心。
可他们并不知道我与阳波之前还那么一段深厚的情谊,为着共同的焦虑和困惑,希冀寻求出一条新路。只不过他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亮和希望,而我所见到的却始终还是一片黑暗依旧。弟子们所听到、看到的都是验案,我所见到的却多是败笔。
可从《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一书的“序言”来看,阳波后来是不再相信钱老先生“中医现代化”那一套了!甚至还留下了“完全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小人”十分激烈的说辞。其实中医就是中医,没有必要去攀附什么,这“化”那“化”,必然最后连自己都“化”没了。
学校大门口右侧那幅“金字招牌”不是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就是一派胡言乱语!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是也,如是则中医已一无是处,还有什么“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可言。大慨那“走现代化的道路”离吾侪也太遙远了,我等恐怕都等不及了,但他又走进了另一条胡同!
我曾揣想过,如果不是那个令人伤心而苦难的年代;如果不是父母的原因;如果当年中学老师所送给他的那本书不是《黄帝内经》;如果没遇上气功、特异功能、人体科学;如果阳波是60后、70后;……。
以他的才智,其人生将是另一番图景。而绝不会走上“巧、工、圣、神”的不归之路!但阳波对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的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完整的领悟,对中医事业的执着,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和解读之深邃,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所谓中医专家、教授、愽士愽士后们,所望尘莫及、完全不能比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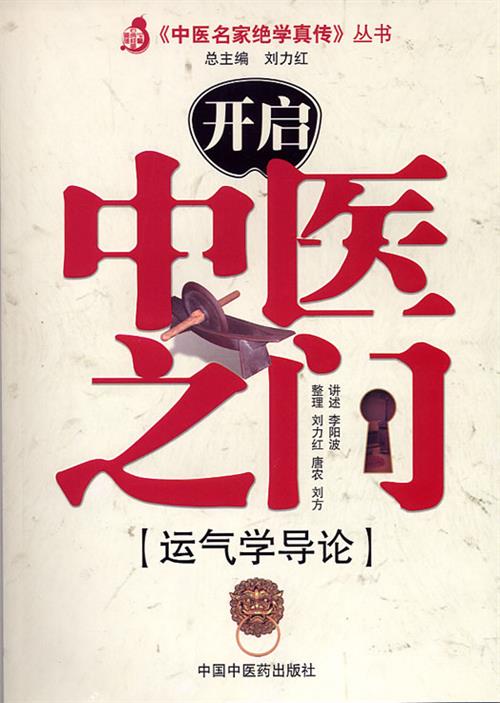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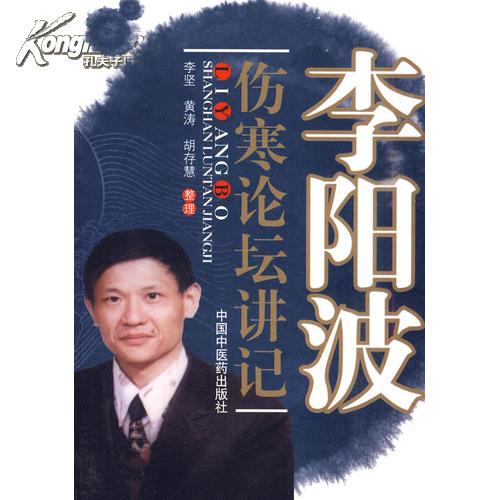
![[转载]转贴:李阳波传奇](https://pic.bilezu.com/upload/e/68/e681ea7b27f210adda40bbeb81eda78c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