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燕案斯德哥尔摩症 李浩囚女案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研究表明,产生这种心理疾病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一、 受害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二、受害人处于完全的绝望状态之中; 三、受害人所获得的信息只是施暴者愿意让他们知道的,施暴者不愿让他们知道的信息则被屏蔽; 四、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于受害人。
病人发病后的具体表现是:受害人对是非善恶完全丧失判断能力,对自身权益基本失去保护欲望,往往对解救者恨之入骨,对施暴者反而感恩戴德。
心理学研究同时表明,只有极少数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甚或是一部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乃至于整个国家的人。
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参看人类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以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上述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刚开始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就会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甚至崇拜这些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面对“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雉法令”,曾有百万明朝的遗老遗少挺身试法,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
然而200多年后,当辛亥革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革命的一个身体标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批批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标志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们的人质资格而痛心疾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合理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让我们理解了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那根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的“辫子”。 首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顺从。
事实上,面对暴力强权,只有低头服从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
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逐步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制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惩戒机制、规范的思想教育(五伦纲常)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封官进爵)实现的,从而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原始本能,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在无理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道理说不清,只好打得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
掌握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得以传播与彰显。 多年以来,无数中国人身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不自知。
昏昏然中,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知道许多权益是人与生俱来就该有的,而绝不是什么“领袖”恩赐的;乃至受到伤害而浑然不觉,偶得小恩小惠就欢天喜地感恩戴德。 (文源自谁能横刀立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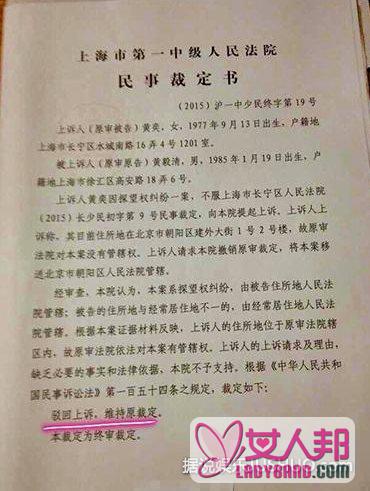




![>吴若甫被绑架案始末 吴若甫绑架案的王立华]吴若甫被绑架案始末](https://pic.bilezu.com/upload/b/3d/b3d0e60c2436919070b4699ebf9c8d8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