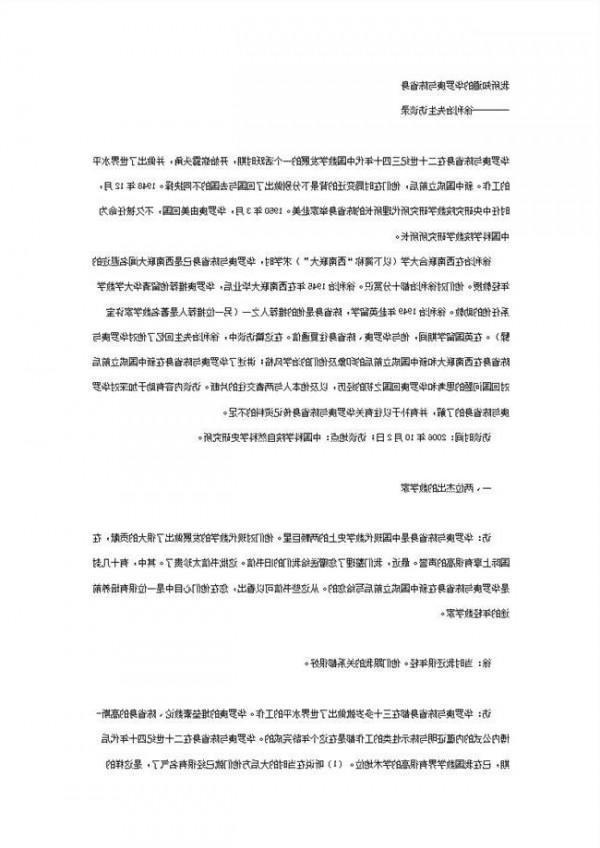阎长贵:我所知道的关锋(上)
关锋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他就是小组成员,1967年1月又兼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然而,1967年8月30日,他就以所谓“乱军”即“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和王力一起被打倒了。
关被打倒也牵涉到我,我所在的单位红旗杂志社以及有关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等也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内容之一是:“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
”“强烈要求揪出埋在江青同志身边的定时炸弹!”我当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我把有关这些大字报的材料拿给江青看(我不能不拿给她看,也不敢不拿给她看),她看后郑重地说:“跟关锋在一起的不一定都是坏人,都是反革命!”江青这样说,表明对我还信任。不仅如此,不久,她还提议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一点不错,我确实是关的学生。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哲史。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关锋。
“文革”前的关锋:开始引起毛的注意
关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他从1950年代起,在哲学界特别是中哲史界,就是有相当名气的人物。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
1950年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行政十级。1956年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借调北京,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思想动态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关调任《红旗》杂志编委,但他除了参加编委会议,给《红旗》写些文章,不做具体编务,专做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哲史研究。
关在1950年代开始发表著作,如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196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更重要的著作: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30万字),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求学集》,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哲学论集》(关锋、林聿时合著),等等。
从1950年代后期起,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三人以“撒仁兴”(即“三人行”)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名噪一时。
关的文章和观点深得毛泽东赏识。我听关说,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提出“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必须 “学习毛泽东思想”,受到毛赞扬,还有批语。
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简称《毛泽东文稿》)第9册出版后,我告诉他:上面载有毛对他《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他说知道,又说,他更看重毛对他写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的批语,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文稿》没有收录。
毛为什么喜欢关的这篇文章?我想原因不是别的,也许是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之后,关在这篇文章中又明确提出 “毛泽东思想”,指出哲学史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
需要指出,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据毛的多次要求和指示做的。1961年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关以何明的笔名发表《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月15日,毛批示:“好文章。”并致信陈伯达,全文如下(见《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陈伯达同志:
何明是谁?1957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可能指《光明日报》1957年8月10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来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晨
为了一篇文章,让作者坐飞机去谈,还要数位专家、秀才陪同,足见毛对关文章的偏爱。
毛批示何明(即关锋,毛此时尚不知何明即关锋)的《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为“好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文稿》的注释如下:该文说,“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先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带着框框下去,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看到、听到自己所要看、所要听的情况,把事情看走了样子。
虚心是非常要紧的;框框,是害人害事的。可是,指导原则和框框却是两回事”。文章联系中国哲学史上宋尹学派和荀子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去进行调查研究。
这不是框框。这是从实际抽出来而又经过实际证明了的真理,是‘望远镜’,是‘显微镜’,是解剖‘麻雀’的解剖刀。
但话还得说回来,不要只是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往客观事物头上硬套,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说,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而是自己造的框框。”“框框乎?指导原则乎?要分清;不要带着框框而要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去进行调查研究。”
毛从1957年起多次召见关——当然都是和召见别人一起,单独召见关我还没听说过,也可能没有;即使和别人一起被毛召见,在当时也是“殊荣”。我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11月21日,毛在杭州召见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关锋,说是要提倡读马、恩、列的著作, 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每本书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
(参见胡绳回忆文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龚育之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毛叫几位秀才每人负责给一本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等)写序言和注释。
关领的任务是给《哲学笔记》写序言和注释。他回京后,我们组的人就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后来由于“文革”的开展,这项任务没有继续下去。
从上面几件事情看,毛对关是很欣赏和重视的。其主要和根本原因,我认为,就是关紧跟毛的思想和行动。如在“反右派”斗争中,关积极配合写了多篇文章(如上所说,有的文章还受到毛的称赞,甚至“想找他谈谈”),并辑成《边鼓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在毛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关立即写了《雷锋是怎样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客观地说,关那一时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贯彻和实践党内正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请冯友兰作报告,还要请关锋作“消毒报告”
关锋在“文革”前和冯友兰先生的论战,是最值得注意和记载的事情。
冯在旧中国、新中国都是哲学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冯任北大哲学系教授。1956年11月中旬,人大哲学系为了活跃学生学习生活,也为了开展百家争鸣,请冯作学术报告。冯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
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
”(冯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吴传启把冯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意见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关认为这个概括“符合冯意见的本质”,冯本人也认同这个说法。(参见《哲学研究》1958年第2、3、5期吴、关、冯的文章)
关写了很多批判冯“抽象继承法”(及其哲学观点)的文章,认为冯的“抽象继承法”是在古代哲学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近、相同或没有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是哲学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等等。在私下,关还说过冯的“抽象继承法”名义上是找“好东西”,实际上是“捡破烂”。
与之对立,关提出所谓“扬弃三法”:一是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继承其一般意义;二是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一重意义,继承其另一重意义;三是否定命题的整体意义,继承其某些个别要素。
关文章中有不少牵强附会和扣帽子的东西,但总的说来,他还是提倡和注重说理的。据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
关和冯针锋相对,阵线分明。在当时,冯被视为资产阶级教授,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各代表资产阶级一家和无产阶级一家。经常有这样的怪现象:哪个单位请冯作报告,还要请关再去作“消毒”报告——这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反映。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两家”,在关和冯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在关和冯的争鸣中,关处于主导方面,冯处于被批判地位。我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有四个搞中国哲学史的人,一个名叫汤一介(时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现为著名哲学家),一个名叫孙长江(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哲史教师,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文章的重要作者之一,现为学界名人),一个名叫方克立(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哲史教师,现为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一个名叫庄卬(北大1955级哲学系学生,时为冯的研究生,仿佛不到30岁就去世了。
现在健在的三人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四位以司马文的笔名写了不少批判冯和中哲史的文章,当时他们常来请教关锋,或切磋问题,有时我也在场。这个情况表明了关当时在中哲史界(以及哲学界)的影响。
冯“抽象继承法”的观点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究竟如何?先不说这个观点正确不正确,根据科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原则,冯提出这个文化遗产继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贡献。应该说,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
再说这个观点本身。我作为关锋的学生,完全接受了他的观点,在文章中也批判过冯的“抽象继承法”;经过多年思考,现在我感到,冯的观点要比关的观点正确(关所谓“扬弃三法”,就其正确方面的意义,冯的“抽象继承法”是内在地包含了的)。
遗产继承是解决现代和古代的关系即联系问题,即今天和昨天以及前天、大前天……的关系和联系问题,很复杂,若没“抽象”(指科学抽象)如何联系?“新陈代谢”是自然过程,“推陈出新”是人类行为。
忠、孝、仁、义,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毛泽东也承认忠、孝、仁、义。他说:“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转引自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201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资中筠同志在讲到冯的“抽象继承法”时说:“冯友兰先生的道德抽象继承……我特别拥护这一点。因为我想不出来传统和现代怎么样连接起来,我觉得冯先生概括得非常好……怎么样把传统的道德和新的时代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一个道德抽象继承。
比如说过去是忠君,忠总是好的,背叛总是坏的,你现在忠于国家也好,忠于职守也好,这是一个品质,类似这样一些都可以添进去,我觉得这是造了一条道路。但是后来他被批判……这样一来我们什么传统都坏了,外面的也不要,传统的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人类文明是几千年也好,一百年也好,多少年的文明就断掉了……”(资中筠2012年1月8日在“理想国文化沙龙”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