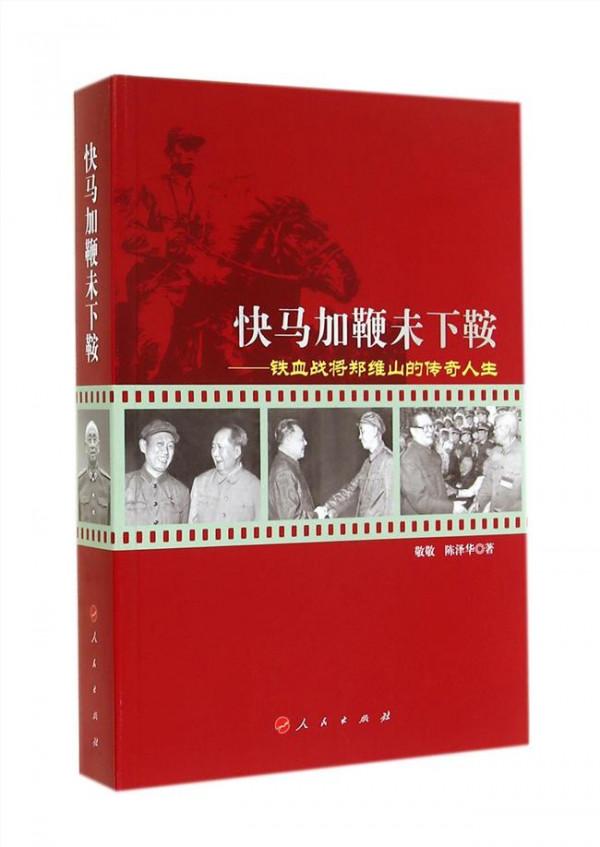严恺与严复 【学人风采】严恺:传奇人生 与水相伴
严恺曾当选“新中国60年江苏教育最有影响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和江苏省“十大杰出科技人物”。作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国际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新中国水利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从事水利事业近70年的他一生闪亮多彩,事迹感人。
在荷兰,有一个世界之最——能够抵御4000年一遇特大风暴的东斯赫耳特防风暴大闸。大闸由62座巨墩支撑,为表明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尊重,这些巨墩,全部用世界上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其中有一个属于东方科学巨星,名字叫严恺。
1986年10月,荷兰海牙国际机场,严恺享受到荷兰人迎接国家元首的礼仪,他这次来是参加一项特殊的典礼。与严恺同时参加典礼的贵宾中,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比利时国王等。这是筑坝王国为中国科学家树立的一座丰碑,而严恺此行的目的就是应邀出席大闸的落成典礼。
2000年6月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为了配合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大会,播出了院士专访系列节目,第一位推出的就是两院院士严恺。在“东方之子”节目中,严恺感慨中国的水利史开始之早,同时也对我们今天把“水利”一词理解得太窄深感忧虑。他说:“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水利这个词很好的,外国是没有的。水利不仅仅是工程的问题,而且是对水资源的利用。”
2006年5月13日,在享年94岁的严恺遗体告别仪式上,1400多人前来吊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哀悼并送了花圈。严恺不仅对科学孜孜于求,对人生亦精益求精。
训江治海 功勋卓著
钱塘江海塘是我国古代与长城、运河齐名的三大土建工程之一。自吴越时起,两千多年以来,就处于一个不断修建不断崩塌再不断修建的过程,一直没有根治。上世纪四十年代,严恺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港工讲座期间,钱江海塘北岸海堤被大潮冲垮,他突破传统的立壁式海塘模式,设计出新型的斜坡式海塘,与海潮“软对抗”,消解了大潮对海堤的冲击力,抗涌潮效果极佳。
严恺的创造精神创造了奇迹,斜坡式海堤更为牢固,这道海堤至今还屹立在杭州湾北岸。
后来,斜坡式海堤在东南沿海又被广泛采用。六十年代,我国东南沿海不断遭受台风浪、风暴潮、天文潮等严重灾害。福建沿海数十公里海堤在大台风中坍塌,严恺受水利电力部委托,率领专家工作组直奔受灾现场。经过一番风口浪尖的缜密调研,他把钱塘的经验运用到这里,两次设计斜坡式海堤。
当地一位领导从没看见过这种斜坡式的海堤,很不以为然,打赌说:“这要是能抵挡海潮,我把脑袋输给他。”最后,专家组通过设计,修起了斜坡式海堤。事实证明,这种海堤不仅能够挡住大潮,而且有效地减轻了潮水对海堤的冲击力,原来海水飞溅堤内,造成几百米土地盐碱成灾的情况也没有了。当然,那位打赌的同志的头还是安然无恙。
五十年代开始,严恺受命领衔世界上水域面积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新港回淤问题研究。1951年8月25日,中国科学院一份急电发往上海交通大学严恺处:“我院聘先生为专门委员,并请代表我院为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
政务院已通过,即请俯允电复为祷。”接到电报,严恺立刻复电:同意担任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至此,严恺参加了新港的恢复、改建和扩建工程。这是一个国家重点及中苏合作的研究项目,严恺和同事们一边调查勘察,一边测绘、记录,逐步建立起港口及周围海域的气象、水文、地质地貌等一整套珍贵资料,受到当时苏联专家的好评。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到六十年代,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恺成功提出了解决港口回淤问题的方案,不仅为新港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还进一步提出了开展淤泥质海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淤泥质海岸的研究工作,使我国在此方面的科学技术居于国际先进地位。
七十年代,当时国内最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严老担任工程技术委员会顾问。1973年,为解决葛洲坝水利工程中的复杂难题,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他率“中国水利考察组”到美国进行了为期八周的技术考察,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微妙阶段,严恺率领的代表团在美国既受到热烈欢迎,又备受瞩目,所到之处,新闻记者穷追不舍。
严恺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地回答记者的各类问题,一时成为新闻人物。1981年,当葛洲坝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给严老发专函致谢。
昂首矗立的葛洲坝,成了年轻的共和国雕塑于长江之上的一大景观。然而,葛洲坝工程不过是三峡配套工程中的一环。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在三峡建坝的美好设想。
毛泽东主席也曾描绘:“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1958年起,严恺就一直参加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论证工作,极力主张这项工程早日实施。
1983年由严恺起草的第一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报告》提交国务院。对于三峡工程,严恺着急,三峡工程成了他有生之年未竟之业中梦绕魂牵的最重要一项。他参加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全过程,是工程上马的积极支持派。
1992年9、10月间,严恺凭借他在国际水利界的威望,再次访美,介绍长江三峡工程,为消除误解奔走呼号,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他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顾问,继续为工程建设作贡献。
八十年代,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我国的海洋资源,从1980年开始,在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上对全国海岸带及海涂资源进行了规模空前浩大的综合调查。严恺被国务院任命为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兼技术指导组组长。调查组由24名专家组成,这次调查历时8年,参加人数过万,严恺的足迹踏遍了海疆,而且身先士卒,披肝沥胆,主持审查各省市自治区的调查报告,一丝不苟。
1990年,他主持的《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通过了审查,这份由他主编的报告由海洋出版社于1991年1月出版,1992年11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1996年他获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1年获中国水利功勋奖。
九十年代以后,耄耋之年的严恺仍情牵水利。坚持教学,笔耕不辍。为适应我国沿海经济开发事业的需要,1992年10月他主编的《中国海岸工程》由河海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96年6月,他主编的《海港工程》由海洋出版社正式出版,2001年8月,他主编的《海岸工程》由海洋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棵真正的大树,在科学的地平线上,他根深叶茂,高大葱郁。
传奇人生闪亮多彩
1912年8月10日,严恺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福建闽侯。父亲严文炳在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任数学教授,其本家伯父是清末大名鼎鼎的学者严复。可严恺在这个书香门第好景并不久长:7岁丧父,11岁又失去母亲,靠着在宁波铁路部门任工程师的二哥严铁生提供经济支持,他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幼年的不幸培养了严恺自强自立的倔强性格。他小学时就聪慧过人,小学未上完就跳至中学,而6年的中学课程又仅用4年时间就学完了,以高二学生的身份考入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
1935年,他在大学毕业并经过2年实际工作锻炼后,报考了中央研究院选派到荷兰的留学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上世纪30年代赴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攻读土木专业的第一个中国人。
1938年12月,严恺从欧洲回到了祖国,在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任工程师,从此,严恺怀着巨大的爱国热忱,为我国水利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1940年,不到28岁的严恺就被中央大学水利系聘为教授。1945年3月,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宁夏工程总队总队长,率领近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对宁夏地区黄河流域进行综合的地形和水文测量,提出整个灌区的改建和发展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严恺除担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水利厅厅长外,还在1952年筹建了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校——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草创时期,千头万绪,他以巨大的热情、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始了华东水利学院的建校历程,他首抓的是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的华水,建校时期办公地址拟设于南京大学内,建校初期仅有16名教授,5名副教授,8名讲师,17名助教。为了给他们创造教学、科研、生活条件,严恺咬牙一次买下了20幢花园洋房。
严恺不辞劳苦地劝说和努力,终于为新生的华东水利学院“挖”来了一支水利教育的精英之队。在他的影响和感召下,著名力学家,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徐芝纶教授等一批国内顶尖学者都来到了华东水利学院。他还为该校亲定了“十六字”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
曾长期与严恺共事,担任过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院士说:“与严老的交往中,我深深体会到他那‘严’字当头的特点。在1956年以前,他并非中共党员,但在讨论华东水利学院工作时,他对党员干部以至党委书记提意见,都是直言不讳,从无顾虑。
以后我虽不兼任院长,由严老担任这一职务,但他每次来京,必电话告我,或在办公室或在我的家里,他对工作,对我个人以至对国家大事有什么意见,都是坦诚相告。有时候,他推开办公室门,坐下来就提意见。
全国水利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也随时向他请教。几十年来,水利建设的一些重大决策,如江河治理、葛洲坝建设、三峡论证以及水利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等,他都认真负责地参与研究。他提的意见,都是从大局出发,经过深入思考的,明确中肯,使我受益匪浅,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位师长和知交。”
河海大学原水港系主任薛鸿超教授是严恺的学生,对他而言,严老既是恩师,又是挚友。回忆起严老的点点滴滴,他感慨万分,不是自己研究领域或不熟悉的问题,他是绝对不会乱加评论的。在搞工程时,他要求所有人对工程上的发言和表达,一定要严谨,不懂的绝不能乱讲,懂的也要讲得慎重,因为如果不仔细谨慎,就会出乱子。
曾经有个别人,对一些不是自己专业、不精通的领域乱说,都会遭到他毫不客气的一顿批评。2000年以后,严老开始谢绝发表任何关于学术上的评论,因为他始终觉得做学问必须保持严谨,而自己年纪大了,判断力也不够。
严恺秘书回忆道。严恺去北京开会,如果是乘火车,他总是叮咛买66次车票,如果工作人员买了其他车次的票,他会发脾气。后来工作人员在一次党员民主生活会上向他提意见,严恺认真听取了批评,并检讨自己发脾气的错误后说:“我这一把年纪了,再也浪费不起时间了。
66次火车从南京到北京是晚间运行,这样我上车那天照样可以干手头的工作,上车后睡一觉,第二天到北京又可以办不少事。”严恺一贯以守时著称,可自己用的却是一只老怀表,每次会议开始,严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怀表从身上取下,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以便严格掌握时间。
这块怀表是30年代在欧洲留学时买的。秘书建议他买块手表,使用起来可能方便些。严恺说,这块瑞士产名表走得非常准,怎能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