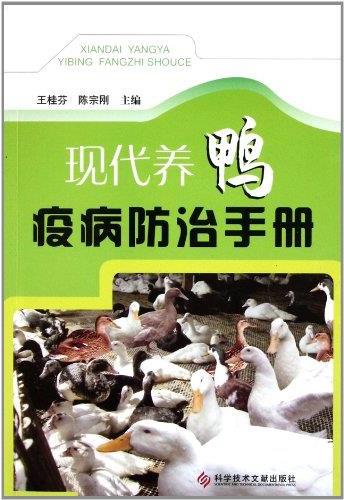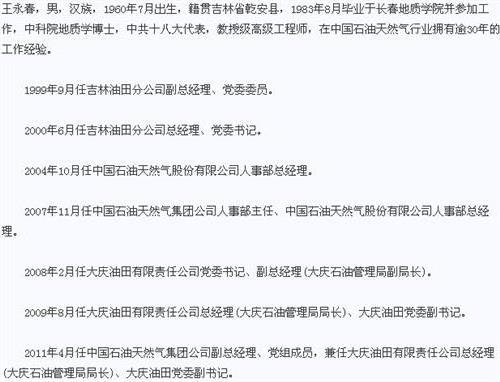王小妮简历 王小妮:相对历史书 细微的真实更可靠
1966年,王小妮11岁,这是一个孩子慢慢开始对世界形成认知的年龄,而她外部的中国正步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王小妮说那一年她“看见很多,听见很多”,1998年到1999年她为这一年写下11个短篇小说,今年这些小说首次结集出版,名字就叫《1966年》。
王小妮笔下的1966年没有残酷和控诉,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两个乡下姑娘为进城看场电影做了精心准备,到了城里却发现因为闹革命,影院早已用做他用;再比如《火车头》,一个孤独的男孩,他的父母被带走,哥哥去北京串联,他整天在火车铁轨上闲逛,受冻挨饿,在一个雪夜他突发奇想在家里的墙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但却不知道正是在这个雪夜,他的爸爸去世了。
但就是在这样平静的笔调下,你不经意间就能感某种刺痛,感到那一年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孤独和困惑、惊恐,感到每个人命运中都潜藏着的让人无奈的戏剧性。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别样的1966年,既陌生又熟悉。
在《1966年》的前言中,王小妮写道:“希望这11个故事能留记那一年人世间的最末梢,并依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
谈《1966年》 没有想过介入,只是呈现
新京报:能先谈谈你的1966年吗?
王小妮:1966年,忽然不上学了。临街的楼房被大纸覆盖,风吹纸响。写满字的带红叉和一串惊叹号越来越大的大字报从三层楼直垂下来,很多人围看,还边看边记,从来没见过的热闹。街头解放牌卡车派“号外”,撒传单,有满是字的,有漫画,丑化了的刘少奇有大红头的鼻子,还布满黑点,没少照着临摹。
见到过从一间阴暗屋子里拉出一个平躺着的人,最先出来一双瘦的赤脚,周围人都在小声说自杀。听说有人从报社楼上往斯大林大街上跳(现在改成人民大街),没死,脑袋缩进了胸腔。
刚开始记日记,被父亲搜到,被再三叮嘱:不能记日记,改掉拿着笔随手乱记乱画的毛病,特别是不能在有大幅照片的报纸背后写字,时隔27年,直到1993年才开始记日记。
上面只是临时想到的,更多细节都在淡忘中。
新京报:《1966年》中的11个小说描述的都是动荡一年中非常日常的生活,这是你希望自己的小说介入历史、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吗?
王小妮:无论历史或现实,日常才是基础,包括我的文字和平时的阅读,都更喜欢沉实平淡的。从没想过介入,只是呈现,我们无力介入。
新京报:你以前接受采访曾说自己的作品中描述针刺的常有,涉及真正刀伤的好像几乎没有,《1966》的写作也是如此,为什么你的写作选择避免刀伤,避免这种冲突?
王小妮:没有有意避免,我的关注和兴趣就在那儿。对于非黑即白和直截了当,有天然的抵触和抗拒。
新京报:你也说过写作中注定有些东西是要沉下去的,《1966年》你选择沉下去的是什么?
王小妮:显现在最表面的,又容易又不费力气能接触到的自然是历史课本,我刚看到一个版本的中学课本,1966到1976的十年,不到十行字,涉及那个年代的图书非常少,少到不合乎一般常识了。
而真正能充实和支持史实的恰恰是那些琐细的部分,包括心理的部分,它不容易被抽离被总结概括,更快更轻易被忽略掉,像细沙注满了缝隙,这才是最可能还原出血肉的部分。虽然历史不可能完全还原,相对历史书,细微的真实更可靠。
而真正能充实和支持史实的恰恰是那些琐细的部分,包括心理的部分,它不容易被抽离被总结概括,更快更轻易被忽略掉,像细沙注满了缝隙,这才是最可能还原出血肉的部分。
谈创作 小说更需要理性,诗更随性
新京报:你说不喜欢在小说中追求故事,能谈谈你理想的小说写作的样态吗?你希望小说体现的是什么?
王小妮:讲故事只是一部分叙事的终点,不是所有人都追求这个。你说到体现,我喜欢的小说里,可能比“说故事”更可怕的是要“体现”。
有各种各样的叙事,我想把读者直接带进来,试试可触碰、可感知、可跟进的滋味动作和态势,更愿意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地方找到事儿,每个人的兴趣点不同吧。
当然,这也涉及比写作还要大或者广阔的判断,我们本身身处在一串偶然中,本没有必然,也就没有固定的故事和所谓的故事的必然走向和结局,永远无力、永远攒劲、永远懵懂,本身就是这样,幻想握有控制力是因为没可能获得它。
新京报:写作小说与写作诗歌,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王小妮:两个完全不同的文体,语言不同,构建方式和节奏不同,小说会舒缓松弛些。平时,它们在脑子里都只是一闪而过的碎片,有些记下来,有些忘掉。但小说更需要理性,要清楚它的构造,诗更随性,诗更没有预知的走向。
新京报:有没有哪些小说对你产生过影响?
王小妮: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吧。好些年不翻小说,上世纪80年代初,大量的翻译作品涌进来,那时候读得多一些。渐渐对翻译有了怀疑,渐渐读得少。
谈历史与现实 对于历史或现实,角度尽量多元
新京报:你在《上课记》里曾写,“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自愿又快乐地参与到对现实的‘建设’中”,但我感觉你关注社会,也不反对写作介入历史与现实,这两者该如何平衡?
王小妮:我一直是旁观和被动的,看看身边的人,有多少是热忱和主动地投身给它,谁能持续地拿性命去投入其中?我们多需要好好看蓝天上跑得飞快的云彩,看看刚要开的花。
我只是做了一个还有知觉的人所能做的。那些东西挑衅一样在找你,用它的刺扎你,你能把你经历过的忘得一干二净?能对电脑一角忽然闪跳出来的“突发事件”框全没知觉?除非你有意逃避,装聋作哑。
曾经我发一条微博说写写1966,有人转发问:为什么是1966,六六大顺吗?这种天真的询问让我愣了一下,后来问了,是个初一学生,初一的历史还没讲到这一节,家里的大人考虑到负面事物对孩子的影响,始终没讲过1966,所以,1966这串数字对于一个少年就剩了六六大顺。好在,当天下午,这学生就问了家人,一下子知道了那一年里的很多事,因为长辈们没忘记,只是没有对少年说。
新京报:《上课记2》中你曾发问“孩子不应该由长辈温和地牵引着去认识这个世界吗?”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保持宽容的同时看待那段历史,或者正在发生的不公平的现实,究竟应该如何区分善与恶?
王小妮: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具体事件都有它自己的个性,我关心的常常是这个性本身,它可能潜在的那些心理的,可能被一掠而过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说,它常常是简单的善或恶不可能涵盖的。善或恶都不可能单独孤立的存在,我对它们的复杂性有兴趣,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对事物的判断不是简单到非善即恶。
对于历史或现实,我的角度主要不是怎样宽容,而是尽量多元,也试图把这样的角度介绍给学生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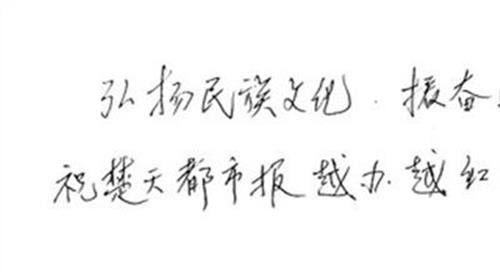
![王文清简历 王文清[化学家]](https://pic.bilezu.com/upload/1/81/1815965e7fb9297e5baa73dccf0ef03c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