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简介 王小妮:一个简单而又繁复的故事
我实在惊讶我们曾经年轻。 当初,我们与简繁一圈一圈绕着南国边城的街巷,彻夜高谈阔论时,很少去留意头上笼罩着凌晨四时苍茫沉寂的夜空。
现在,我们都"老"了,当不久前激昂慷慨的简繁再次走进我们房门时,我竟然感到了突然而至的苍茫沉寂。它原来这么切近,谁能无视这种生活对人的冷却与雕造! 每一个人都无法度量他自身品尝过的艰辛苦涩。
从一个在街头拾食西瓜皮的孩子,到成为中国一流艺术大师刘海粟的研究生、助手,简繁所经历的就更加繁复沉重。 记得有一个大雨滂沱的白天,他来敲我们家的门,二话没说就要酒喝。
于是徐敬亚就与他喝酒(火辣辣的高粱酒他喝了七、八两),我们就谈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突然,他话锋一转,谈到李清照。他说《声声慢》的开头十四个字太惨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人还能活下去吗?"简繁平日嗜酒,而且每喝必醉,但那次他醉得最凶。
他匍匐着,笑了又哭,哭了又笑,"他妈的,我不能凄惨完了还戚戚!" …… 如果,阻止历史也是可能的,阻止人淤积内心的阴郁却永无先例。
所以,一个曾经在安徽听过简繁为未来文学院的学员们即兴讲课的女孩子写信说,简繁像一团雾。
作为真诚于艺术的艺术家,在简繁身上,内心的迷惘与清澈是那么繁杂地交错在一起。 他在浙江美术学院进修时,由于品学兼优,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动员他报考本系研究生。
考试在即,他意外得知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先生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马上要求转考。当天,他就办理了转考手续,从杭州赶到了南京。
明澈,源于他对艺术的坚韧执着。 考取了刘海粟先生的研究生,简繁当即声称:"我要让海老为我这个唯一的研究生感到自豪。
"从此,他躲避了所有的展览、发表和征稿,放弃了显露的机会与社会应酬,把自己伏在画室的案头上,伏在书卷笔墨之中。 三年之后,当简繁站在南艺空旷的展厅里,准备第二天论文答辩前的画展时,当简繁面对一百多幅已经悬挂其间的作品时,当灯熄了,蜡烛完了,夜色默然逝去时,他一个人,和衣而立,他再一次品尝到的是什么?作为他多年的朋友,我说不清楚,作为他自己,我想他也说不清楚,这恐怕就是那个女孩子所讲的一团雾。
一团萦绕着恢宏崇高的形而上的迷墙的雾。 简繁的毕业论文和毕业画展在校内外获得了震动性的反响。
导师刘海粟教授看画展之后异常激动,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画了",他评价"简繁才气过人,画中充满了力量,他日不可量也",并断言"简繁有可能成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大师。
"画展之后,简繁成了刘海粟逢人便谈的话题。后生可畏,老人确确实实对这个年轻人生发了由衷的自豪。 论文答辩和毕业画展的成功,改变了简繁既定的生活道路。
学校根据刘海粟教授执意的提议和坚持,否决了简繁要求去新疆乌鲁木齐的毕业分配志愿,安排他留校任教,并作海粟老人的助手,环绕着他的开始是"辉煌"的灵光。 但是,简繁在生活的这一刻中又沦入了他特有的明澈。
他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别人(即便是伟人)的影子,从此他将面对的可能是光芒间的争斗,可能是对自身追求的严酷背叛。 变迁激荡着简繁命运中注定不谐和基调。
终于有一天,他离开了海老,离开了南艺,离开了可能使他慢慢地也能瞻望到的"辉煌",他只身来到了深圳。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且谈且喝,且醉且醒,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去得好像十分轻松,十分潇洒,十分孤傲,但我不敢说他的内心是平静的。
海粟老人在他们师生合影的照片上题过这样的诗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都是莫测的。 人类的悲剧与生即来,逃避它与接近它都不在选择之列。
这之后,两年的时间里,在朋友传言中的简繁被灾难包围着:妻子和学生背叛了他,兄弟决裂,好友反目,……当我们想安慰他时,却听说他去了普陀山。
醉酒如常,谈笑如常,匍匐于命运之中也如常。坐避佛山与紧闭门户,像当年论文答辩、徘徊于辉煌灵光之中一样,简繁仍旧没有能力平复内心的繁复交错。
这之后又是三年,他曾三去佛山,深入简出,潜心在自我的繁复世界当中,三年的时间里,他潜心作画数千幅,却从不示人。绘画从实质的意义上融入了他日渐明澈的生命意识之中,是非得失远离了他,宗教般地面对一幅白纸的执着占据了他的内心世界。
三去佛山,他欲求却不得的解脱原来只是潜行在这平白无皱的宣纸之上。 三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南方这个最不安分、最不宁静的都市里,简繁把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局限在一间并不宽敞的陋室里,他的天地已经成了形而上的广阔境域。
三年间,简繁的画风几经变易,他的画,荒寒、博大,深沉中表现了他的自我生命形态,超乎物象,超乎时空,是生命和存在的最深神秘,是从宇宙生命最深之渊发出的孤独而灿烂的光。
简繁走近来时,一切都和当年一样,但是那浸人的苍茫沉寂感,使人知道他付出了有生以来最为昂贵的代价,终得顿悟。
他走近来时,我是那么非个人性地酸楚。 简繁远离的东西太多了。他的离开曾使刘海粟先生的心头蒙上一层惆怅,当老人九十三岁时,十上黄山,捎信要他同去。
一见面,老人就激动地叫起来:"你这几年过得好吗?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有才情的,我对你寄有厚望啊!"历尽沧桑的老人的谈吐该是发自内心的。简繁站在老人的对面,在外人看来他谈话仍旧境若当年。
"他日当独执中国画坛之牛耳也未可量也",对刘海粟先生的这一评价他也一笑置之。 不久,他将暂时走出他的陋室,有一个友人资助他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虽然,几乎与此同时,刘海粟先生曾推荐他去日本深造,他还是坚持了自己自信又固执的选择。对于一个真诚的人,抉择没有正误之分,对于艺术家,路没有坎坷、平坦之分。不过,远去天涯海角,他也还是那个在南国边城中深夜兜圈子的简繁。简繁战胜不了迷墙,但他可以作为永不散去的雾。 (载于1990年11月香港《当代艺术家》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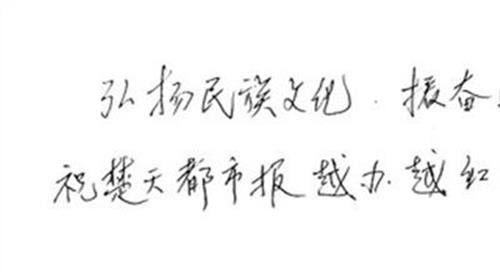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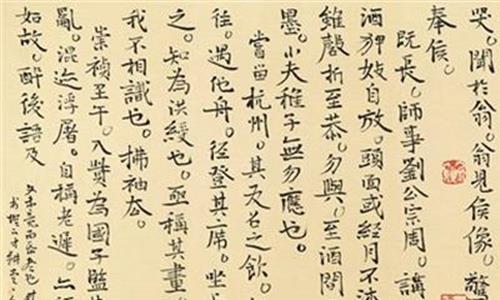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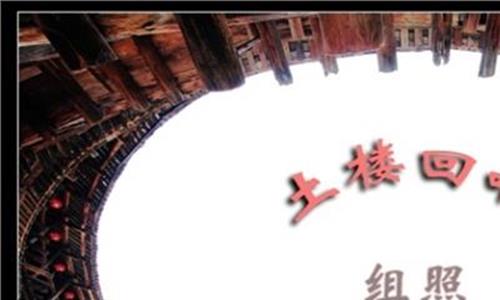
![>王若飞简介 王若飞[“四八”烈士]](https://pic.bilezu.com/upload/1/19/11979035b2120e5735fe2b2ccbb0e47b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