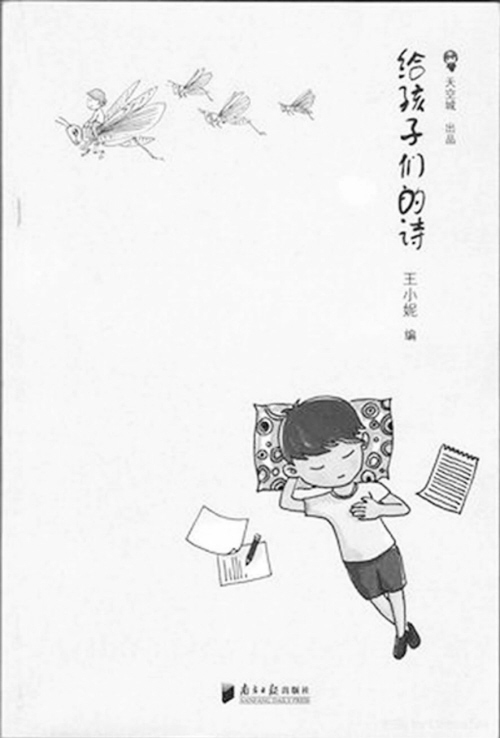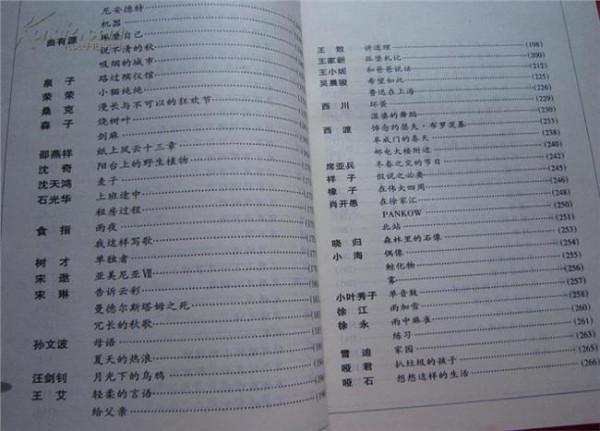王小妮古诗词 王小妮 | 上课也是写诗
这依旧是一篇旧稿,距离采访王小妮已经过去了3年,但下了地铁徘徊在小区门口等她接我的情景却没有模糊。深圳对我来说是座烙有个人印记的城市,当我初出校门的时候。但此后一直到关注王小妮,我再没有与这座城市发生任何联系。
王小妮是起势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人,可由于年龄的跨度我并不熟悉她的诗作,或者说我接近文字的通道并不是诗。当出版社的编辑将《上课记》交给我后,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并对这个怀有诗意的老师产生了兴趣。
4月的深圳草木**,王小妮一身麻布衣裤飘然而至。她告诉我儿子一考上北京的大学她便立刻卖掉了市中心的房子搬到这里,图个清静。可叹穿行在小区里时,身边不时就晃过一个手握大扬声器听戏曲的大爷,王小妮摇摇头。
怨不得书里的孩子说愿意把心里所有的话都说给她听,聊完了正题,我们便一起踱到她家超大的露台上,站在花花草草中间,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孩子。
露台下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已经将它挤挤挨挨的枝叶几乎伸了过来,空气中弥漫着什么东西正在悄悄生发的气息。那一刻我几乎忘了来这个城市是为了什么,也在心底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什么也不要行动,不要搅动过去。
希望当自己也了无牵挂的时候,做一个毫不多虑的决定,就像王小妮一样。
王小妮从来没预想过自己会在一所海岛大学当了老师。大学时代的她是个不怎么亲近老师的学生,遇到不喜欢的科目就毫不犹豫地逃课。做了母亲,对儿子从小到大的老师,她也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虽然她也曾有感而发,以一篇《把孩子交出去》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一些思索,不过,孩子转眼**,她和老师、教育,似乎再也不会有什么瓜葛。
2005年8月,王小妮第一次站上了大学的讲台。决定做得很痛快。这所海岛大学发起了一个诗歌研究中心,旨在汇集一批诗人从事相关的工作,发起人正是王小妮多年的友人。十多年都处于自由写作的状态,王小妮完全不知道学校是如何运作的,但几年前和一帮大学同学环海南岛的自驾游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天总是蓝的,白云滚滚,天高地远,一片原始风光。后视镜里都看不到其他车,广东已经开始塞车了。反正孩子也不在身边,两个人去就去吧。”对于即将当一名老师,王小妮没想太多,由于并不是作为教学人员过去的,在她的理解里就是一个学期开几次象征性的讲座,应该很简单。
用王小妮的形容,这是一所“既不悠久也无名气”的偏远大学,刚入岛时卖她空调的小伙子就毕业于此。因曾在电影制片厂干过多年的剧本编辑,学校安排王小妮去刚成立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影视写作。开始一周上两次课,后来学校高层人事变动,课程增加到一周4次,除了写作课,还要给中文专业的讲诗歌,她被正式纳入了一个教育机构的体系。
第一次站上讲台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面对一群全新的面孔,那种彼此之间的陌生与隔阂至今让王小妮难以忘怀。“我不知道对方究竟在想什么,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于是她像自己做学生时看到的老师一样,站在那儿就讲,讲完就走。她认为自己就是个老师,是要教给坐在下面的他们一些什么的。
或许是出于诗人的敏感,很快王小妮就察觉到了如此当老师的乏味。“其实学生和你同样的细腻,只是你能不能唤起他们的细腻。你像木头似的讲,他们也就像木头似的听。”她开始摸索如何能讲得更好的方式,像写文章一样不断地进行调整,上课的四个月里几乎放弃了全部的个人创作。同时她也慢慢转换施教者的角色,仔细倾听来自讲台下的声音。
她相信人心总是能焐热的,更何况是孩子。她发现最初的隔膜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她能异常敏锐地接收到来自对面的信息。“去年我的学生一共将近400个,我不能全认识,但我能感觉到在哪个教室最后排的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他听进去了。
后来别人告诉我他是谁,我一想,对,我收到过他的邮件。这些都是好奇怪的事,有多少注意的眼神,听到什么程度,我立刻都会知道。到最后我去上课就像回家一样,说什么都可以,可以进可以出,很舒服的状态。”
下了课总会有学生跑到自己跟前问点什么。11月,海南的天气也有些凉了,来自北方的学生会趴在讲台上对王小妮说:“老师呀,家里都下雪了,我好想家呀。”有一些学生永远和老师保持那么一点距离,就像当年的自己,还有一些学生渴望亲近老师,想对一个长者说说心里的事。王小妮认真地去听任何一个自愿道来的故事,忽然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喜欢孩子。她问丈夫:“我怎么这么怪呢?我怎么一进教室看见他们就想笑呢?”
年末,学生们穿上厚衣服排大队买回家的车票。王小妮的课只有一个学期,第二年她将不再是这些学生的老师。望着手里留下的快要翻破的学生名单,想到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就要这样切断了,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故事也随即淡忘,她觉得有点可惜,也有点心疼。
第一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从2006年起,王小妮开始随手记录下和学生们相处时的发现,也因为这些记录,让她对这些年轻人投去了更多的关注。
王小妮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乡村,大部分是女孩。从第一堂课开始,她就深刻感受到了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虽然学的是影视专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却从没进过电影院。
为了让这些分不清电影和电视剧区别的年轻人写出生动的亲身经历,王小妮持续几年进行了一项小小的调查。在2006级的学生里,当问到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城以下的村镇时,20多人举起了手,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再问读书费用依靠父母种田维持的,大约10人举手。
事后一个班干部告诉王小妮,其实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只有11人,其余的都靠父母种田或打工交学费。
“每顿能吃肉的和一星期吃两顿肉的不一样,晚上能去街边吃小摊的和不能去吃小摊的也不一样,还有期末能订飞机票和订火车票的更不一样。如果谁说我买飞机票了,其他人心里就咯噔一下,也会有人说出来有什么可炫耀的,不就是飞了吗?”
在王小妮的眼里,他们朴实、敏感、不自信。因为太底层了所以自卑挥之不去。2011年最后一个学期结束前,一个大四女生给王小妮送来一个笔记本。本子是在校内的小超市里买的,女生就着超市的柜台用前两页给王小妮写了一封信。对她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第二年6月她即将毕业。
“记得大一的时候你让每个同学写个小纸条,自己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我没有写,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来自农村,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书,因为从前我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除了课本以外的书。我当时对您是抗拒的,不想让您注意到我,但上了您两个学期的课之后,我产生了想接近您的想法,非常想了解您,因为我觉得您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像老师的老师,最像母亲的老师。
您对待学生是那么亲切,让人一点都不怕您,反而更想接近您,想把自己的事说给您听。我跟您有特殊的交集也就两次,一次是我给您发了一条长达几百字的短信,一次是您和几位老师去吃饭,我竟然作为服务生出现在那次饭局上,这都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在王小妮的记忆里,这是个沉默、不起眼的女生,和母亲的感情非常疏远,但直到此刻她才得知女生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曾经的知青生活让王小妮对土地一直充满了情感,但于他们心中,来自土地的身份并不那么值得骄傲,更非人人都愿意写下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好在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关于家庭出身的举手表态和小纸条都已取消,她小心地维护着他们的自尊心。
“事实上这是社会的问题,如果从底层向上走的通道是畅通的,农村的出来也能找到一份有面子的工作,也能有足够的钱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就不会自卑。如果不能,不是今天卖空调就是明天参加传销,还是买不起房子、结不了婚,那他们的心态永远都是底层的。”
和送本子的女生一样令人心疼的孩子还有很多。去年的一次作业给了王小妮新的发现,学生里超过一半是曾经的留守儿童,跟父母存在着很深的情感隔阂。他们直截了当地在作业里写:我没得到过爱,没人爱过我。父母出外打工,农村的爷爷奶奶把他们带大,保证吃饱穿暖已算尽了最大的责任,余下的可能就是每时每刻的抱怨,尤其抱怨女孩上学有多没用,不如把钱省下来给家里的男孩。在父母这边,拼命干活为孩子交上学费,这就是爱。
但走出乡村的孩子看了电影、电视,看了城里人,发现爱那么复杂、那么丰富。他们太久没有得到足够的温暖,也太久没有人愿意听自己说什么,他们反问王小妮:我没得到过凭什么付出?
一个老师喜不喜欢听自己说话,十八九岁的年纪顷刻就能领悟。于是课间休息的楼道里,下课回宿舍的小路上,短信、邮件的往来之间,王小妮不用任何压迫的方式去挖掘什么,只需要观察和倾听。“所有他们说出来的,都是他们要说的。我不能变成一个调查人,变成一个到学生那里去挖煤矿的人,我回避这样,除非他们主动说。”
给2008年新生的提问里,关于是否相信真理的一条,全班只有一个人没作回答。仔细查对一番,王小妮得知这个学生名叫**。但真正将人名和模样对上号,还是开学两个月以后的事,这个来自陕西乡下的女孩突然退学离开了海南,在《上课记》里王小妮记录了她申请复读未果又回来的故事。返校以后,**依然坐在教室的后排。直到全部课程结束,王小妮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喜欢上这个专业。
令人意外的是,忽然有一天**独自跑来找王小妮,坐下一说就说了好几个小时。“她走以后,其他学生知道了很惊讶:啊老师?**跟你说好几个小时?我们和她一个班都没说过几句话。”
一个孤独的孩子,得多信任一个人才会滔滔不绝?“**告诉我她9岁时妈妈就死了,但她一点也不伤心,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妈妈。从那以后爸爸带着她和哥哥过,她对家里两个男人说,从今天起你们两个不可以叹气。她说后来她就当了这个家里的妈妈,做饭、洗衣服,从9岁开始伺候家里这两个男人。
现在,一直在外面打工的爸爸腰都弯了,哥哥已经在杭州工作,她自己马上也快毕业了。她对哥哥说,我们要把爸爸养起来。然后她又说,老师,我爸从来没有爱过我,但是现在我要对他付出了。说的时候可委屈了。”
紧接着,**又开始唧唧喳喳地诉说她的打工见闻,这是她每个假期都会做的事情。在深圳一个做插线板的工厂里她曾经干了两个月,发现有个女孩总是戴着口罩,而且她的工资也比其他人多出300块钱。**一直不得其解,最终,“你知道吗老师,原来这个女孩接触甲醛。”
王小妮完全不知道,尽管她就生活在深圳。而这样的故事,**讲了很多。这么多细腻的感受原来都藏在心里头,沉默仅仅是她的一件外衣。
沉默的余青娥也多次出现在《上课记》里,王小妮毫不掩饰对她的喜爱。“上课从来不吭声,快期末了才认识她,不教她了关系才亲近起来。”这个鄱阳湖女孩让王小妮知道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在余青娥写的寒假纪事里,她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一直到年三十晚上才带着上小学的弟弟赶回老家。
弟弟进门脱下热气腾腾的棉袄,身上捆扎着两条鼓鼓的长丝袜,里面塞的全是钱。一条袜子里装的是她父母一年赚的,另一条里是亲戚委托他们带回来起新房子的。这又悲又喜的景象是那么鲜活,令王小妮不得不感叹,待在城里的作家如何想象得出来?
眼下余青娥在三亚的一家公司里做事。她会拿着奶奶做的米花糖来找王小妮,边吃边讲家里的故事。有时还会忽然发个短信,说老师,家里的××花开了。
不知何时开始,讲台下面坐着的就全是90后新生代了。王小妮被学生告知:现在两年就是一代。比起80后,他们的头脑更灵活,更加自主。2011年下半年,学校组织**代表的投票选举,选票发下来后,班里的学生纷纷要求知道候选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有个学生在微博里说我现在手在发抖,我坚决不能同意他们安排给我的,所以我光荣地写上了我自己的名字。另一个说我的票被几个班干部代填了,我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有人写上了自己喜欢的明星。”
王小妮欣赏他们的直接和敢于表达。尽管外部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太多,就业、房价、家庭经济条件等等,但也会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未来他们没问题。”
在2007年“上课记”的引子里王小妮写道:把课上要讲的内容设计好自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要付出人和人之间的最平常朴素又真诚的情感……
进海岛大学之前,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曾经肯定地告诉王小妮,大学四年自己没有遇到一个好老师。惊讶之余,她在心里说:如果有当老师的机会,我可得当个好老师。
这话她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傻,“做个好老师也许不难,但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要复杂。”六年的时间里她不断感到一个人的想法和力量太渺小而不切实际,然而记录和写作的过程又时时掀起一种飞蛾扑火的冲动,牵引着她向她所理解的好老师靠近。一个从外校来旁听的学生课后对王小妮说:老师我终于明白了,杨丽萍在访谈里说,她就是不跳舞,留在村子里种庄稼也是种得最好的,你就是这种人。
王小妮的关注换来了这些年轻人“单纯而又热烈的友情”,他们在她的手机、邮箱里留下各式各样青春的信息,带给她快乐和希望。很多年以来她一直对“我”以外的世界没有投入过热忱和主动,去上课时却感到自己急着要同他们交谈;去上课,变成了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历程。一个原本悲观的人能这么做,“想想原来是在自救啊”,“说是你教育了他们,其实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太多”,“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
几天前,《上课记》里一个上课爱睡觉的男生给王小妮发来了邮件。两年报考电影学院研究生落榜,他最终落脚在安徽阜阳电视台,和几个同学占稳了一档栏目。《上课记》出版后,王小妮给书中写到的每一个人都邮寄了一本。
“他在邮件里说,他现在一边读《上课记》一边读我当年上课时给他们念的《许三观卖血记》,看到许三观号啕大哭他也跟着号啕大哭,跟从前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这个当年其实什么都听到了的男生还告诉王小妮,他现在正给当地一所学校影视专业的学生讲影视写作,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他会读上一段《上课记》。
王小妮说,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不是缺少精英,而恰恰是缺少更多平凡的好人。《上课记》里的年轻面孔,都将是平凡的大多数。她不奢望他们成为大导演、大作家,她只希望他们都能活得好,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能把农村的父母接到城里来,能正正当当地做一个好人,甚至不是她所理解的正正当当……
一个人能做得太有限了,但王小妮做了她该做的,“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上课记》结集出版了,王小妮的“最后一课”也已经结束。2012年,她将不再返回这所海岛大学。在“最后一课”上,她没告诉学生们这个决定,因为“说了会有一种煽情的感觉,我特不喜欢,他们本来就是一些脆弱的小孩。
”离开还是因为体制,就像多年前离开电影制片厂一样,她不愿受束缚。她特意把车从深圳开到海口,好拉回这么多年保存的学生作业。发给他们,他们随手就丢了,王小妮觉得可惜。2011年的上课记还没动笔,这些都会是有趣的参考资料。
离开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学生们了,王小妮的心情也很平静。早就不是古代了,况且学生最精通各种信息交流的手段。在深圳的家里打开微博,《上课记》已经成了焦点。有学生说:老师,××不是这样的!你把他写得太好啦!
王小妮承认,她不会把学生写得太不好,“万一他看到了伤害了他呢?”还有学生说他读了《上课记》很愤怒,老师说农村的孩子淳朴善良,他是城市的孩子,他也淳朴善良。老师还说学校是偏僻的平民大学,好像很差,他觉得他们的学校其实挺不错。王小妮回复他:你心平气和地看,我心平气和地写,有什么观点慢慢讨论。
“一个小孩可以愤怒。我不敢说我写的就是完全真实的,但我没有编造。城市的孩子本身已经很优越了,所以我没太多写到他们。也许他看到的真实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学校在变,我们也在变,一个人一个角度。”
不做他们的老师少了很多顾虑。上课期间她不轻易请学生来家里做客,因为不可能招待所有的人,就会让学生感到亲疏之分。“他们特别敏感,我不希望这样。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被老师一样喜欢的。”从此她可以肆意地对她喜欢的更好一点了。
离开海口4个月了,王小妮的手机还是海南的号,她担心马上就换会有学生找不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