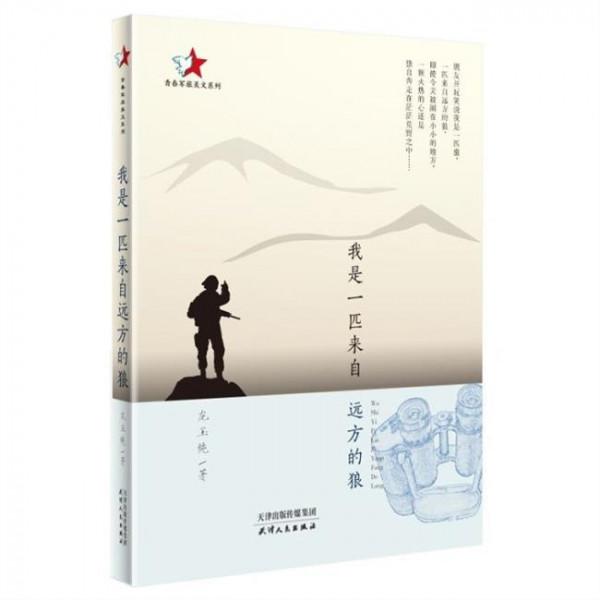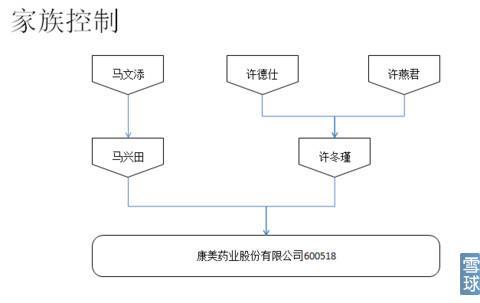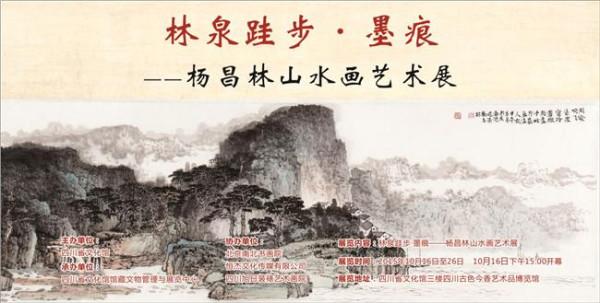许冬林时间的忧伤 【墨舞天涯】时间的忧伤
一直被催着,被时间催着,心上发紧。 仿佛还是六七岁,,还没有入学,终日在河堤上玩。不厌其烦地捉迷藏,和堂姐,还有弟弟。有一回秋后,躲到河堤旁的石桥底下,忽然听见铃声长长一阵响后,便是人声喧哗杂乱而来,一簇簇的少年背着书包从村庄深处,迤俪向河堤走来。
那是河对岸的一所小学放学了。我从桥洞里爬出来,隔河看他们一路说笑雀跃,心上仿佛有钟鼓在紧敲,无端焦急起来。
一颗纯净而蒙昧的心,无着无落地就那么悬起来,在铃声的余音里伶仃晃荡。 原来别的孩子都长大了,都上学去了!别人都随着时间去往远方,只有我还在这里!像一枚干瘪的种子被丢进阴暗的瓦砾之间,还没有发芽。
我心里好怕呀! 那时不知,这竟是我关于时间的最初的忧伤。 似乎是十四岁的一个初冬,一个人爬到平房的顶上,坐看平野落日。田野尽头,橙红的夕阳滑下去,先是圆的形体隐遁,化作了小半天的云彩,然后云彩也消隐。
一颗硕大的橘子糖融化在蓝色的远山和大地之间,骤然,四隅黯淡,暮色惆怅。那一刻,听见我的心啪地裂了细小的口子。仿佛航船被冰山破了个窟窿,冰冷的海水持续涌入,船儿沉重地渐次下沉。一天的时光没了!又没了!
也许,我的少女时代也像这个黄昏的夕阳一样,糖化于水中,缓慢消逝,永捞不起。 谁来收拣我呢?在青春的尾巴上。谁有一双巨大无比的手,将我从滔滔的时间之流里捞起来,呈在掌心上端详?我对时间,是这样怀着疼惜忧惧之心。
那天,去“永和豆浆”打发晚餐,一个人,一份客家汤面。吃到半途,遇一旧友。其实也说不上“友”,我和她的过去若有交汇,也不过是我曾在16岁那年托她代买一本当地一诗人的自印诗集。她也来吃面,也是一个人,风尘仆仆的样子。
两个人寒暄后,大约出于礼貌,她夸我道:你呀,还是那么年轻漂亮……。我笑,回她:我老啦,倒是你,一点样子都没改!她辩解,皱纹啦……斑点啦……语气沉痛。 其实我们都变了,都不是从前,都不是留在时间里的十多年前的那个小女人了。
二十岁之前,亲戚们与自己一年一见,见时总要大赞:大了大了,变了变了,更好看了……那时,时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重一重的惊喜。三十岁以后,已经不敢再要改变,再改变,便是悬崖峭壁,便是风里黄花。
一点点的痴心,竟是想要墨守十年或五年前的样子,但这是很难的。所以,旧友再见,道一声容颜未改,便成了至高的安慰。是啊,是安慰,在时间里流淌,委屈之心渐生,时间于这时的自己,多半是冷了心肠的恋人。
在时间的册页里,从前我们是灰姑娘,是白雪公主,情节越走越好。即使暂时曲折,但终点是明朗的,最终都穿上了水晶鞋,都坐上了马车,都住进了城堡里。但三十岁以后,一切都要慢慢变卦,这厢才千方百计用尽心思,那厢已经是黔驴技穷捉襟见肘。
手拿魔镜一照,最优秀的女人已经是别人家的女儿。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个老巫婆的垂死挣扎。是啊,越看自己,越是一个巫婆的角色,有笨拙的小伎俩,有萧瑟寒冷的心,有一不小心就沦为笑柄的情节。
前三十年,时间的帐里,我们算的是加法,美丽,宠爱,观众的掌声……跟着跟着就来了。三十年后,河东换河西,是减法,豪气一日日地短下去,激情的焰也日渐低矮,掌声来得艰难了。
我住的这栋楼里,有一户人家的客厅里坐着一尊落地大钟,每到半夜,万籁俱寂之时,那大钟“当当……”敲响,浑重的声音在夜气里久久回荡,令人如同置身深山老林,听见古寺钟鼓之声撞山而来,实在惊人心魄。 夜半的钟声,在三十岁之后的女人听来,一声声,都是寒怆的。钟声敲打无眠,想起少时老宅墙上的一只挂钟,绛红的外壳之下分明一副冷峻凛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