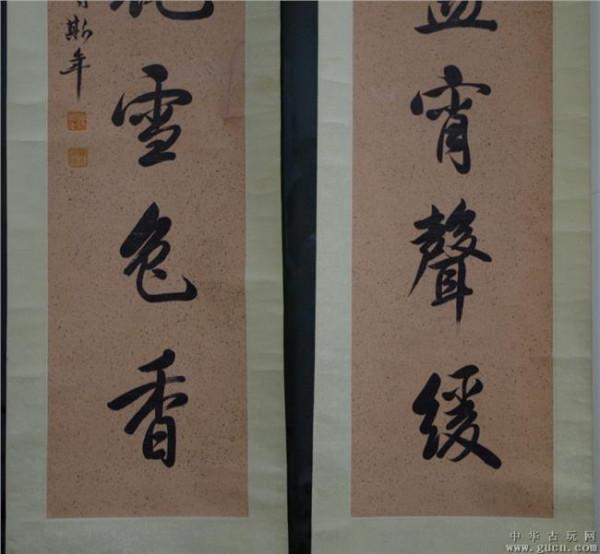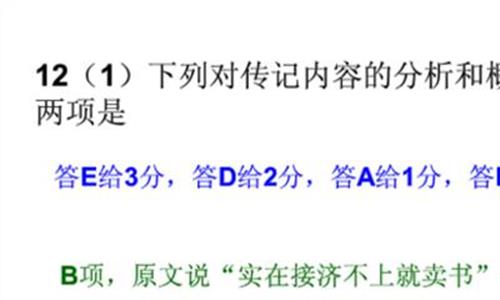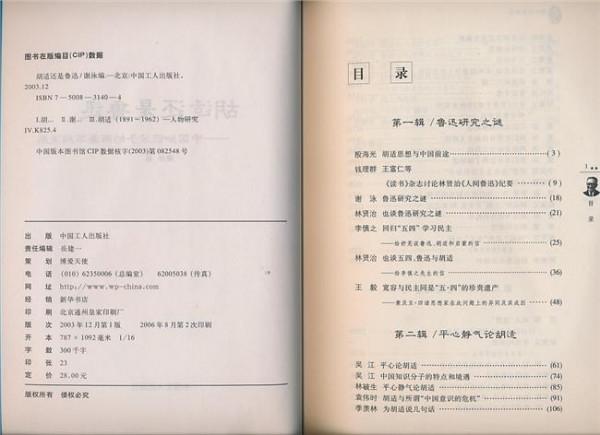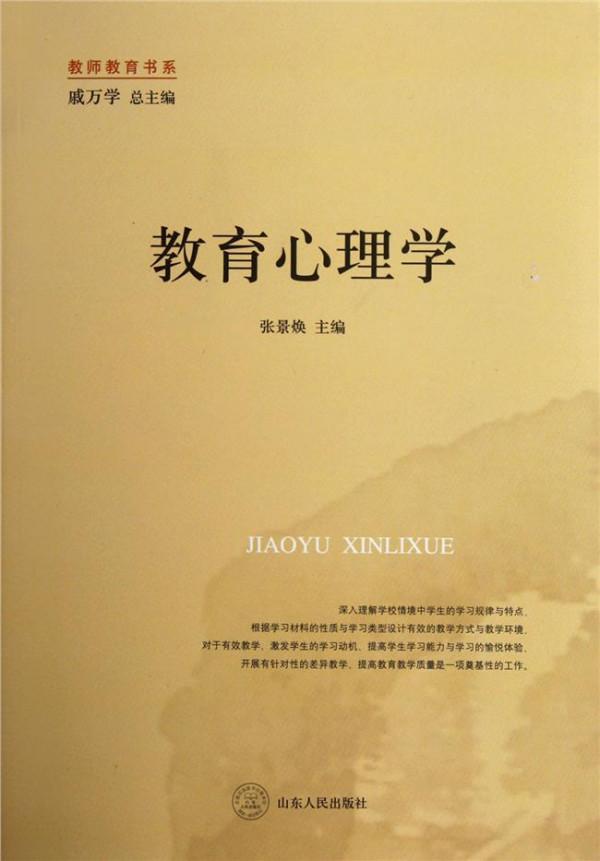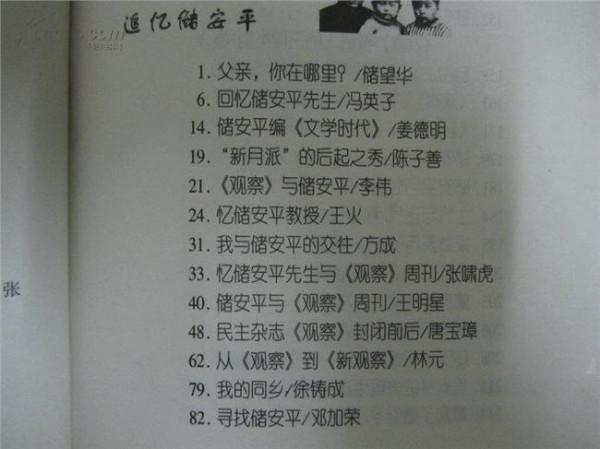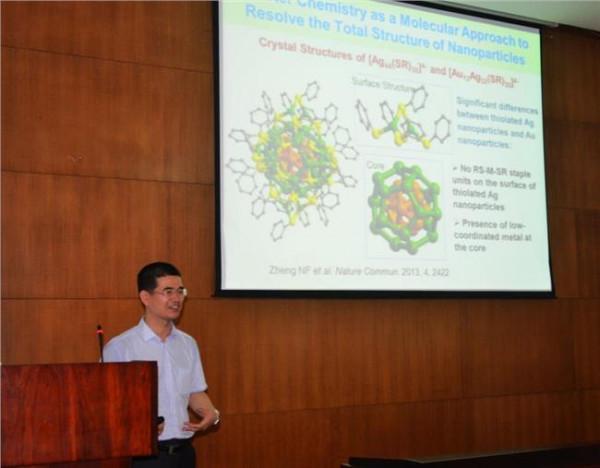谢泳回到傅斯年 要不要“回到傅斯年”?
谢泳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一书。何谓“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学观。而傅斯年的史学观,按谢泳的概括,“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 所谓“史学即是史料学”,这其实不是什么创见,中国的旧史学向来如此,西方也有兰克及其影响下的兰克学派。兰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可是现在为什么谢泳要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回到傅斯年”的命题?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原来,曾几何时,史学是不是史料学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学者态度、立场、阶级属性,关乎“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问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有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学派的斗争。这场斗争以195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一篇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揭幕。
陈在讲话中说:“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资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以此为基调,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系学生分别发起了对陈寅恪、岑仲勉、童书业、徐仲舒等著名学者的批判,这种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历史学界的“三大老板”——胡适、顾颉刚、傅斯年。
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内容从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诗中可见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诗不太雅正。与此相比,还是学者的分析有分量些。
且看唯物史观派领军人物范文澜和胡绳的文章。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见中国社科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发表在陈伯达的报告传达之后,要点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范氏在文章中指称,以胡适为代表的史学家大搞烦琐考证就是“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胡绳题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长文(收入人民版《枣下论丛》)发表在1956年,语气较为平和,其中重点批判了傅斯年的历史观,他说:“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
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历史的海洋中。
”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对史料学派的不满都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史料学派是只讲求占有资料、考订史实,拒绝理论(当然应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无法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客观规律。
回顾这场“斗争”,现在可以说范文澜等人对史料学派的指责没有什么根据,因为史料学派中人并非一定排斥理论,如顾颉刚早在1940年为《史学季刊》作《发刊词》时就针对考据与史观之关系说过如下的意见:“历史科学家惯于研索小问题,不敢向大处着眼……若不参与历史哲学,俾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功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
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试看顾氏此论与上引胡绳的话有何区别?顾颉刚另有一句名言,见于他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这句话在五十年代曾颇让顾的批判者愤怒,其实顾氏“味之素”云云何尝不是从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观的功用? 本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史料派与唯物史观派之间不应该发展到无法并立的地步,不仅是顾颉刚等人分明有赞同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的话,而且就是范文澜、胡绳不也曾对史料学家的劳作表示过肯定?胡绳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说:“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而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
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
”尽管如此,“路线斗争”云云还是向我们这些后世读者提示着过去那场争论的严重性,否则当年执教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也不会愤怒地拒绝为学生开课了。那么两派史学家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呢?首先是误读的存在,正如谢泳所分析:“对史料学派的批判是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史学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也根本没有过史料的理论”;其次我以为应该是对“理论”“史观”内涵理解的歧异,如前所引,唯物史观派固极重理论的引导,史料学派也并未排斥,但史料学派反对将“理论”庸俗化,坐实为唯物史观,像顾颉刚就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
”而所谓唯物史观派始终坚持历史研究应在以现实政治为最高导向的理论指导下进行。
同一“理论”,大异其趣,所以范文澜才会号召要对“坚持学术独立”“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胡适门徒”开战。最后,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也是各有主张。“历史有什么用?”当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曾被稚子的这句质问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纸堆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用”的含义丰富,如果仅仅定义为实用意义上的“用途”,史料学派中人的态度是:历史学可以有“用”,但历史学家不应去求“用”,像顾颉刚就坚定地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作学问的目的”。
而唯物史观派中人则认为,历史学必须有“用”,历史学家应该去主动求“用”。胡绳特别举了个例子来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写了篇《明成祖生母纪疑》而且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胡绳乃对此问道:“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来的”。
现在看来,明成祖的生母是谁的确是个琐屑的问题,但是否就真无意义还大有可商处,试想一下,如果与此相关的小问题都弄明白了,人们对明宫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会不会更深一些呢? 通过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之争的回顾,走过一段弯路的我们终于明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熟悉、考订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工作。
所以谢泳先生提出了当代中国史学要回到傅斯年的传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对过去那段迷误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对比西方史学的发展,我们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
西方在兰克学派以后,有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有年鉴学派,有斯宾格勒有汤因比有布罗代尔等大师,无不是对以实证史学为特色的兰克学派的扬弃。如果史学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传统,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罢,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著作,这岂非荒唐?另外,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向来发达,中国人思维、治学的特点本来就“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所以历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虽然重要,但难道我们不应同时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俄罗斯知识分子有言:“我的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否也应具备这种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还有一点,强调“回到傅斯年”似乎还忽略了学者禀赋、气质之差异,其实,只要没有现实政治的干扰,何妨让几个没有兴趣钻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论?不着边际之处,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时也许还会有灵光一现呢。
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名著当下屡被人讥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论”中有片言只语启发你深沉思考,这不就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