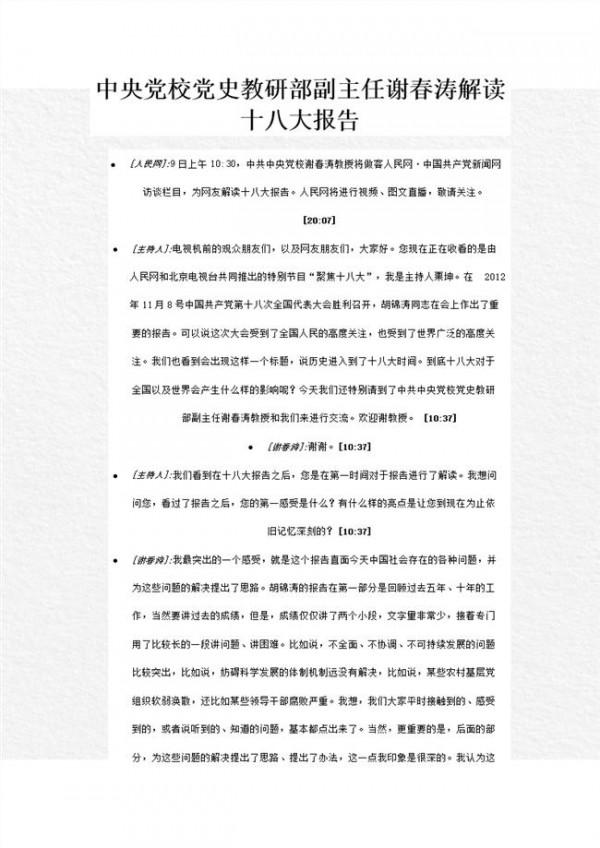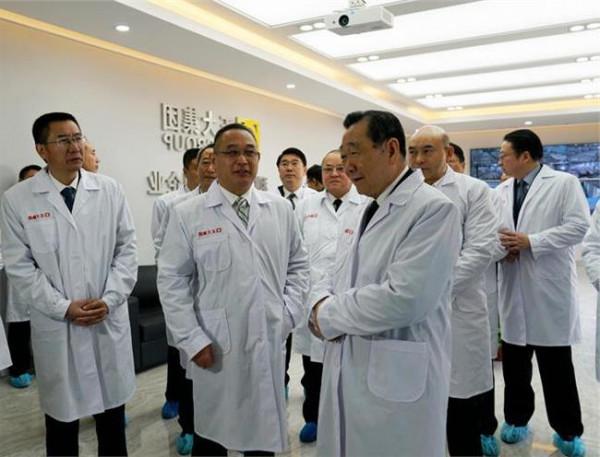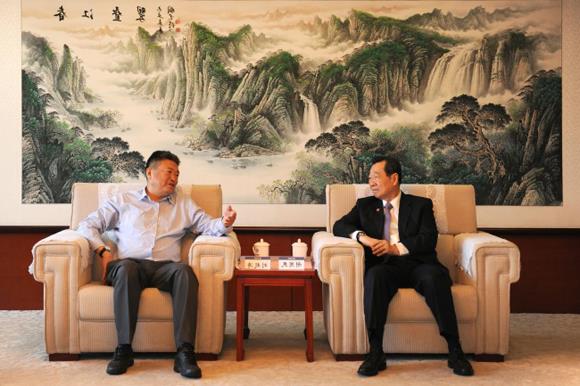谢泳为什么被厦大禁 谢泳在厦门大学遇到了什么事?
说起谢泳,只要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史稍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这颗1961年出生在山西省一个小城市的“读书种子”,在其人生的求知阶段,却正好遇到“文革”的浩劫,无书可读。
因此,在“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他与其同一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面对打开的大学校门无能为力,只进入了山西的一家中等师范学校。如果谢泳不是对现代文化史发生了浓厚兴趣,那么到今天,他可能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
但是,谢泳在他置身的那个经济不发达、学术研究也无氛围的城市里,选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即一个人(储安平)、一本期刊(《观察》杂志)和一所学校(西南联合大学),以个人之力精心耕耘,终于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著作如井喷一般不断出版,向我们打开了触摸那段已经逝去的岁月中的知识分子风骨的大门。
谢泳在学术研究上展示的成就,不仅为学界所公认,也引起了高等学校的重视。2007年,他以一家文学期刊编辑的身份,进入厦门大学的人文学院当了一位教授。说实话,在今天教授已经多如牛毛的环境里,多一个谢泳这样的教授,似乎并不是什么大的新闻,因此在当时也未见报章对此有过什么报道,今天在网上能够检索到的,只有寥寥几位高校里与谢泳早已成为至交的教授,在博客上发了几篇文章为之喝彩。
谢泳毕竟只有一张专科文凭,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成为教授,这在当下等级森严的高等学校环境里,却又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厦门大学的校长因此而在那寥寥的博文中被尊称为“蔡元培再世”。
高等学府为这位踽踽独行的学者打开了大门,而谢泳本人也开始按照高等学府的要求来对自己进行“格式化处理”。身份转换以后,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散淡的文学编辑,他必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拿出过硬的教学成果,才能站住脚。
在这同时,他也开始接受学校对教授的考核,拿出自己符合规范的学术成果。尽管谢泳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但多年的个体研究早已使他具备了撰写学术著作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他的技术不可能比那些高学历研究者差一丝半毫。
很快,他出版了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谢泳已经超越了对个案的研究,开始以一个教授的身份向他的学生传授他的学术研究技巧。谢泳的研究严格遵循胡适提倡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对史料的辛勤搜索使他的立论站在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结论大都很有说服力。
但是,如果以为谢泳能够轻松地在大学里站住脚,显然又太乐观了。最近,谢泳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思想利器》,看这个书名,颇像他多年前的著作,带有了一点文学味。但是,这仍然是一本从史料出发进行研究的书,谢泳通过各种不为旁人所注意的冷僻史料的挖掘对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些疑窦丛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他那本作为教材的专著提供了丰富的实例。
翻开这本书,我照例先看书的后记。不料读到最后,竟读出了作者的沧桑之感。
后记的写法,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作者在最后总要借此机会对帮助他完成这本书的一些友朋和家人表示一番感谢,谢泳的这篇后记也没有跳过这个俗套。但是,他在感谢了一连串人后,又特意写道:“此外,我更要感谢周宁兄。
五年前(这篇后记写于2012年10月——引者注),他费心调我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编辑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虽然我努力工作,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还是给他添了极多麻烦。在我面临失业的时候,他以出色的行政才能和政治智慧,使我化险为夷,得以终老厦大。”
谢泳的这段文字,和他平常为文的内敛严谨大不一样,充满了一种情感的宣泄,虽然是在感谢他的学院领导,但其实是在吐露自己胸中的块垒。这段文字给我的信息是,谢泳在厦门大学一定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这个事足以让他丢掉在厦门大学的教职,只是因为当时力主调他进厦大的周宁的斡旋,才算平息。而那一句“得以终老厦大”,则显示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的无奈,凄楚,甚至不安。
谢泳在厦门大学遇到了什么事?作者没有说,我从网上搜索了一番,也不见有公开报道。只是见到一条并不显眼的消息,2012年12月,他在重庆的一次学术演讲中谈到了现行大学的三个问题,一是高校行政化,二是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三是高校高度的职业化。他说,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虽自甘边缘化,但为了应付考核标准,他在厦大并不幸福。
谢泳指出的现行大学存在的三个问题,并不是他的首创,很多高校教授都有过类似的吐槽。但是,这番话从一个对旧时代的西南联大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谢泳嘴里说出来,却还是别有一番滋味。
今日的高等学校,毕竟已经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也不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谢泳可以因为大学领导对他的厚爱而进入高等学府,但是他却不可能穿越已经高度格式化的高校行政化管理,也不可能超脱已经扭曲的学术评价体系,即使是那些礼聘他进入高校的领导,对此也无能为力。
于是,当谢泳进入高校以后,他就从一个本来是学术研究上独树一帜的人物沦落为一个不合格的教授,处处受到掣肘,以至发出了“不幸福”的慨叹,甚至要面临失业的风险。
现在,这个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阴影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上。6年前,当他受聘进入厦门大学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意气风发,期望着能够借助大学的平台在学术研究上创造出更高的成就,他对这所将要给他创造新的学术生命的高校也一定会充满感情。但6年后的今天,他却发出了“得以终老厦大”的慨叹。其间的委屈、辛酸,他只能通过一篇后记来抒发。看来,大学对他来说已经只是一个解决吃饭问题和养老问题的场所了。
今天的谢泳,其学术研究的方向早已突破了年轻时定下的一本书、一本期刊、一所学样的目标,他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但是,他的研究对象却不是当下高校里的显学,而是一系列充满了敏感色彩的当代文化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即以这本《思想利器》来说,其研究内容即有胡风、林昭、思想改造运动、反右等,尽管他的研究保持了一贯的严谨与冷静,严格从史料出发来推出观点,但是这些人物和事件在今天的社会里,却都已经成为敏感词。如果谢泳在大学课堂上向他的学生提起这些话题,那些在主流意识形态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生,还能欣然接受吗?
谢泳进入了行政化色彩浓厚的高校,但他不可能像他研究的前辈一样,借助大学的讲台自由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被锁进了体制的厚障壁之中,从此,他在这个体制中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他再也不能让他的“周宁兄”再为了他去耗用其“出色的行政才能和政治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