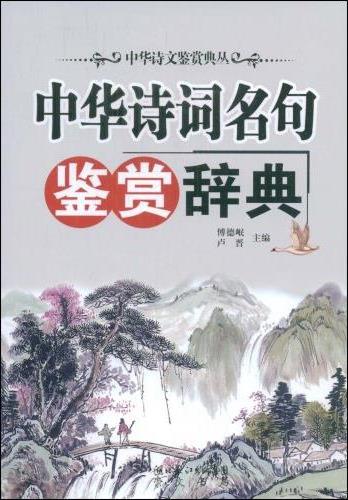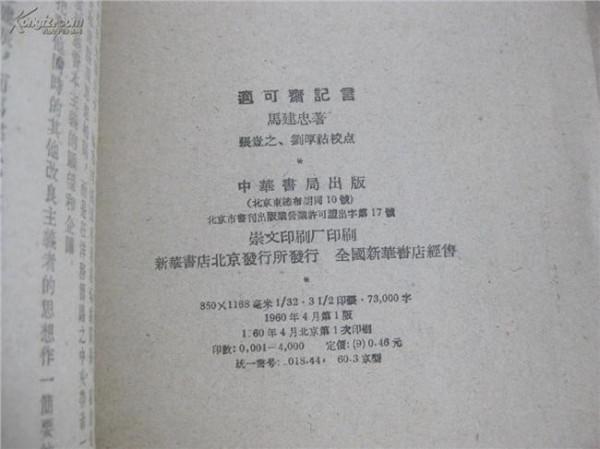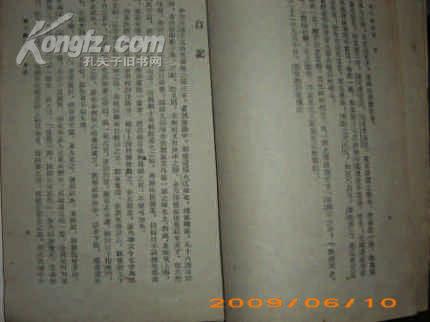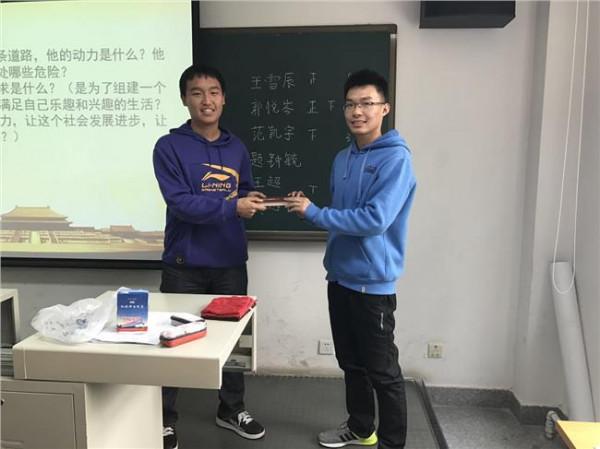马建忠书法 清马建忠著《马氏文通》一书的历史介绍
《马氏文通》,十卷。清马建忠著。成书於一八九八年。有清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绍兴府学堂教科书版、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上海印书馆版、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杨树达刊误本、一九五四年中华书局印行章锡琛校注本等。
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〇〇),字眉叔,江苏省丹徒县人,少好学,通经史。曾在法国人办的上海天主教教会学校学习,精法文、拉丁文。一八七五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大学政治学院留学,同时兼任清驻法使馆翻译。
毕业后回国,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多次上书言借款、造路、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材等,深得李鸿章赏识。一八八一年奉李氏之命,赴印度与英人议鸦片专售事。一八八二年与水师提督丁汝昌到朝鲜蒞盟,诱擒大院君,平定朝鲜政变。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北京,李鸿章率马建忠赶至上海,主持一切。是年八月中旬,俄国沙皇政府突然发来抗议电文,威胁将封锁吴淞港。电文长达七千餘字,由马建忠负责连夜译成,终因过度劳累,併发热症,於八月十四日过世。
平生积极主张变法维新,认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为中国近代资產阶级改良主义的先行者。著作除《马氏文通》外,又有《东行三録》、《法国海军识要》、《适可斋记言》、《适可斋记行》等。《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有传。
马建忠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纷纷瓜分中国、广大人民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开始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形成了一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潮。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同思想的有识之士,马建忠也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
他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语文教学方法,认为"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后序),原因就在於西方教授语法,而中国没有语法著作。由於中国没有语法著作,所以"四千餘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也就无暇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西人相角逐之时,"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同上)。
为了改变中国语文教学的落后面貌,使人民在年富力强之时就能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马氏乃积十餘年勤求探讨之功,写成了《马氏文通》书。
《马氏文通》全书共十卷,卷一是正名,卷二至卷六论实字,卷七至卷九论虚字,卷十论句读。书前有作者的《序》、《后序》和《例言》。从内容来说,"是书所论者三:首正名,次字类,次句读"。(例言)其中,正名是对於书中字、词、次、句、读等概念作出界说,以为全书论述的基础,所以此书实际上分成字类(词法)和句读(句法)两大部分。
此书的字就是词,字类就是词类。字分为两大类,即实字和虚字。作者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卷一),可见作者是从意义角度区分词类的。实字又分五类,即名字、代字、动字、静字和状字。
作者指出,"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凡实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凡实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凡实字以肖事物之形者曰静字"、"凡实字以貌动、静之容者曰状字"(同上),可见这五类实字大致相当於今天所说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
虚字又分四类,即介字、连字、助字、嘆字。作者指出,"凡虚字以联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凡虚字用以为提承展转字句者统曰连字"、"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凡虚字以呜人心中不平之声者曰嘆字"(同上),可见这四类虚字大致相当於今天所说的介词、连词、语气词和嘆词。
此书的句指句子,词指句子成分。词有七种,即起词、语词、止词、表词、司词、加词和转词。作者指出,"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凡以言起词所有之动、静者曰语词"、"凡名、代之字后乎外动而为其行所及者曰止词"(同上),可见起词、语词和止词相当於今天所说的主语、谓语和宾语。
作者又指出,"惟静字为语词,则名曰表词","表词不用静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静字"(同上),则表词相当於今天所说的形容词谓语和名词谓语。
作者说,"凡名、代诸字为介字所司者,曰司词"(同上),"外动行之及於外者,不止一端,止词之外,更有因以转及别端者,为其所转及者曰转词","内动之行,虽不经达乎外,至其行之效有所于归者,则为转词"(卷四),则司词就是现在的介词宾语,转词相当与现在的间接宾语和动词涉及的某些状语和补语。
在介词结构中,介词宾语对於介词来说是司词,对於动词来说则是转词。至於加词,则有两种:一、"介字与其司词,统曰加词"(卷二),这是指介词结构充当的状语或补语;二、"凡名、代、动、静诸字所指一,而无动字以为联属者,曰加词"(同上),这是指同位语。
此书的读是指主谓结构的词组和复句的分句,即所谓"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卷一);此书的顿是指句中的短暂停顿,所谓"凡句读中,字面少长,而辞气应少住者,曰顿。顿者,所以便诵读,於句读之义无涉也"(卷十)。
根据"中国文字无变也"(卷七)的特点,本书又在字和词的相应关係上建立了位次理论。作者指出,"凡名、代诸字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曰次"(卷一)。次有六种:一、"凡名、代诸字为句读之起词者,其所处位曰主次";(同上)二、"凡名、代诸字为止词者,其所处位曰宾次"(同上);三、"凡数名连用而意有偏正者,则正意位后,谓之正次"(同上);四、"凡数名连用而意有偏正者,偏者居先,谓之偏次"(同上);五和六、"凡名、代诸字,所指同而先后并置者,则先者曰前次,后者曰同次"(卷三)。
由此可见,主次和宾次是一对概念,主次指主语位,宾次指宾语位;正次和偏次是一对概念,正次指偏正结构中的中心词,偏次指偏正结构中的前加修饰语;前次和同次则是同一概念的两个位次,包括表语、同位语等。
这三对概念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一指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句法关係,一指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前后位置,因此正次可以是主次或宾次,前次或同次可以是主次、宾次或偏次。
《马氏文通》的科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的语法体系十分完整而系统。它从词本位的理论出发,把汉语的词分为九个词类,这九个词类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代语法学,也不过是把数词从静字(形容词)中分出来,另立一类量词,以及名词分出方位词、动词分出趋向动词等附类而已。
它以起词和语词总括一切句子成分,认为其他句子成分都是分别属於起词和语词的,这种析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层次性。它对各种语法结构和语法规律都作出了详尽而周密的描述。
全书先讲词法,后讲句法,卷二讲名词和代词,卷三就讲位次,因为只有名词和代词才有位次现象,卷四讲动词,卷五就讲坐动和散动,因为坐动和散动是动词的运用。卷十讲句读,先从分析句和读的成分开始,分别讨论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等,再进而论述顿、读和句,组织严密,次序井然。
其次,此书的价值还表现在,它在模仿西方语法和继承古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在收集分析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了汉语特有的许多语法规律。例如作者根据汉语的特点,首创划分出介词和助词这两个词类,他说:"泰西文字,若希腊、辣丁,於主、宾两次之外,更立四次,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故名一代诸字各变六次。
中国文字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卷七)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种"格"的形态变化,而是用介词来表不"格"的变化所表达的语法意义。
他所确立的五个介词,除"之"以外,其餘四个"於、以、与。为",至今仍然是语法学界公认的介词。作者又说:"泰西文字,……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
……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卷九)拉丁语的语气是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达的,汉语的语气则是通过助字(语气词)来表达的。马氏所列举的助字"也、耳、矣、已、乎、哉、耶、歟"等,也至今为人们所沿用。
又如作者在详细考察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了古代汉语的六种被动表示法:一、加"为……所"表示被动;二、加"为"表示被动;三、加"於"表示被动;四、加"见"表示被动;五、加"可"或"足"表示被动;六、外动词单用表示被动。(卷四)其中除五、六两种外,其餘四类都为后人所接受。
《马氏文通》的价值还在於书中收录了大量古汉语例句,总计大约有七千至八千句。对於这些例句,马氏的分析解释未必完全恰当,但他并不回避矛盾,而是把所有的现象都一一罗列出来,这就促进后人去思考,去解决,从而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例如他说:"‘吾’字,按古籍中用於主次、偏次者其常,至外动后之宾次,惟弗辞之句则间用焉,以其先乎动字也。若介字后宾次,用者仅矣",而"‘我’、‘予’两字,凡次皆用焉"(卷二)。他的这些话引发了后人关於"吾"、"我"是不是上古汉语格的变化的许多讨论。
由此可见,《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的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正如梁启超所説:"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马氏文通》以前,中国没有语法学。虽然章句和句读之学在汉代就已经產生,但是当时的学者大都是从修辞上着眼,而不重视语法的分析。
以后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虽然都专门讨论了虚词,但它们都是逐字为训,并没有构成语法体系,因而只能称为语法学的萌芽。
马氏此书则完全突破了传统小学的框框,揭示了语言内部的语法构造,勾画了古汉语语法的轮廓,破除了"汉语无语法"的谬论。因此,《马氏文通》的诞生标誌着汉语的语法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训詁学的范畴,而卓然成为一门独立的生气勃勃的学科。
《马氏文通》问世以后,对於汉语语法学具有重大的影响,此后,无论是描写古汉语语法的《中等国文典》、《国文法草创》,还是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新著国语文法》、《国语文法概论》, 一直到现代的许多光辉著作,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马氏的语法体系而加以发展变化。八十多年来,我国语法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跟《马氏文通》的歷史功绩是分不开的。
不过,由於创业的艰难和歷史的局限,《马氏文通》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首先,由於此书出版於马氏逝世前两年,作者生前来不及对这部三十万言的巨著进行最后的校订,因而此书在术语、引例和解释等方面,都有许多前后不一致和分析欠准确的地方,从而引起后人的许多批评、指责和争论不休。
例如此书前后共出现六个位次名称:主次、宾次、偏次、正次、前次、后次,但是马氏又云:"次者,名、代诸字於句读中应处之位也。次有四:曰主次,曰偏次,曰宾次,曰同次。
"(卷三)没有提及正次和前次,那末此书究竟有几个位次,就成为后人的疑问之一。同时,作者在卷一中指出:"凡名、代诸字为句读之起词者,其所处位曰主次",可见主次只限於起词;可是作者在卷三中又説:"凡句读中名、代诸字之为止词、起词者,皆为主次,已详於前",则主次又出现於止词。
对此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认为"止词"係"表词"之误,但也有人认为这裹的止词是指兼语而言。又如关於司词,马氏在卷一中指出:"凡名、代诸字为介字所司者,曰司词",可见司词是对介字而言的;可是他在卷三中又提出了"象静后之司词",认为《论语·为政》"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寡"是静字,"尤"和"悔"是其司词。
可见这种司词并不指介词所司的成分,而是指补足静字之意的成分,相当於动字的止词或转词。因此这种司词跟介字后的司词实在是同名异实,不宜互相混淆的。
其次,此书往往从意义出发来研究语法。研究语法不能不顾意义,但是不能离开语言的组织功能来谈意义。例如马建忠根据有解、无解来区别实字和虚字,也就是根据意义上的差别来区分实字和虚字,他说:一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
"(卷一)但是既然虚字是"无解"的,那末虚字又如何根据意义来进行再分类呢?马氏把意义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而且把词的词匯意义和结构意义这二者混同起来。当他说"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的时候,是根据词的词匯意义而言的,以孤立的字为对象,拿意义作标准,自然认为字有定类;可是他又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卷一)这时则是根据了词的结构意义,即当词进入句子以后,获得了不同的句法意义,所以又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了。
马氏未能分清这两种意义,所以弄得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了。又如根据马氏关於次的定义,次是跟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位置有关,但马氏在对同次进行解说时,却说表词与起词所指同一,所以归入同次(卷三),这时他又根据意义来判断次了。事实上,从句中位置看,表词跟起词是根本不能同一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马建忠的眼光中,希腊语法也好,拉丁语法也好,汉语语法也好,"其大纲盖无不同"(后序),"各国皆有本国之葛朗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可"(例言),於是他就用西文"一定不易之律","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后序)。
因此,此书的理论依据是拉丁语语法,其语法体系是根据"西文已有之规矩"(后序)建立起来的。例如《孟子·公孙丑下》"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马氏以"孟子"为转词,"室"为止词,而《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穡",马氏则以"民"和"稼穡"为两个止词。
(卷四)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实际上这是马氏以拉丁语法以律汉语的结果,因为在拉丁语法中,告言义的动词可以带两个受格宾语,而授予义的动词只能带一个受格宾语和一个与格宾语,与格宾语就相当於马氏的转词。
马氏对於西方语法的这种生搬硬套,不但严重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大大影响了他对於汉语语法特点的分析和研究,而且开了后来研究者的模仿之风。
例如在汉语中,动词、形容词也可以做主语和宾语,名词、代词和形容词也经常起到副词的作用,为了维持词在意义上的类别和跟句子成分的对应关係,马氏把这种现象统统算作"假借"。这种词类假借说,是作者在模仿西方语法遇到困难时的一种变通的办法。
事实上汉语的词在造句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而非单一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们所处的位置与西方语言不同,而认为其中一些词类以借为其他词类。在古代汉语中,词类假借说(又称词类活用)应该真正严格限止在个别词的临时性灵活使用上,如果某一词类能够大量出现在某一句法地位上,那就不应该视为假借和活用。
又如作者关於次的理论兼指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句法关係,而起词、止词等也表示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句法关係,因此次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起词、止词等句子成分的概念有许多重合,这样,除了因为名词修饰语马氏未立词名,所以偏次尚属有用之外,其餘的次和词就是徒然多立一套名目了。
马氏之所以在词之外又立有次,其原因又在於模仿西方语法在句子成分之外又有格。但是西方语法的格有其形态的标誌,汉语没有,汉语只有位置一途,则次和词的相重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此书使用的许多概念、术语,如字、词、句、读等,往往与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名称相同,而文中又不能不用传统语文学的名称,这样新旧名称参杂互用,鱼龙混杂,往往使读者不明所以,难以卒读。例如卷一界说九:"《论·公冶》:‘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又《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也、矣、乎三字,今以助一字而已。故同一助字,或以助字,或以助读,或以助句,皆可,惟在作文者善为驱使耳。"这裹第一、四两个"字"为文字之字,第二、三两个"字"则相当於今天所说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