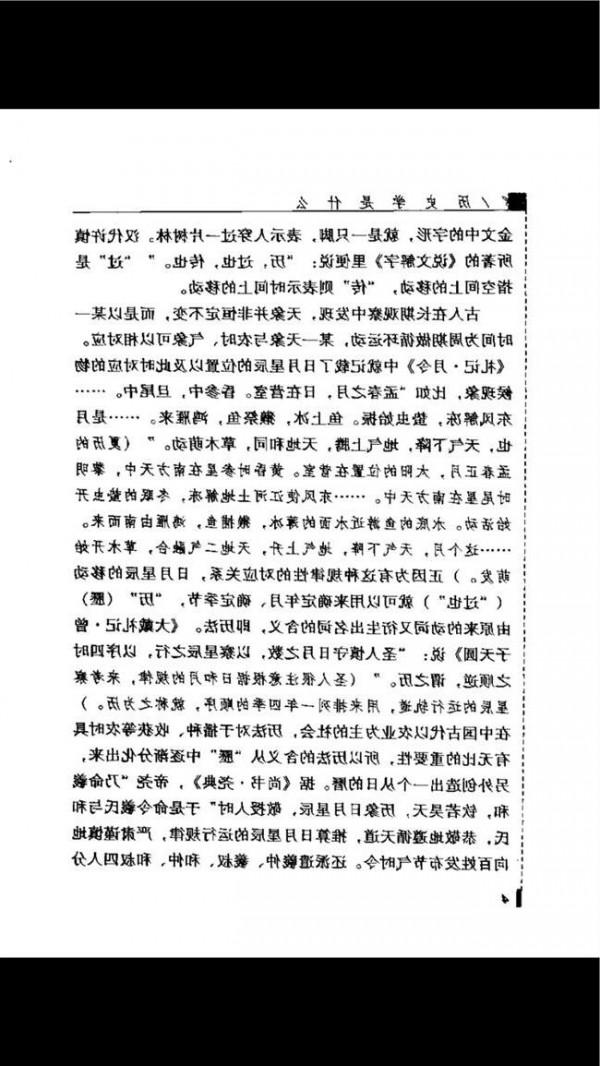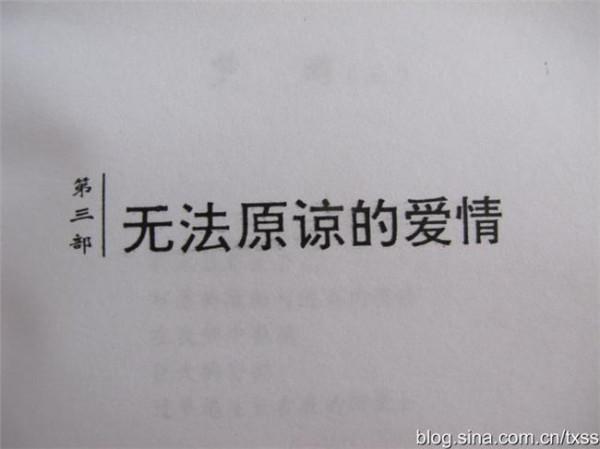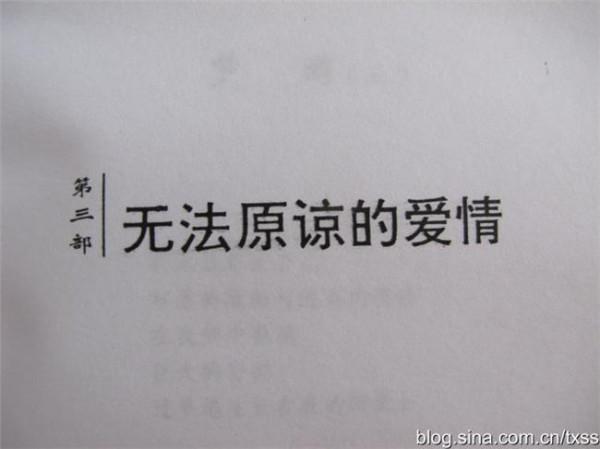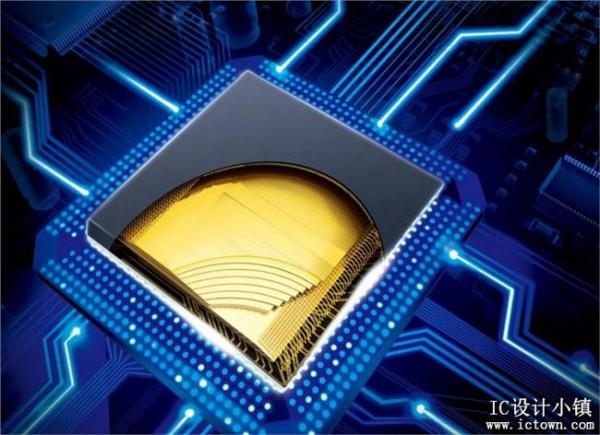阎连科日光流年 阎连科《日光流年》自序
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对我实在是一种考验。我原不是那汇总要十年磨一剑的人,几天、几十天做不完一件事情,焦躁与不安就会涌动上来,人变得浮躁不堪,仿佛头被人摁进了水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写小说委实说不是一件上好的事情,下一人生如何选择,我怕不会再去选择这种职业。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续过程,尊卑贵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皇帝与乞儿、权归与百姓、将军与士兵,事实上同来之一方,同去之一方,无非是在来去之间的行程与行向上不同罢了。就在这不同的行向的行程中,我渐次的也才多少明白,所谓人生在世,草木一生,那话是何样的率真,何样的深朴,何样的晓白而又秘奥。
其实,我们总是在秘奥面前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枯荣的一次轮回。可枯荣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繁琐、意义无穷。
就像我们写小说的忍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与众不同了似地。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在生命面前,不该是这个样子。
倘若任何结果都等于零的话,那么等号前的过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应该说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能不去在意,也不能太过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说下一人生,不愿再选择写小说这种职业。
我想四十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小家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我的父辈、祖先以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不是要学习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内心深处清美博大的诗境。
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利和欲望。
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美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走去。
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什么的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一座房子住的太久了,会忘了他的根基到底埋得有多深,埋在哪儿。现代的都市生活,房主甚至连房子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样都不用关心。
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深水之间都以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
我写《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们寻找这些。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是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连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的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的上路走了。
既然不知道远处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想到了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四十岁的门槛。
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心平气和的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至于用三年的时间写作,半年的时间修改,这除了我身体状况大不如往年,再也不能对一部作品一气呵成的原因之外,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对原初的寻找的凄楚的愉快,我害怕这种凄凉的快感很快会从我的身边走失,而使写作带给我的安慰转眼间烟消云散。
我不渴望写作,可我渴望无力摆脱人世的缠绕和困惑时,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可我写完他之后,我将面对写作目瞪口呆而不知所措。这不是对写作的江郎才尽,不是对艺术的一种困惑,而是对生命原初寻找后的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把本可以快一些的写作速度慢下来,把先前一般不改稿子的习惯改了过来,把原来四十六万字的作品,一气压、删掉了近十万字。这不仅是说我想让《日光流年》更趋完美,我知道《日光流年》里的遗憾也许尽其我毕生精华都无法弥补,我这样修改了一遍,三易其稿,还是为了延续写作中那种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
把《日光流年》交出手是,无人可以体会那中我完全被掏空了的感觉,那种心灵被悬浮的感觉,如果不认为是一种矫情,那时候能回到山脉的土地上去种种地,和我少年、青年时期一样的劳作一些日子,真的会比读书更觉得充实一些。
无论如何,《日光流年》的成败已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在四十岁前写了《日光流年》,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了,我又可以想、继续写我的别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的劳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