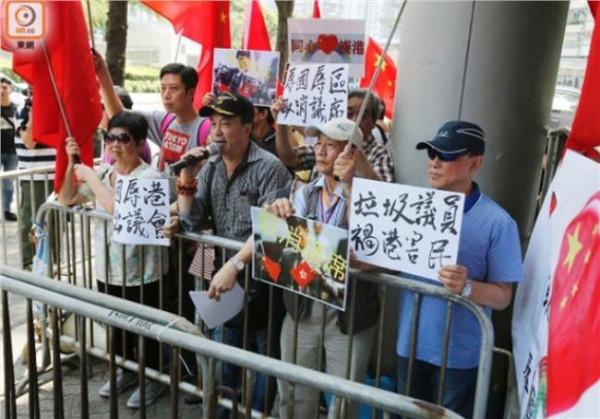凤凰网郑永年 转凤凰网 郑永年先生《我最失望的就是中国知识界》(转载)
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
很多人认为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
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
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
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
我们做学者的,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
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对当下知识界的激烈争论,其实我想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
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之前出版过一本书《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
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
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
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
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
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
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
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
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于国家的“转型”这一话题,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
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
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
我们的学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有关知识界的分化问题,其实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
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
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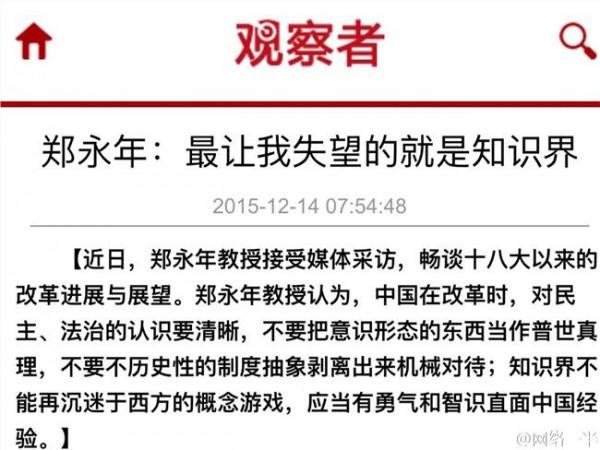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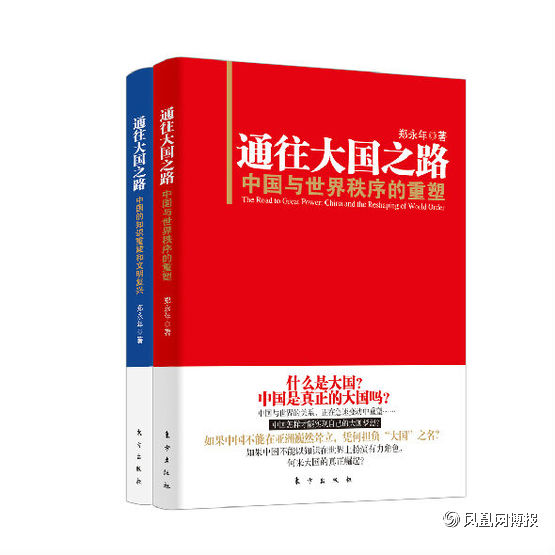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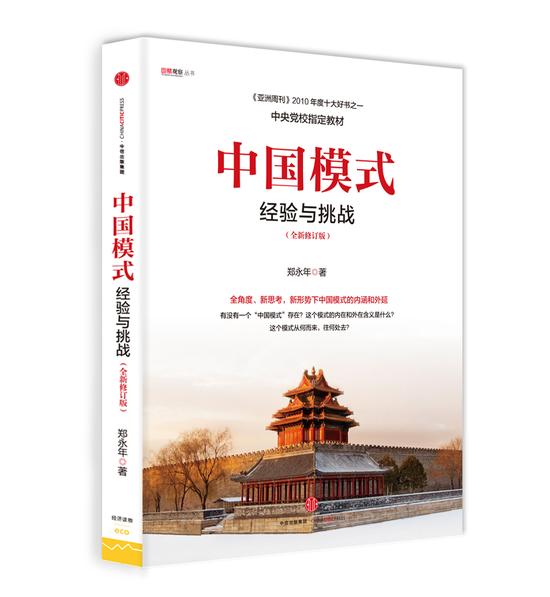









![郑经私通 郑成功被郑经气死? [趣闻]](https://pic.bilezu.com/upload/f/a8/fa8ca857ffb40a853da92e281ec569b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