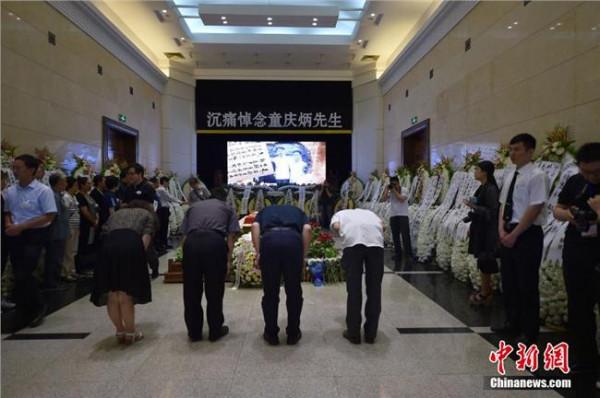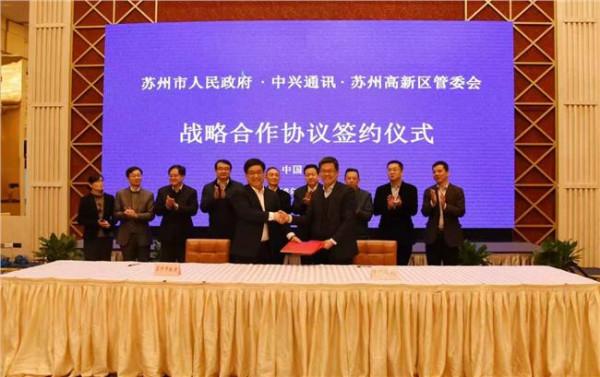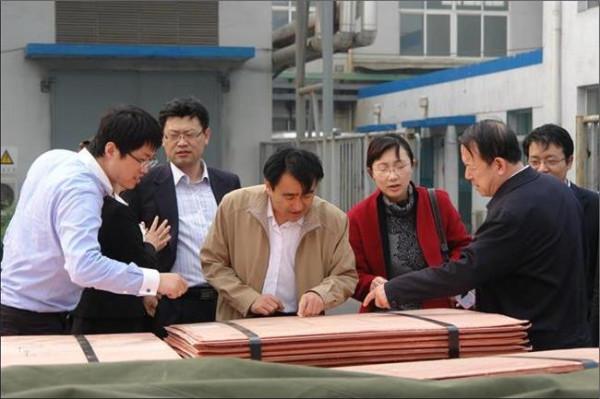徐童访谈 片场调研|徐童导演访谈
许金晶(下简称许):《珍宝岛》这个小说是写在拍纪录片之前,后来出版,对吧?
徐童(下简称徐):对,《珍宝岛》是2013年出版的,写的就是北京的城乡交界地带。在我上的学校附近,四惠桥往外,朝阳,沿着通惠河那边,有个地方叫做高碑店。高碑店那一带有成片的低矮的平房,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鱼龙混杂,街道上污水横流,两边是小的杂货店,各种五金店,农贸市场,鳞次栉比。
那个地方我非常熟悉,我就以那个地方的空间为背景,写了上个世纪末,各种底层的人的生活状态。时间跨了半个世纪。故事性是非常强的,不像纪录片那样散,故事丝丝入扣,是传统的叙事小说。
写完之后就觉得还不过瘾,感到文字不如影像具有强烈的冲击力。然后就用摄像机拍我熟悉的街上的那么一间小发廊,那小发廊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从河北跑到那儿去卖身救父。那时候拍了第一部纪录片。
许:徐导您曾提到毕业分配的时候被人背后捅刀,《麦收》里面苗苗最后也是被她的一个朋友出卖,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感触?
徐:是的,肯定是人生经历有这一块,这个细节就会捕捉住。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你的生活阅历积累之后,你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再去看别人的生活,就会更加敏感。现在年轻人缺的就是这个,他看到别人的痛苦感觉不出痛苦,看见别人的喜怒哀乐他没有那么强的感觉,因为他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个“酒”还没有酿好,等它酿好的时候,别人的悲喜你马上就能感受到。
许:我发现,您最早的三部作品就是“游民三部曲”,包括现在一些后续的,比如《挖眼睛》,去年应该是出了一部叫《四哥》的,一直没放,其实您一直在关注这些游民,这些流动人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群体有这种一以贯之的关注?
徐:从近的说,就跟大学毕业之后那个生活处境有关。那时候人人都有“铁饭碗”,少数人辞职不干。从我停薪留职,大概是1988年,去自谋生路,我对生存艰难的体会就一定比同龄人多很多了。无论是为了生活去奔波、去谋生的这种体验,还是说从居住地获得的那种生理般的直接感受,都格外鲜明。
往远里说,我是生在60年代,长在70年代,成年是在80年代。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差,生活非常艰苦。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很不一样,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
成人世界的争夺,多少也会映射到孩子的心里,比如说“批斗”啊,“运动”啊,谁是“坏蛋”,谁他爸是“右派”,谁他妈是“五一六”了什么的。这些事情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很深刻,那个时期的残酷性对心理多少都会有影响,就会让人对残酷性有一个比较早的认识。
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让我对底层江湖、对社会人很容易接受。第三个理由,和搞当代艺术那一段也有关系。搞当代艺术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只会学西方大师的作品,到后来接受一些后现代的思想,基本上就是左翼的思想,比如像美国的苏珊·桑塔格是我最喜欢的文艺批评家,她绝对是一个左派。
左派一个最明显的标签就是同情底层民众,这就导致了我在艺术创作当中往往是从同情底层民众的立场出发,由此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思想态度。
当然后来我又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包括写作、拍纪录片,对底层民众的了解多了,从一开始的同情、怜悯,到后来发现底层民众真正是一块无主之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于有时候是盲目的暴民。
这就是底层社会的复杂性,它是上层权利意识层层沉降的地方。我觉得它很值得表现。游民世界是一个隐性的社会,尤其是游民当中更边缘的,那些走偏门干黑道的,更应该记录下来。
这样,时间一长,感情也全部放进去了,游民的世界成了我最倾注感情的一块地方。你看像《挖眼睛》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情怜悯的问题了,很多人看了可能会有点感动,但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完全不希望你用简单的同情,去掩盖事情的真相,去把一个复杂的生命简化为一种政治正确。
感动于这样的人的悲惨遭遇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感动却不覆盖。实际上《挖眼睛》很复杂,这个人也不一定就是很值得同情的,他毕竟是要强占人家的老婆。
底层人的恩恩怨怨,也不是简单的靠正义就能解决的。底层的思想意识中有很多东西是迂腐的,甚至是非常反动的,因为他们是被长期愚弄的。比如说底层人最爱看什么,他们实际上不爱看《挖眼睛》,不爱看咱们这些纪录片,独立纪录片在底层没有人爱看。底层人爱看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底层人的梦想是成为上层人。
许:只有知识分子看。
徐:当然。关于游民这个话题怎么也说不完,因为最后还是关于人的处境问题。实际上《挖眼睛》也是在表现人,我们不去求证谁对谁错,而关键是在于一个人面临了这样的绝境,他怎么能够从这里面摆脱出来,还能够延续他的生命。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以死连生的故事。他的办法呢?完全靠的是负能量啊,这是底层人自我解脱的一个方法。
许:我看这届影展的画刊,选片人对你这个片子的点评和介绍,强调了这是对民间文学传统的追溯和回归。我觉得这种追溯其实在《算命》里面也有。您个人对中国传统的习俗和文化在江湖民间的传承和延续状况有哪些感受?
徐:上次在凤凰卫视和窦文涛聊的时候,他摇着脑袋,抑扬顿挫地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这东西实际上是没变,虽然说现在拍的是游民,有些东西似乎是跟传统文化相衔接,可能就像《算命》的那种叙述方式,包括像《挖眼睛》这种二人台的演唱,都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尽管这种形式不多见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是普遍存在的,我指的是它背后隐藏的游民文化。
社会的问题,使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生存,江湖习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甚至成为集体的一种规则,一种潜意识,一种心性。
江湖究竟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没有生活来源,没有资源,特别是作为底层人,身无长物,背井离乡,到外省去谋生,他往往靠的只能是一些江湖上的本领了,至少骨子里的这种江湖气就有了。
具体说来,游民之所以具有反社会性和暴力倾向,是因为他从原来那个宗法庇护的家族之中脱序之后,流落异乡,变成江湖人,他只能靠自己的个人奋斗,只能个性张扬,“三刀六洞”“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是这一套,以搏衣食,就得出狠招。
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让他摆摊,他就能跟你玩命,那些和城管对抗的极端事件,都带有很强的游民特征。一个卖西瓜的,他本身背井离乡,靠卖瓜糊口,养活一家老小,推着个小车,你这个地方不让人摆摊,把人西瓜全砸了,还要给人打一顿,那人家急了,只能是拿出刀来捅了城管,鱼死网破。
这就是把人逼到了墙角里,万不得已的时候,游民的本质就瞬间爆发出来了。在我的纪录片中,这些都有体现,像二后生那个片子,人物根本就没有法律的概念,就是他给我逼急了,我就给他眼睛挖了,实际上这些都属于江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看似极端的东西在今天还依然存在,有的还很有普遍性。
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一般人都是从比较浪漫的角度去理解了,仗义疏财,自由飘逸,该出手时就出手,这都是表面的东西,是诗化了。
我还是认同游民江湖的本质是野蛮性。这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的天性。不信有一天把你扔在一个没有保障的险恶环境里,你的野蛮性立刻会表现出来。
“文革”里的人就是这样啊,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决裂,这不是普通老百姓才这样,知识分子也一样,完全斯文扫地。另一方面,人性当中这块东西,也许是文明永远无法把它彻底地驯服的。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天然的破坏力,反体制反威权的冲动,是否具有革命性呢?我也在思考这个有点后现代的问题。
许:“游民三部曲”这些故事是怎么发现,怎么拍的?
徐:不是特意地选题去做的,不是先有一个游民的概念,我要拍江湖拍游民,再去找人物。如果是按这个逻辑去拍片,就容易把东西拍得死板,就会变成社会学的一个设题似的,这样是拍不出好看的电影的。简单地说,这个东西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的。
再加上你的生活,正好跟他们有交集。你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就跟他们相通了,拍摄是个自然而然的事。纪录片有这么一个特点,只要你的大方向是这样一群人,你在跟拍的过程中,故事总会发生,它就在那儿,跑不了。
许:细节不是想象出来的。
徐:用不着特意地想拍什么,不过大方向你要有。魔鬼藏在细节里,它是编不出来的。所以说纪录片不管作者用什么方式写作,它实际上是要发现,进入一个人群当中,成为这个人群当中的一员。你既是导演,又是这个人群中的生活者,一起生活,然后完成作品。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推一个,生活不断延续,作品也不断延续。是这么一个过程,边生活,边拍摄。
许:《麦收》自问世以来,一直面临着不小的争议。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徐:简单一句话,不断地加深对纪录片伦理或者道德底线的理解和思考,我觉得作者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控制范围。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出于正义的初衷,而损害了个人的利益。自由主义有一句名言,叫“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限”。
许:我们知道,形式本身也是内容的一部分。《算命》采用传统章回体形式进行讲述。这种讲述方式本身,跟片子的内容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徐:它跟片子的内容是非常贴合的。我感觉只有用章回体的方式才能把算命先生那种自古口口相传的手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也和我喜爱中国古典文学有关,拍《算命》的时候很容易联想起《水浒传》《三言二拍》之类,你不觉得“唐小雁棒打无赖汉”和《三言二拍》里的“XXX棒打薄情郎”是一回事吗?
许:在《算命》之中,厉百程试图去掌控和推算别人的命运,而他自己的命运却同样是随波逐流、求助神灵。作为拍摄者,您是怎样看待这种反差的?
徐:实际上我觉得对厉百程的这个设问有点问题。这个设问,他是一个算命先生,就该掌握别人的命运。但实际上,我所理解的,厉百程的算命只是他用以糊口的一门手艺,仅仅是一种谋生办法。他根本就掌握不了别人的命运,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的命运也掌握不了。
他给我的感觉始终是一个为了谋生在外边苦苦挣扎的残疾人。他没有任何神性、功力。有一些谋生的方式看起来很了不起,比如一些卖艺的,耍大刀的,练硬气功的,实际都不是什么高手,都是江湖把戏。你也不能说他坏,说他全是骗你的。那是他的一种谋生的手段,糊口而已。
许:我觉得《老唐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1957年就因为晚了几天,就被解职了。
这就成了他个人的一生,他的一个家族的转折点。我记得我写了一个影评,叫做“个人命运的偶然,时代命运的必然”。
徐:好,你的总结太好了,应该在这里用上。《老唐头》不只是说个人命运。为什么影片的英文名字叫“Shattered”,就是支离破碎,实际上还是一个折射,通过一个基层的农村的普通家庭的故事──儿女最后“鸟兽状”散去,老人孤独地等待着死亡,这么一个状况,折射出中国轰轰烈烈的半个多世纪,最后竟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存在状态。
许:在文章里我也提到,这个片子里有两个细节令我印象特别深。一个就是老唐头从
1946年挂的像一直挂到现在,然后唐小雁取下来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他还在画像边吹口琴,很浪漫很诗意的一个镜头;另外一个就是他本身就看不惯“大跃进”时候的那种浮夸,但是后来,他女儿说要拿回扣,他也是非常生气,要和她吵架。这两个细节非常鲜活,您当时是怎么把握到这两个细节的?
徐:纪录片不是由导演设计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物身上自然流淌出来的,也就是说老唐头这个人物,他像一个多棱镜一样,折射出不同的光谱:一方面他会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塑造,他被这种思想深深地禁锢住了;同时,触及他个人利益的时候呢,他又会猛烈地反抗,会为了女儿不顾一切了,并导致一生的改变,这是人性。
许:片子放出来以后,对片中人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徐:我一直希望多少有一些人愿意出来帮助他们。《算命》放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回,有一个观众直接站起来说能不能给老厉他们捐点钱,后来还真有一个观众把钱汇到我的卡上来,好像汇来了200多块钱吧,我就转给老厉了。
但你要说太大的改变,没有,这不是一个影片能做到的。放映是小众的,知识分子愿意看,我觉得这就对了。如果当官的愿意看就更好了,权贵、有钱的人都愿意看就好了,他们是可以决定别人命运的。我常说看见是改变的开始。同时,一个致命的关键就是这样的声音能不能有效地传达出去。
许:今天放的《挖眼睛》,我觉得有一个对比很强烈,就是一边放着欢快的流行音乐,一边讲着二后生的凄惨遭遇,这种对比的设置,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考虑?
徐:这也是自然而然的。我始终相信,纪录片是可以做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浑然天成,纪录片没法去设计。他(二后生)既要娱乐大众,有些娱乐性的音乐舞蹈,就是他们那些演出,同时又有自己亲身遭遇的倾诉。他眼睛被挖之后的四十多天住在医院,只有2000块钱,这些钱用完了,之后医院就给他轰出来了。
他的哥哥也是瞎子,当时到医院来看他,他本以为哥哥能给他带点钱过来,让他继续治眼睛,但哥哥来了之后对他说,兄弟啊,我也没办法,我只给你带来了这个──卖唱用的竹板。
从此,他就开始在医院门口唱自己的经历,据说他唱的时候包着绷带,头肿得像篮球这么大,声音也非常弱,但透过纱布,眼泪还能流下来,血红色的一片。那种惨状真的是无法描述,像这些东西真的不是能导演出来的。
后来他就一直唱,经过长年的重复,他就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唱得非常的合辙押韵,故事的起承转合全都在肚子里了,这就是他唱的《挖眼睛》。所以像这种东西都是人物遭遇,经历给的。后来他用乞讨来的钱慢慢恢复了,等他基本上好了,这个《挖眼睛》的曲子也家喻户晓了。甚至后来就纯是挣钱了,所以也有观众看完片子说二后生是靠揭伤疤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