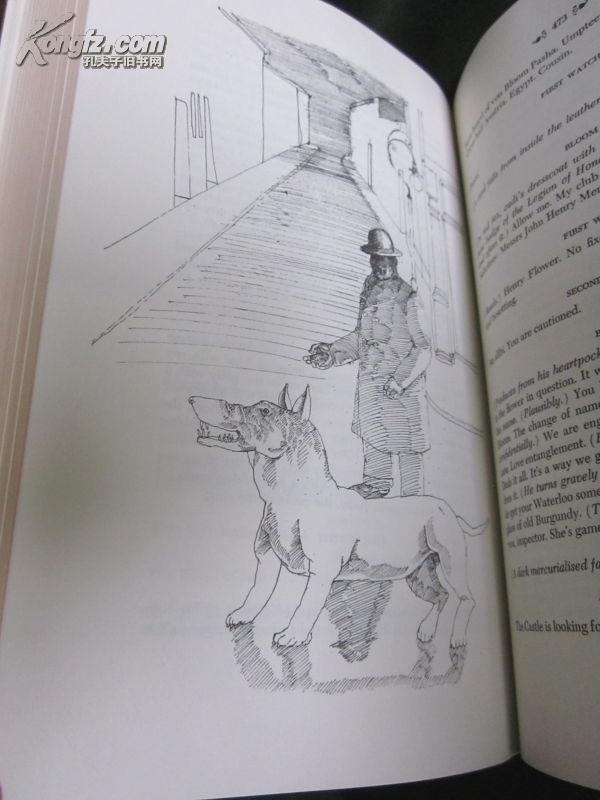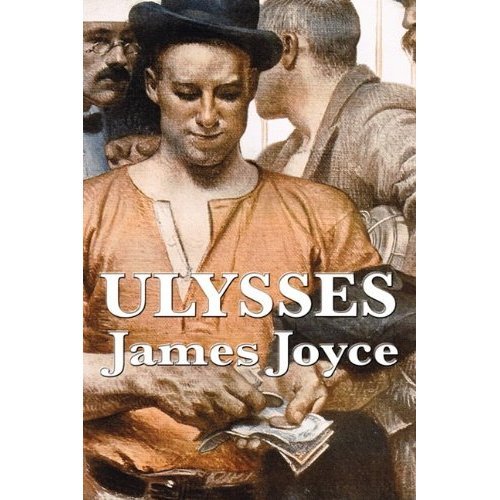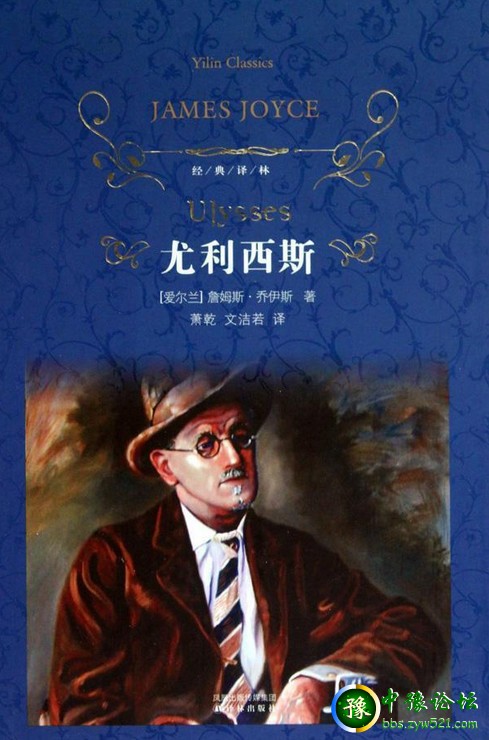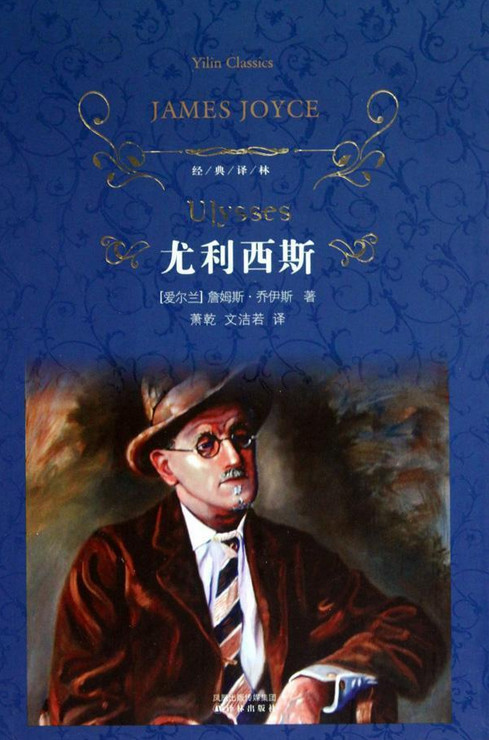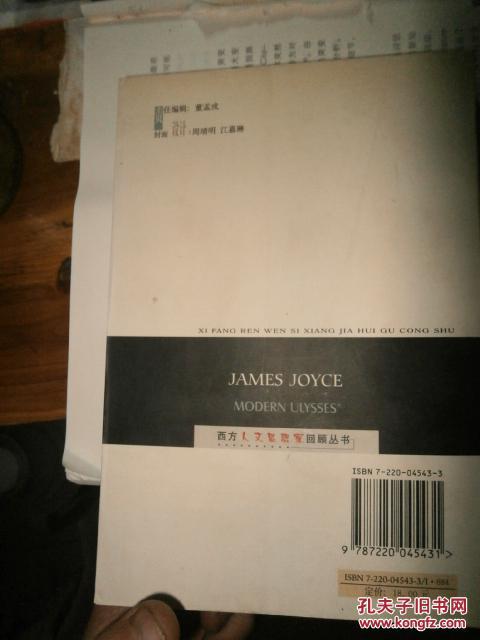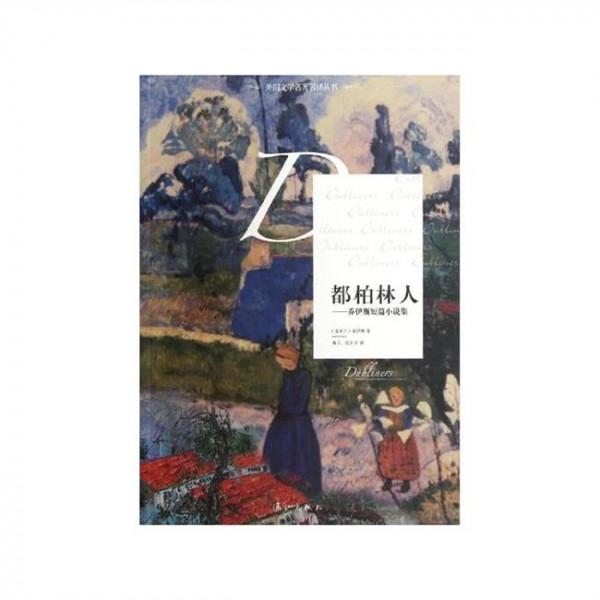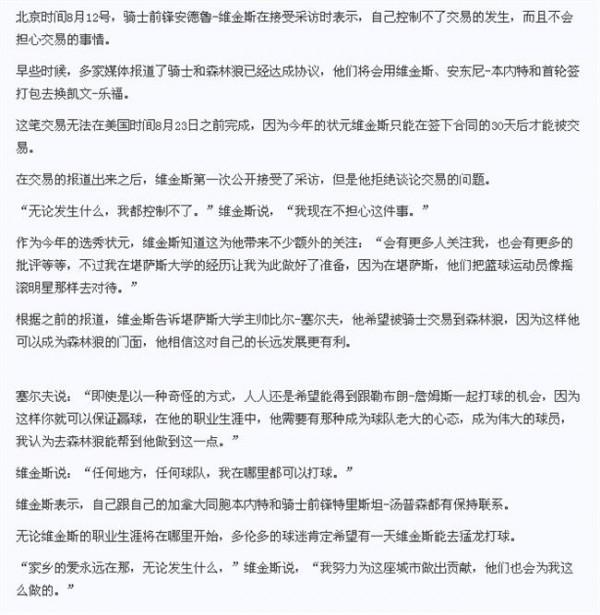乔伊斯尤利西斯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隐喻
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其文学生涯始于他1904年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他的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詹姆斯·乔伊斯这样,被谈论得如此之多,被阅读得如此之少。对于乔伊斯作品的价值、乔伊斯本人地位的评论,争议与差别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不少作家和评论家认为,乔伊斯对现代小说、现代文学乃至对现代艺术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可以从小说技法的创新与探索、人物意识的深度与层次、处理经验世界的角度与力度等向度出发,把文学分为“前乔伊斯时代”与“后乔伊斯时代”。
在他们看来,与同时代的卡夫卡、普鲁斯特、穆齐尔,稍后的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为数极少的作家相比,乔伊斯即使不能被视为更伟大,至少也能和他们一起,毫无疑问地跨入与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并列的层次,成为永远被人类阅读与崇敬的光辉圣徒。
但另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在谈论乔伊斯时却犹豫得多。他们认为,阅读者每说出一句关于乔伊斯作品的话,都会像强迫症患者一样自问:“他是这个意思吗?”也必然会面对别人的疑问:“你读懂了吗?”读不懂,是乔伊斯面临的最大指责。
晦涩,不是乔伊斯的特质。但只有乔伊斯的晦涩,会让人恼怒。更何况,迄今对于乔伊斯的评价与争议,都还只是建立在几乎不触及他最后一部作品《芬尼根守灵》的基础上。这部被博尔赫斯称为“没有生气的同形异义文字游戏的编织物”的作品,其意义与价值早在写作过程中,就受到庞德等乔伊斯同代人的怀疑,他们曾对作者进行规劝,认为他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浪费自己的天赋与才华。
乔伊斯的妻子诺拉则干脆恼火地斥责道:“你就不能写一点别人看得懂的东西?”
不过,那些指责乔伊斯的人也知道,仅仅因为晦涩指责他总有点儿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他们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反对对乔伊斯的“高估”。他们同意乔伊斯是20世纪、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但他是否可以被称为“小说家”却是个问题。
有人说,乔伊斯笔下的一切都来自他的生活,他所有让人们惊叹的地方都是原封不动照搬他本人或身边人的经历,这只能证明乔伊斯有着非凡的整理能力,不能证明他的创造力,尤其是作为小说家所必须的想象力。
发生在乔伊斯身上的不少轶事似乎也能对此提供佐证,经常被提到的就有两个。其一,诺拉写信不爱区分大小写字母,也不使用标点符号,乔伊斯把这一点视为“女人的特征”,并把它搬进了《尤利西斯》,写成了莫莉那没有标点、一气呵成的独白,从而被视为小说史上标志性的创新;其二,乔伊斯创作《芬尼根守灵》的时候,更为经常和直接地从生活中拿东西进来。
有一次他向贝克特口述时,有人敲门,贝克特没有听到敲门声,乔伊斯说“进来”,贝克特就写了下来。后来贝克特把所作的记录读给乔伊斯听,乔伊斯说:“那个‘进来’是怎么回事?”贝克特说:“是您说的。”乔伊斯想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吧,不用改了。”
对于这两种指责,乔伊斯非常清楚。他根本没有把“晦涩”当一回事,认为自己只是使用了小说需要的技巧,有的时候,他更是故意制造阅读障碍,以让读者陷入语词迷宫为乐。对于第二种指责,乔伊斯也很少给出针对性的回答,更别提为自己辩解了。
他最常见的反应,也只是给出似乎在应和这一说法的自嘲、自贬性的评论。1921年6月24日,在给维弗小姐的信中,他就称脑子里的《尤利西斯》素材为“从各处捡来的鹅卵石、垃圾、折断的火柴以及玻璃碎片”。在和尤金·乔拉斯谈到《芬尼根守灵》时,他也说:“这本书,是我遇见的人、我认识的人写成的。”似乎他的小说完全是现实世界中的可见之物,他做的不过是把它们捡起来,拼装好而已。
乔伊斯的自评无意间掩盖了他作为一名小说家最杰出的贡献:如何从自身的经验世界创造出全新的世界。看起来,这是一个毫无意义、或者说同语反复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小说家处理的都是经验世界,至少也是以经验世界为根基的。
但乔伊斯的创举在于,身边的一切都被纳入了他的经验世界,前面所说的“鹅卵石、垃圾、折断的火柴以及玻璃碎片”既有引申层面的意义,更有实际层面的意义。乔伊斯仿佛有着强大的磁化能力,身边所有的东西都被他看到,都被他磁化。
他构思小说,就像在制作一个个特别的、有着不同甄选标准的筛子,这些磁化的经验倒在筛子上,一一筛过,通过的就是需要的。乔伊斯再以看似随意、实则胸有成竹的方式把它们放到应该去的地方。经验世界的扩大是乔伊斯的基础,他最根本的创造在于,还世界以经验的本来面貌。
这并不是说乔伊斯与其作品不关注超越性的东西,不关注超越个人经验之外的普遍性。没有多少作家对人类的命运与处境的关注达到乔伊斯的深度。但是,乔伊斯的关注采取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他不是要从自身经验中提炼出普遍原则,而是把文学中常见的戏剧性处理、超越性观照、普遍原则通通化解,把这一切编织进人物、或者说他本人的经验里。他对经验的处理,有些像亨利·摩尔雕塑作品对物体表面的处理。
那些雕塑身上有很多个孔洞、缝隙、入口,但是所有这些从表面进去的通道,依旧从表面出来,并且自身也成了表面。呈现出来的、看得到的,永远只是表面。经验这件皮袄在乔伊斯手里,翻过来还是一件皮袄。他固执地在个人经验上堆垒一切迎面碰上的东西,直到这个经验的世界庞杂无比、深不可测,成为世界与人本身的象征和缩影。
我们看到的一切,是一面无边无际的镜子,我们身在其中。我们的看,正是我们漂泊的一种方式。当乔伊斯第一次想到“尤利西斯”这个小说题目的时候,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花费自己9年的时光。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尤利西斯”这样一个漂泊的形象,经过他的处理之后,成为了一个绝佳的隐喻。这个形象身上,有着太多的东西可以被当成现代小说家(现代艺术家)本人。
其一,他是经验层面的永恒漂泊者。这种漂泊是自足的。现代艺术家已经被逐出乐园,他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讲述着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神话和故事,仅仅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少许调料就心满意足。那些简单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的情节,也已经不能成为他们的依靠,因为他们再也不能用这面镜子照出自己的样子。
他们要做的和感兴趣的,就是获得经验,拓展经验世界的边界。有时候,这仅仅取决于他们是否换取了一个新的角度。他们似乎不深入这些经验,当人们感叹从这些经验上看不出深度的时候,他们会严肃地说,本来就没有深度,或者说,你看到的就是深度。
在他们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深度早已经被令人绝望地证明是虚假的,而他们发现、提供的经验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深度。他们相信,他们的漂泊本身就是这种深度的体现。
他的漂泊也是寻找读者的过程。现代主义之前的艺术家们不需要寻找读者,他们是广义上的说书人,所有的听众都入场了,他们才开说。他们说的一切,或许与听众的经验层面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听众都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容。现代艺术家不然,舞台早已垮塌,人群早已散去,他们需要大声吆喝才有可能把人们聚到自己身边,但围过来的人未必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流浪,希望有一天能碰到称心的听众,他能支持自己把故事说完。最好的情况下,这个读者还能是一个对话者,激励作者的创造力。
乔伊斯的一生,也是在寻找这样的读者。几部作品带来的信心,让他能够在自己身边摹拟出读者来,自己能够分身出读者来,以自说自话的方式,坚持完成《芬尼根守灵》的创作。否则,他要么疯掉,要么像卡夫卡一样,要把自己的作品烧掉。
荷马笔下,尤利西斯(奥德赛)在海上漂泊,与阻止他回家的一切东西抗争。然而,他的心里充满着希望和甜蜜,因为他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他也完全想象得出,那个目的地的样子,那儿会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在等着他。一路上,他有痛苦、有眼泪、有拼搏、有危险,但是希望不变。
乔伊斯笔下,尤利西斯(布卢姆)没有目的地,也可以说,他就是在目的地漂泊。他不知道该与什么东西抗争。但是如果我们循他的漂泊之路而去,我们能看到这一路上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