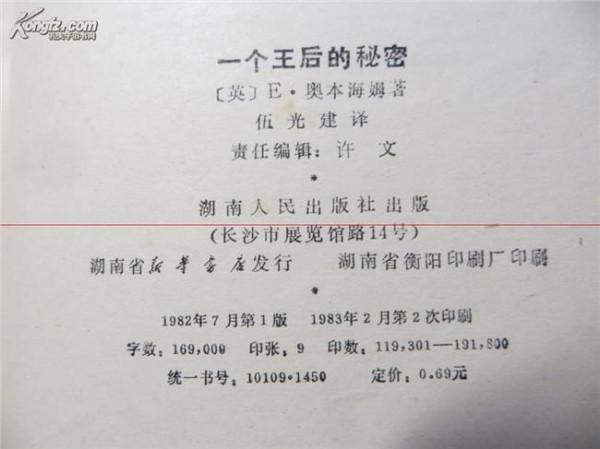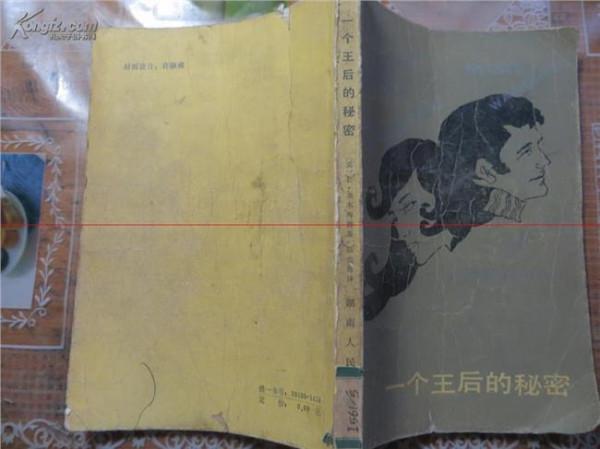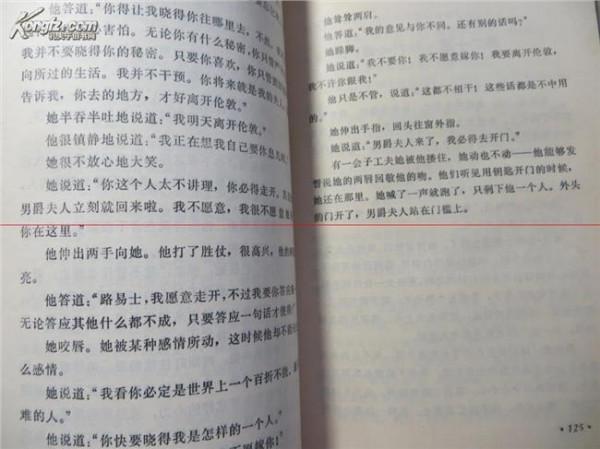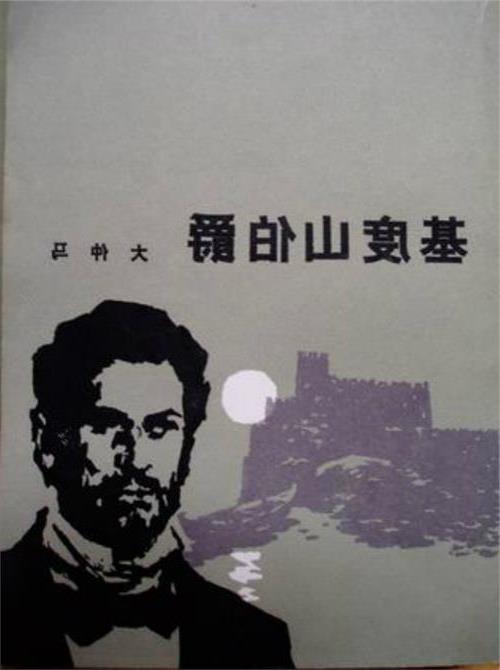翻译家严复 步严复后尘的翻译家:伍光建名字不应被遗忘
1877年,严复等人被派往英国,专门学习驾驶兵船技术。起初,他们是在抱士穆德学校接受以英文为主的预备训练,随后进入著名的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系统的海军知识。严复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努力钻研高等算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诸学,最终取得“考课屡列优等”的优异成绩。
出洋留学使严复一下子眼界大开,结合早年在国内军舰上的实习经历,严复开始思考中国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才能走上富强之路。
因此,他没有仅仅局限于对舰船知识的学习,而是逐渐对英国的社会组织和各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走出校门,去法庭看审判,进议院听辩论,到居民区观察基层社会组织,和同学们一起参观工厂、学校、商店、博物馆等,总之,严复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英国社会,努力地“开眼看世界”。
在他阅读的书籍里面,有关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学术著作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作品,他都涉猎过。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知识不断地充实着严复的头脑,他也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为自己苦苦思索已久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1879年,因福州船政学堂急需教师,严复被调回国内,出任学堂教习。1880年,严复又被调往天津,任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开始长达20年的执教生涯。当时的学堂总办虽为吴仲翔,但实际工作均由严复承担。
由于受到过正规的海军教育,研究过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学说,因此严复在办学的过程中,大胆吸取英法等国同类学校的成功经验,对学制、课程设置及教学环节都做了详细规定。他极为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结合,无论驾驶还是管轮专业,学生都必须进厂或上船实习。
他对学生的考核十分严格,学生只有堂课考试合格,才准予上船。严复办学以掌握世界最新技术为目标,因此坚持派遣学生到英、法等国留学,以接受比较先进的专业训练。
在执掌北洋水师学堂教务的同时,严复坚持系统阅读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并从事大量的翻译写作工作。由于向中国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严复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学的第一人。
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法》)、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自由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社会进化简史》)、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
由此,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得以进入中国。严复的译著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无论译文还是按语,都渗透着其探本溯源的治学精神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体察。
在那个梁启超形容为“学问饥渴”的年代,严复的译著令人耳目一新,他试图引领人们将目光投向英、法等国“船坚炮利”的背后,察看导致这些国家强大的社会原因,探究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他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对传统旧学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产生猛烈冲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人们所接受。以《天演论》为例,这部书从翻译到出版刚好经历了维新运动高涨时期(1895-1898年),一经问世,便引起思想界的轰动。
梁启超在《天演论》出版之前就加以宣传,康有为也称“《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1898年,该书出版后,有的学校教师往往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题目,青年们更是争相阅读,对它爱不释手。
鲁迅回忆自己读《天演论》时的情形:不仅觉得书中“写得很好的文字”,而且“一口气读了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底)、柏拉图也出来了”。严复所宣扬的进化论思想连同科学理性精神、民主思想不仅影响了戊戌维新运动,而且也对后来者们寻求救国真理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难怪鲁迅称赞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除了执教北洋水师学堂、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外,严复还在《直报》以及自己所创办的《国闻报》上发表过大量时事评论文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宣传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理念。
后来他还担任过复旦公学校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凭借着对西学和中学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长期从事的教育和翻译活动,严复一直希望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陈宝琛在严复的墓志铭中说:“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
在严复所培养的众多杰出人才中,伍光建的名字不应被遗忘。因为他与严复既为师生,又同为著名翻译家。伍光建(1867-1943)是广东新会人,19世纪80年代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师从严复,接受了十分严格的外语和专业训练。
毕业后,他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五年,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天文等方面的知识,兼学欧美文学。归国后,伍光建到北洋水师学堂教书,并开始钻研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学问。1905年,伍光建随载泽等人前往西欧和美国,考察西方宪政,对西方政治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回国后,他陆续编写了物理、化学、英语等学科的教科书,如《帝国英文读书》(五卷)、《英文范纲要》、《英文习语辞典》、《西史纪要》(二卷)等,前二者还成为学部审定的教科书。
多年的留学生活和严格的专业训练使伍光建具备了较高的英文阅读和听说能力,这为他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从事翻译活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持续50多年,所译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各类书籍大约130种。
甲午战争之后,维新运动蓬勃展开,伍光建应邀为汪穰卿在上海创办的《中外日报》撰稿。该报通过社论、副刊、插画等形式针砭时弊,揭露官场腐败,关心民众疾苦,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那时,林纾的“古文改写”式的翻译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流传极广。
伍光建所译作品,则改用白话,署名“君朔”,陆续在《中外日报》上发表,令读者耳目一新。针对人们渴望更多地了解西学新学的实际需要,伍光建选译了一些体现进化论观点的作品。他曾坦言,当时较多取材于英国弗劳德的《大问题小议论》,读者最喜爱的是几篇寓言故事,例如《母猫访道》,讲的正是当时中国读书人所向往的“新学”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辛亥革命之前,他的白话译作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仍署名“君朔”,其中以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二十年后》)译笔生动传神,而深受读者欢迎。20世纪2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茅盾评注本《侠隐记》,收入《万有文库》,并作为高中学生语文自修读物,起过良好作用。
胡适、曾孟朴、徐志摩等都很欣赏伍光建的译笔。徐志摩曾约他为新月书店翻译英国启蒙时期的剧作家谢立丹的作品《造谣学校》和《诡姻缘》,胡适约他为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翻译吉鹏的《罗马衰亡史》。上世纪30年代,伍光建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美、德、英、法、意、俄、瑞典、丹麦、挪威、西班牙等国40余种小说的节选本。
伍光建的翻译数量十分可观,选题广泛,视野开阔。他认为“了解西洋,介绍西洋,不等于盲目崇拜西洋”。为了让读者看到西方国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也将有关小说翻译过来,以便中国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西方。除了大仲马的作品之外,伍光建还翻译了狄更斯的《劳苦世界》(《艰难时世》)和《二京记》(《双城记》)、斯威夫特的《伽利华游记》(《格列佛游记》)、夏落蒂的《孤女飘零记》(《简·爱》)、雨果的《海上的劳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恶与惩罚》(《罪与罚》)、塞万提斯的《疯侠》(《堂吉诃德》)等。
传记方面则有福雷的《拿破仑论》和路德威格的《俾斯麦》。晚年的伍光建,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翻译了一些哲学、历史方面的著作,例如麦尔兹的《十九世纪思想史》、基佐的《法国革命史》、麦考莱的《英国史》等。伍光建翻译的文学作品通俗易懂,颇受大众欢迎,他因此在中国翻译界享誉盛名,赢得“翻译界之圣手”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