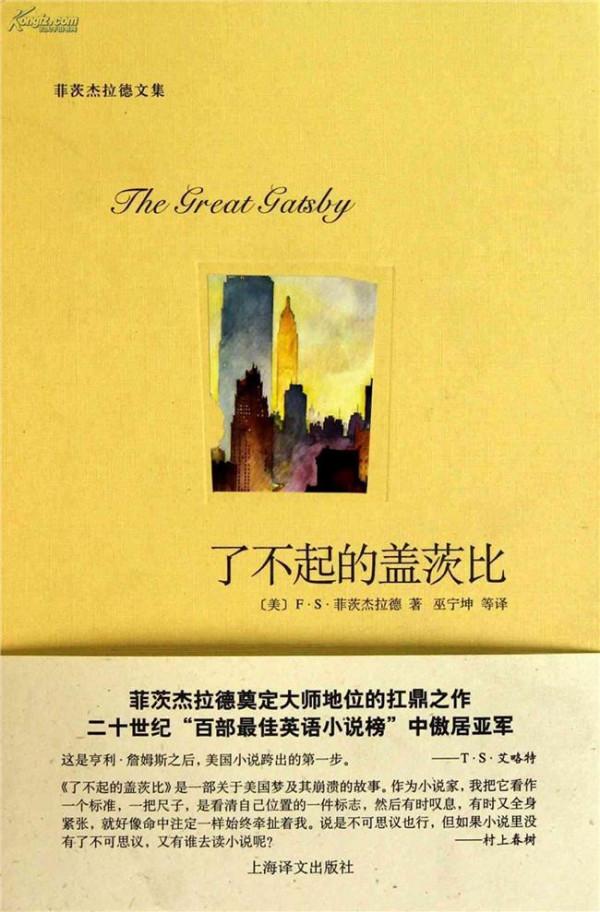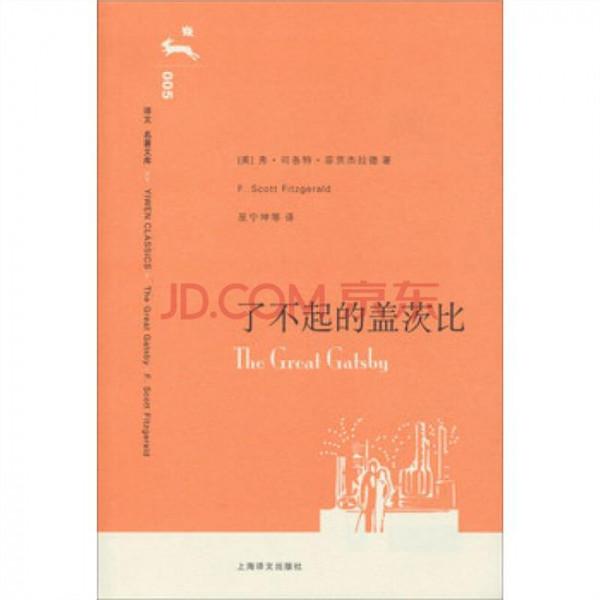巫宁坤一滴血 巫宁坤:《一滴泪》“我归来 我受难 我幸存 ”
《看历史》文│李怀宇 劫后余生的巫宁坤用一句话概括他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他的个人史,也是同时代诸多知识分子的苦难史。 第一次见到《一滴泪》一书,是在余英时先生家里。《一滴泪》伴我度过从普林斯顿到耶鲁再到波士顿的火车时光,我深为巫宁坤先生的故事感动,几欲落泪。
到了哈佛大学,我决定访问巫宁坤先生,一问余英时先生,原来巫先生住在华盛顿,再问我在华盛顿的朋友谭加东,原来他们是忘年交。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2007年12月6日晚饭后,谭加东开车带我来到巫先生家。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一句话都会笑。
我感佩《一滴泪》中笑对苦难的豁达气度,“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一句使我心灵如同触电。巫先生笑道:“余英时先生让我写关于思想改造的历史,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所谓‘心史’,特别是人的灵魂的受难。
我最近发现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狄兰·托马斯写的就是人的灵魂的受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那是最高级的人的灵魂的受难。《呼啸山庄》写的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所以才有价值,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则根本看不懂。
”《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联大生活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我说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巫先生便取出一封汪曾祺的毛笔信让我欣赏。
“曾祺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这两天刚整理出来他给我的信,他送过一张最好的画给我,就是昆明的雨。这封信是讲怎么画昆明的雨,很珍贵,用毛笔写的,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圆珠笔或钢笔了。
”他悠悠地回忆,“我们是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在那儿真是朝夕过从。后来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
我们写出来都是互相先看一看,投稿出去,拿点稿费吃馆子。” 我好奇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巫宁坤说:“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本字典去卖掉,一起吃饭。
这恐怕是后来的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当时我们就觉得曾祺才华在我们之上,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我在茶馆里看的,好像是发表在《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平明》上。
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稿子,特别是罗隆基夫人王右家当主编的时候,她很喜欢我写的诗、小文章。” 我访问过的何兆武、杨苡、方贵龄都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巫宁坤在西南联大读了一年半,杨苡和她哥哥杨宪益都是他的好朋友。
巫宁坤回忆:“那时大家生活过得很苦,可是情绪都很高。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欣赏文学,所谓文艺青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
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也不是每个教授都教得很好。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师生的接触超出了教课的老师,好像沈从文、卞之琳没有教过我,可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教师。
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我也是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吴宓。” 我问起沈从文的旧事。巫宁坤说:“沈从文先生没有架子,我跑去拜见他,他总是欢迎的。后来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现沈先生原来跟我是亲戚,他的太太是张家的,我的姨妈就是她的婶母,所以后来他送给我书的时候,就写‘宁坤表弟’。
我非常喜欢沈先生的作品,我到了北大荒还有机会读他的《边城》《湘行散记》。有一个跟我一起的人是沈先生过去的学生,他带去了沈先生的作品,我们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他的书,一边劳动,一边谈。
沈先生的书鼓舞人心。” 巫宁坤也与卞之琳时相过从:“我的外国文学都是亏他给我介绍,每次他都给我几本书看,对我影响很大。
”我即刻说:“我到耶鲁访问了张充和女士。”巫宁坤笑道:“充和是我的表姐。卞之琳追张充和追得很厉害。原来在北京就追,到了昆明还追。卞之琳后来到英国,我在美国,他给我写过信。多年的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张充和嫁给傅汉思了,他很伤心。
八十年代以后,我每次到美国,他都让我带书送给张充和。我到张充和家去过,就是因为卞之琳让我带书给她。” 我问:“您在西南联大的兴趣在哪里?”巫宁坤说:“就是看书写东西。那时候想写诗,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胡写,因为我的老师也鼓励,就想学点英国文学。
我那时候会英文,法语刚学了一年,本来读下去的话,法语要学三年,那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了。说实话,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学过许多东西,都是看书,都是卞之琳借的那些书,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
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又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你听说过杜运燮吧?老杜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老杜写诗很有意思,一天一本小笔记本。
我是一天一首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当不了诗人。” 至于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巫宁坤说:“我们在高中有英语课,到了西南联大,大一英语就是一本英语课本,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英文散文,一门叫英文诗,至于小说,还没有碰到。
我跟吴宓先生学了一年,他教欧洲文学史,这是外语系的必修课。他当然有大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乡土情怀 1941年,巫宁坤在西南联大只读了一年多,毅然到空军当英语译员。
“因为飞虎队到中国来了,我是第一期翻译班,是战地服务团办的。那时候要学英语,而且我要抗战,美国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去吗?我跟杜运燮同时报名,当时外语系只有我们两个报名。
”巫宁坤回忆,“我在1943年12月到美国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所以飞行人员就送到美国来学习。我在机上当翻译。打完仗,我第一个辞职。学英语还要回去啊?当然在美国学了,就留在美国读书,原来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又学了一年多,就毕业了,1948年拿到学士学位。
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留下来念博士学位。” 1951年夏,巫宁坤为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候选人,正在写博士论文,应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回中国任教。
谈起当时的想法,巫宁坤说:“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在美国时,中国的亲友不断来信劝巫宁坤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
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而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教书最主要的促使者是赵萝蕤。
两人学的是同一个文艺理论,皆属芝加哥学派。巫宁坤说:“她是非常温和的人,很听话,时代变了,就跟着走,不是对着干的。她亏得是这样,本人吃的苦就不多了,当然后来她丈夫陈梦家自杀了,她自己也变成精神分裂。
她写了陈先生简单的传记,在国内发表,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我对陈梦家先生的遭遇深表惋惜。巫宁坤说:“陈先生的学问当然很专了。他不像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当然看得起的人很少。陈先生当年是新月派主要的人物,后来又搞文字学又搞考古学,他的成就是全世界都承认的。
赵萝蕤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留在美国绝对没有问题,她赶回去了。陈先生以他的考古学成就,在美国教书也没有问题。他们很爱国,乡土情怀非常浓。
” 临回国前,李政道去送巫宁坤。在北京,巫宁坤还可以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时代》《生活》杂志,得知李政道在国际学界大获成功的新闻。《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再教育 中断研究二十年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就被调去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当翻译。
一起工作的有卞之琳、朱光潜、钱锺书、李赋宁等人。巫宁坤回忆:“我那时候有情绪,觉得让我翻译这东西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吗?钱锺书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就是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人物。
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上班。” 我问:“您在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巫宁坤说:“那当然是很自由,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
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教书。同在南开大学教书的有著名教授雷海宗,巫宁坤回忆:“我是因为政治问题没搞清楚到南开大学去。
雷海宗跟郑天挺都是北大、清华的大教授,而且很有名,很有学问。翦伯赞要当北大历史系的主任,把雷海宗放在那里怎么行呢?翦伯赞的威信怎么树立起来呢?因此把雷海宗搞到南开大学去了。
后来评教授的时候,郑天挺评了一级教授,雷海宗才评了二级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教授。 我问:“穆旦(查良铮)在南开大学的时候也是郁郁不得志?”巫宁坤说:“那当然了,南开大学的人应该是有些自卑感,怕别人比他们强。
我们新来的人都要受他们的排挤。”我说:“穆旦的诗后来被推崇得很高。”巫宁坤说:“后来说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这话当然有道理,他的诗写得好。
” 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极右分子”,送至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文革”期间,全家流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问:“像在‘反右’、‘文革’这些大关口,心理上怎么挺过来?”巫宁坤说:“许多人碰到一件事情,挨整了,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整到我?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为什么不能整我?而整别人?起初我还在怀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追求进步。
吴兴华可惜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锺书啊!
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我很痛心,因为我是很喜欢吴先生的,我们一起打桥牌,他讲话有时候也露锋芒吧。环顾左右,就是那个情况,很多人起初也是没有办法,那就跟着走吧,像政治学习很多人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再发言,就是怕被抓住小辫子。
我在南开大学的时候,还是觉得总要让人干事情,后来到了‘反右’才发现,左右这些人,他们是为虎作伥。”《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我要自由的文学” 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改正,返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
巫宁坤又见到许多老朋友:“赵萝蕤还有联系,穆旦全家一直也有联系。我一回去,钱锺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
我们东拉西扯的,你不用提话题的,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 巫宁坤觉得到沈从文家特别舒服:“沈先生从前住在一间西晒的破房子,后来给了他两间也很小,最后他才分到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
他是到历史所去当研究员,他的级别恐怕不会比我高,他是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人家不管这些。” 当时汪曾祺《沙家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巫宁坤回忆:“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压抑,他喝酒,是酗酒。
你别看他那儿很热闹,谁来都行,他是那么聪明的人,看透了这些表面的文章,很寂寞。” 而对自己二十多年有没有机会做学术研究,巫宁坤笑道:“无所谓嘛,我们的灵魂在受再教育。我后来也写不出来了。脑子真正松开恐怕要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在成都会议上讲了一番话,那很有意思:我要自由的文学。
余英时非常欣赏这段话。实际上我们不懂政治,现在很多内幕出来了,我们是一无所知,就是周一良说的书生本色。 周一良后来也忏悔了。
穆旦被批以后,在他们家就变成划清界限的对象了,穆旦的太太是周与良。周家有很多党员,所以对穆旦很看不上眼,穆旦后来变成‘历史反革命’了,周家可能也没有人去他的追悼会。周一良到晚年,是坐着轮椅到穆旦坟前去忏悔。
周煦良是我的好朋友,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从扬州跑出来,跟他坐着同一趟火车,他和他未婚妻要到四川大学。后来他在华东师大,‘文革’结束以后,他到北京去开会,我陪他去看望周一良。周一良当时问题还没有解决,情绪很大:‘我有什么问题,叫我检讨这个检讨那个,我有什么好交待的?!
’” 历史奇妙地让巫宁坤做起了翻译的工作。我问:“您怎么翻译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说:“1980年,是《世界文学》找我翻译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当时是受批判的人。
限我两三个月交稿,当我是翻译机器似的。我在五十年代也翻译过一些东西,都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我自己没有做翻译家的愿望,也没有翻译家的本领。” 我又问:“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是怎么回事?”巫宁坤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让我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
我寄给他稿子以后,觉得自己翻译的实在不好,就给他写信:你退给我吧,你找王佐良翻译好了。
袁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是你。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那样我就算了,后来隔了多少年后,香港有个诗人叫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把余光中的翻译贬得一文不值。
我是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能把话讲得过头。他很强硬: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反驳的文章登出来。可网上有些人写了,都同意他,觉得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 1982年,受加州大学的邀请,巫宁坤到了美国。从此他的履历有了这些记录:1982年至1983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员,1986年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人文科学名誉博士,1991年曼彻斯特学院驻校学者,1992年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客座教授。
晚年定居美国,巫先生多写书评和纪念性的文章,小说家哈金每本书都会送给他,由他写书评。“现在余英时先生叫我收集起来,在台湾出版,他觉得这些很重要,应该把它结集出版,这书叫《孤琴》。
”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
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一滴泪》《孤琴》,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