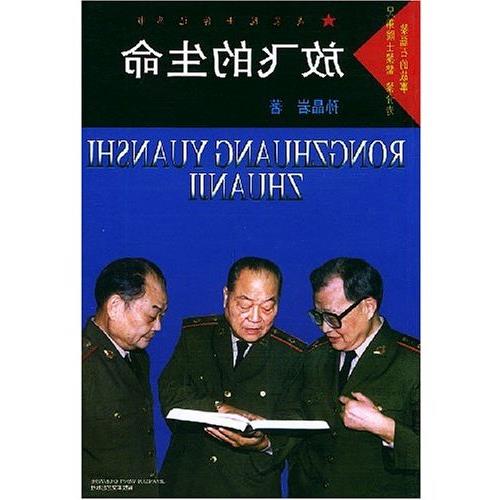黎磊石为何跳楼 [访谈]黎磊石院士如何培养人才
研究所发展的奥秘
的确,我们研究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科室,发展今天这个全国最大、实力最强的肾脏病研究所,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40年的道路,西方1960年组建这个专业,我们1980年才开始,到今天,我们与世界肾脏病发展的脚步相合拍。
秘决在哪里?90年代初期,部队卫生系统一些老的首长,总后卫生部部长张立平等,到南京来看了,说我们有个研究所现象,主要的是我们有研究所的精神,包括:一是有个使命感,就是原来没有肾脏病专业,后来301也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刚开始肾脏病是一个空白,但病人又很多,很痛苦,往往又很年轻。
我们作为医务人员,越接触多,思想感情震撼越大,这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肾脏科年门诊量十万多,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还是有很多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得不到应有的健康,病人的要求和我们为病人提供的服务相差很大。刚开始,我们肾脏科只有几张床,后来越来越多,我们透析原来只有一台机器,现在有80多台,我们移植原来是没有的,现在也是重点移植单位。
所有这些,都是不停地往前走,为什么?我们没有停下来的可能,我们永远有压力,病人的眼光、病人的痛苦,始终在我们心里拂不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伤病员服务。
第二,我们的发展得很快,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是借了改革的东风,我们研究所创立的时候,正好是1979年,改革的思想带领我们走出去,请进来,与我们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当时的家底是 1万块钱,现在几个亿没有问题,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像人才,一个院士值多少钱?一万块20多年后可以变成上亿,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绝对不可能。
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从物质上来讲,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好的技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还给我们提供了解放思想,给我们敢于做前人没有能的事。
现在研究所有好多个世界第一,这个在过去就不可能出现,现在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研究所在国内第一个成立了移植中心。1993年刚搞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没有技术,什么也没有,总后来检查工作,王局长带着专家检查,说我们总院肾脏病科做肾移植,那是狗拿耗子?没有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也不敢做,现在成功了,全国都在向我们学习。
肾脏病研究所发展到今天,上级提供给我们的投入很少。
机器从哪里来,人家不要的东西,我们拿过来修修补补,派上了大用场,这些东西,一批从美国来,一批从澳大利亚来,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向人家要来的。一批我们出了运费,一批我们连运费都没出。这些机器到我们这里后,我们就马上应用到病人身上,就获取了经济收益。我们没有要上级拔钱,而且我们给上面创造价值。
第三,与我们这支队伍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支队伍是优秀。好在哪里?一个是梯队搭配合理,所有的人才都是从这个航母中打造出来的。留洋的人才不多,几乎全都是从这个鸡窝里走出来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在全军、全国都找不到像我们这样干的,我们每周两三个晚上组织学习和学术活动,只要通知一下,大家都来。
前段时间,我们专门给护士和技术员上课,连续一个多月,每周四天,大家都来。这些是其它有些单位学不来的。现在的年轻人,晚上还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我们这里已成了习惯。
院里要求过双休日,我们就行不通,全体人员都是星期六要上班,都是自觉的。所以说这支队伍是好。好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1986年,总后要调我去北京,叫我去301医院,于永波说,老黎,调你走啊,我说我不去。
我说我愿意去为他们开创肾脏病,我希望这个专业能够很好地为部队、为人民服务,但我舍不得这支队伍。所以达成一个协议,兼301医院的肾科主任,就这样,我一个礼拜飞两次,把 301医院的肾科组建起来了,从1986年到92年,我一直兼着这个职。
89后“64”前,301想把我留在医院当副院长,我没有答应。92年,我把 301的房子退出来,回到了南京。很多人不理解,北京条件比南京好,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你要回来?关键是我舍不得这支队伍。这支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10年后,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的发展比北京的要快、要好。
关于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我的夙愿,没有人才,就没有发展。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像刘志红这样我花了很大气力的,我培养了4个,就是刘志红最后成才的。
前面三个,两男一女。第一个,是我的硕士研究生,85年开始培养,那时我一心想多培养人才,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为了他,我想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送他到澳大利亚深造,我自己飞过去,帮他联系好导师,走之前,我和二医大打好招呼,学校说我们过去都没有这样做过。我找校长、政委做工作,我说他真走了不回来我负责。毕业后,他走了,不回来了,这一个失败了。
第二个,张丽红,是一个军级干部的子女,当时,她们这类高干子女不能出国,我找到总政,用非组织手段批了。她出去了,到澳大利亚3年后,我去看她,我问她有什么收获,她说,黎老师,当然有啊,原来跟着你人活着就是要享受工作,到这里才知道还要享受生活。我一听就来气了,你享受生活放在第一位,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人在贫困线上挣扎,你享受生活,他们享受什么?你享受工作,他们才能享受生活。我说,你如果只想享受生活,你就别回到我们南京总医院来,在我们研究所,我不说你不要享受生活,但享受工作肯定是第一位的,享受生活是第二位的。这个位置不能倒。你的担子那么重,怎么能光享受生活呢,所以,这一个又是失败的。
第三个,他不是享受生活,他就是说,美国条件就是比中国好,我在美国能更好地发展,我不想回国,我说行。但我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哪个国家做科学,都是为了病人,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祖国就不要了。
刘志红好就好在这一点,她的的确确是一名爱国的,是把享受工作放在首位的。她要留在美国,也有可能成就比现在大,当然她现在也很不错了,当院士了。但你为祖国做出的一分贡献,可以抵得上在国外做三分贡献。我们越是穷越是落后,就越是需要科学。所以培养人呢,别尽看到我光彩的一面,也要看到我窝襄的一面。培养一个人,他走了,你的心里肯定很难受。培养人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社会的事情,你说你花了那么劲培养他,他走了,想法不同,认识不同,他和你走了两条路,你也没办法。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培养4个,成功了1个,还是幸运的。
培养人才,要从小事做起,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刚成立研究所,没有医学院的大学本科生,82年才有,像唐政、刘志红,没有办法,只有搞短学制培训,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我们医院有个“桥北大学”,医院有座桥,我们办的训练班就在桥的北边。
刚开始成立时,肾脏科是一个新兴学科,引进不到人才,到哪里去找呀?我们只有原地培养,现在我们还留了两个。现在季大玺、陈惠萍,教授、博士后导师、国家特贴获得者,他们都是“桥北大学”的,我们都是就地取材、因人施教。
后来,本科生来了,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我们这个梯队是好的。因人施教,只要你认真去做,都能培养好。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讲要引进人才,我讲,这个引进的人才,他没有根啊!
国外的东西,好是好,但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我们研究所有个治学理念,9个字,头一条就是不崇洋,为什么,一个是人才培养是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东西。我规定研究生只许看洋文书,目的是要把这个手段学到手,学好外语这个工具,洋为我用。
第二个是严字当头。从三个失败的例子来看,我觉得还是严得不够,放长线、放风筝,还是要收一收。培养刘志红,我接受了教训,我规定也到美国后,不许跟中国人住在一起,一是时间很短,你要把西方的文化学回来,假如说你住一起的还是中国人,那不就等于把北京搬到了华盛顿。
二是跟中国人一起,星期六、星期天,你就想跟他们一起去买一点便宜的鱼、肉回来炖一炖、烧一烧,哪里还有心事去工作。后来,她是住在公寓里的,很贵,一个房租一千多美金,但是很安全,很值,你在那里住两年、三年,要得到10年、20年的成就,就要把一切时间节约下来。
我和她的老师商量过,她可带家属、带小孩,钱他们研究所出,但她没有带,三年里,家属、小孩都没有去过。
古人讲,严师出高徒,你心肠不能软。她回来后,上午到南京,晚上就到了实验室。有时,我严得不尽人情,谁让你生在中国,你还是中国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是精英?你肩上有没有责任啊?你有责任,不吃苦怎么行?做一个中国人,是很累的,你做出一点成绩,有多少人的眼睛盯着你呀?你的那点成绩,能为多少人服务呀?我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的进步。
我们肾脏科每年11万的门诊量,你们哪怕每个人改进了1%,意味着要多位1100个人带来好处,星期六,人家都去看电影去了,你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学习,那要创造多大价值,为多少人服务呀?
扬眉吐气的时刻
我就讲最近一次,今年,在美国圣地亚哥有一个会,叫做国际血液净化学术会议。这个会议是国际性的,今年是第11次,每年开一次,在我们研究中,血液净化不是专行,只是个副业。但我们这个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但也没有着意去宣传它,发表文章也不多。
但我们做的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一点名气,很多人到过我们医院都讲我们这项工作做得好,去年他们发了个电子邮件,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出钱,我就答应了。他们要我在会场作一个小的报告,20分钟,先给他们写个摘要,4、5后,电子邮件又来了,他们说原来听说你们这方面做得好,现在看了摘要,我们更信服了。
我们希望你们的经验再多传播一点,你们是不是再做一个报告,再做20分钟,我想没有什么,反正我是有工作有成绩,让我再写一个就再写一个吧,写了以后不到两天,又邮了过来,说你们这个材料我们理事会所有成员都读了,说很好,我们希望你们是不是干脆做个大会报告,40分钟,除了这两个小会报告之外,在全体大会上作一个专题报告,好像我在升级一样一步步升级,我想,看来你们还识货还认识我们这个是有身价的,于是我又回了封信,我说我们第一宣传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落款应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我们也没有吹牛,我们的的确确是有东西的,我们不是胡说,做学术报告,要拿数据和材料,货真价实的,我说行,再写一份,准备的时间长点。
结果不但又回了一封邮件,而且专门来了一个人到上海,说,我们看到你的报告感觉到非常振奋,这样,我们请你担任大会的执行主席,主持一个大会。
我同意了。他说我们想在你的报告把这个名字再改一改,你也可以把这个内容再改一改,什么题目呢?说“血液净化学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下面小标题“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这个题目对我还是有点吸引力。
三月份我去了,结果把我们的报告放在闭幕回上“全体会议报告”。而且我去之前就证实要邀请伙担任会议的组织委员会成员,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国际组织,没想到就这么几个月就给我发展过来了,当然首先也是人家很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标题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个事情我很坦率地讲是比较高兴的,虽然这几个月来来会回折腾这么几次,也就是把你几时年来的工作在简短的时间里集中地反映出来了,我们的的确确是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40年的路程,与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做完学术报告会后很多人来给我照相,这个事情也部分地反映出来西方对我们的看法,国际学术委员会成立10年,前9年都没有邀请我们去,的的确确是我们名声在外了,我们有学术论文在外面发表,你杰出人家认为你果然还是会真价实的不是冒牌的,这件事也是对我们研究所20年来耕耘的评价。
关于医德医风
其实严格讲我不是一个当好医生的料子,我脾气比较躁,性格急,从小在家里谁也没想到我会当个好医生,中国人讲“儒医”,应该是温文尔雅,我恰巧不是,而且我的性情也比较倔,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只是阴差阳错学了医。我也想过,我曾经不是被评为“全国百佳名医”吗?我都觉得拿这个称号和不合适,我觉得技术上是好的,但我是不是有这个风度,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要辩证地看待。研究所要成为“名医的摇篮”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对弱势人群的同情,对弱者的同情,这是医生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和条件,患者是有病,那怕他曾经是一个强者,他生了病,被病痛折磨,他卧床不起,他就是一个弱者。
能不能同情弱者,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说“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你就要同情他。我说实话,我现在承认我看病有一点优势在我认为是同情他们。在家里我就不受宠,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是因为我父亲是个“穷秀才”,家里的书很多,我当时就喜欢“七侠五义”,打抱不平,包括英国、法国的书我都看,喜欢《孤星血泪》、《买火柴的小女孩》、《老人与海》、《灰姑娘》等,虽然我自己并不强,但是好强、好斗,就是这个道理。
当医生一般讲,年轻医生能够同情病人,老了以后,他又司空见惯了,但我不是这样,直到现在,昨天,我还在为一个病人看病流泪,你说是天性,但还是后天培养的。我很能体会病人想怎么,可能你觉得自己的一个举动很随便,但病人就不是这样想,打个比方,我们医生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处方,比如说,一个病人慢性血栓、尿血栓,一个年轻医生说,这个五年可能变成尿毒症,这个队医生来说是一个科学,但病人可不这样想,五年就变成尿毒症,就意味着这个病人的生命就结束了,他讲这话时好像在推心置腹的告诉你,他们感觉不到我就能感觉到,我当时没法给他们发火,但是事后我会找他们,他们认为自己没讲错话,但是,我说你就相当于判他死刑,缓期五年徒刑,我就感觉到病人这样想。
他没有从灵魂上和精神上想病人之所想,所以说同情弱者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脾气很不好,但是跟我工作在一起的人,包括我的学生,像刘志红这样的,没有不挨骂的,所以这是我的一大缺点,也是我受争议的一个地方,所以***时人家对我那样无情也跟我自己有关系,但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是同情弱者,你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
就好像你跟一个三岁五岁的娃娃,你就要哄着他。所以到他们面前,你永远是这样的角色。这不是假装的,好像演员下了台了成了一种台词,这是内心的一种感觉。正因为这样,我对我的下级要求是比较严的。
我对我们的医德医风是比较满意的,至少我们没有哪个人说是收“红包”的、拿回扣,是没有的,我们公开讲是站得住脚的。最近,一个新加坡病人送了我们医生一块金砖,很漂亮,但是他马上就交出来了,没法退,因为病人飞走了,我们还有个医生也把六万块钱原封不动地交出来,因为这个是无法退退不了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好的。
但是我也实话实说,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觉得是两面,一面是应该尽量的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不会受外面的诱惑,但也不能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在物质方面还是要给一定的保证。
在研究所,我非常注意员工的物质待遇问题,我会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小孩交不起学校的费用而发愁,所以在物质奖金方面我负责的研究所还是发功夫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要想在我这里发财,不要现在我这拿红包、拿回扣,那不义之财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我们说的人还是比较自觉的。
但医德医风不仅仅是拿红包的问题,作为医生你拿红包就损害自己的人格了,等于自己给自己脸上抹一道黑,不管别人看不看的见。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养成,真正的对病人关心,所以我们有一个为病人服务的理念,这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在39病区工作中的成绩。这个东西好像很抽象,也好像不大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我们39病区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出来我们要成为一个特殊的病区,原来有个政委说叫特区病区,我说反正我们要非常好的服务,让病人感觉到满意,让病人感觉到在这里修养对你的工作也放心,对你的工作信赖,包括你给我打针发药都不会感觉到痛苦,对这个环境感到温馨。
现在我们39病区是最吃香的、最热门的,有的病人就指名要住39病区,不是说都是大款,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市民,他就觉得值,住进来放心,住这里就得到一种保证。
所以我觉得医德医风不是钱的标准,我们要让病人感觉到温馨,现在社会上很多医疗纠纷,病人对医院的意见很大,什么“白狼”,但我们39病区的病人走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而且有的又会回来。
我们39病区的医疗费并不比别人贵,同样是结帐,这边是六千块,在那边还是六千,甚至七千,因为这边的医生他会精打细算,有的检查不该做的就不做,用药跟你考虑得很周到,所以我感觉我们社会在抓医德医风没抓到点子上,没有从根本上考虑问题。
昨天我在门诊遇到一个病人,她住过院,没有完全把病治好,我给她做个心电图,使心肌炎,我问她你休息不休息,休息就会好得快,她就讲我没有钱,我想了很久,我心想把她送到急诊室去,她丈夫说我们还是回家吧,我说我安排你住院肯定会为你解决的,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跟博士在一起谈,我说我给你付费。
他怎么跟我讲,他说:“不行,我也不是完全美没有钱,还有三千块钱。”我说我借你钱,他说:“只要我能借得到,我就要为她看,他说我看出来了,你很同情我们,但是你们救济得了吗?一天你们能看多少我们这样的,我还能借到钱,还有更多的人借不到钱,我希望你们认认真真地把握的病看好我就感激不尽了。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到这一点,医德医风根本的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心。
关于对医护人员的严格、苛刻,有一次撕病例的事,当今社会追求奢望、浮华、享受生活,举一两个例子。我还是那句话,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这么做,所以和我在一起久的同志能理解,事后他们也能理解我,那是 2001年,我刚开过刀没多久,那时不怎么管病房,结果我们有一个病房,当时一个病人,手术做完以后,就发生出血,我们是有一个医生在那监护着,但这个医生年纪比较轻,病人出血后止不住,他就给电话给经治手术的医生,结果医生告诉他,不要紧,给他输血就行了,后来他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主任,他说你给病人查查病理,把这个情况给另外一个医生汇报一下,结果值班医生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医生,这是一个30多岁的医生。
结果到了凌晨三四点,才惊动了另外的备班医生,他过来抢救,这个时候抢救,到了七点多钟病人死了。
但这个事情,这个病人你说能不能抢救过来,也不一定,但是很明显,这三个人没有尽到职责,手术医生没来,主任医生不舒服,另一个医生也没来,中间就去掉了两三个小时,这事情发生以后,我是非常火的。
我们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调查了一遍,包括季大玺、刘志红等把病人家属、护士、医生像刑事调查录口供一样过了一遍。病人虽然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认为一直是有医生在护理的,打电话的事他们不知道,后来抢救的场面很大,觉得医生尽力了。
但我们自己不这么认为,我们就下决心,最后把三个都“罢”掉,那个主任是正高级主任,他是我培养的,而且他是这事之前一年评的正高,还是我代表研究所出面给他讲话,这是年来对移植还是有贡献的,这十年来,一直都是他带头,会有今天,他是出力的,但是这件事我是一点都不客气的,我说你靠边站,国家给你这么高的待遇,你是正高,但是我认为你不能再干这个岗位,我说你不能让别人服你,你发烧,哪怕你到39度你也应该来;还有一个医生是当时做手术最好的,他也有点骄傲,我让他下来,送他到武汉同济医院学习去;还有一个调到门诊。
这个会议我们开了一个星期多,我当时跟卢政委讲,我要“动手术”了,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情,我现在有点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要是不搞,还是要出事的。
政委说我们支持你,我们并没有动用行政上的降级什么的,都没有。从2002年到现在都很好,去年还出了个中国“十大新闻奖”。
出去学习的我把他送到全国最好的医院,把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他。主任我跟他拿道理讲清楚。这些同志现在工作都很好,这件事对他们震动很大,谁也不敢在电话里指手画脚,人命关天谁也不敢这样做。
不过这件事我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因为他三个是主角,一年做几百例肾移植,三个一起都把他撤掉,人家觉得你很胆大,我当时就想,我宁愿第二年少做几例肾移植也不能给别人带来伤害,在医德医风上不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就要杀一儆百,这件事我只在科里,没在院里讲,事后他们说这件事只有你们研究所这样做,一下罢三个,我说病人不告状不等于病人受到了应有的待遇,我有一个思想家丑不外扬,包括我自己,给病人看错病了,我也检讨自己,因为在科学面前有些事你可以弥补,这个事情没做好明天好好干加倍弥补过来,但病人生命只有一次,宁可多做一千条病人看似没有效果的检查,也不能放过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不是说做得很好,但我们是这样严要的。这三个目前都很好,没有消极不满,消极怠工的。
最新的科技成果
我们研究所人的精神是永不自满、永不言败、永攀高峰,我讲一个插曲,我们有个研究生,硕士读完读博士,跟了我五年,这个人相当勤恳,后来我们去年年底我们决定留她,她今年七月份毕业,我们干部引进的条条框框很多,最后我找了干部部的部长,副部长,最后同意留了,我们干部处干部科也很高兴。
七月底的一件事情,她做最后一个课题,做一种染色,这个技术也不是很难,结果他四个月没做出来,但是我们迫切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刘志红跟他谈话,说你要努力,怎么四个月过不了关,她说“我已经尽力了”,没办法做出来,刘志红跟我讲了之后我说不行,这个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志上人家介绍的,人家能做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假如看一个病人,病人希望你能把他救活,你说“我已经尽力了”,该死该活我管不了,我说这个不能说,比如说东西卖不到可以说,我们生死交关的事情怎么能说这个话,只要有百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也要把他救活,结果毕业前我又找他谈话,我又讲了这个事情,她说院长你不能怪我,我已经尽力了,我火了,既然她是这种求学的态度,我们研究所也不能留她。
走过生死关
2000年以前,我一直身体很好。2000年,我74 岁,到北京开会,突然感到脖子很疼,在会场就坐不住了。散会后,当天下午会没开,就离开北京回到了南京。跟放射科打了个电话,安排好拍片子,拍守片子一切都正常,自己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请骨科查了一下,也说没事。回家吃了点止痛药,晚上睡到半夜感到手发麻。第二天去做CT,结果出来果然三个颈椎都破坏,是肿瘤转移的侵蚀性破坏,当时就没回家,被他们用轮椅推到了高干病房。
我简直感到就像是晴天霹雳。周一,医院组织会诊,基本决定是肿瘤转移,一定要做手术,不然脖子一动就会断掉,要上钢板和钉子,做骨移植,问我同不同意,我想有病了只好治了,但是有个要求,要么手术做不好死掉,活着下来了,你们要让我的脖子能动。
后来到二医大作会诊,脖子上用石膏固定住。当前我说,手术完了以后,能会八个礼拜就行了,我还很多事没有处理完,八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在推向手术室的长廊中,真有点像向遗体告别的样子,两面站满了人,有总后的,总院的,二医大的,当时,我就跟陈锐华说了一句话,真有点像“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手术后,感觉还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我过了生死关和工作关,生死关,你当时会考虑得很多,活下来了,还能做些什么,死了,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我当时不是怕死,只是想活了还有没有什么意义,死了带来什么后果,自己也在权衡轻重,活要活得有价值,死也要死得其所。 2000年8月做的手术,半年以后,生死关基本上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考虑怎么样去工作。想到的是退还是干,还能做些什么,考虑得确实很复杂。到后来,我也想通了,没有什么顾虑了,可以用洒脱两个字来形容。觉得自己也许下个月、明年就走了,但我什么都安排好了,我准备好了,但是上面不让我走,我就不能走。我想,如果组织上认为我没有用,我退下来,写写书,如果认为我还有用,我就继续干,要死得其所。我就像一支蜡烛,不希望自己还能燃得很久,但我要力求放出最大的光亮,照亮别人,奉献自己。
现在,我采取保守治疗,好象觉得没有生病这回事一样。今年,我已经出了四趟国了,有时,坐飞机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我觉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