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书跋 《止庵序跋》的序和跋(止庵)
《止庵序跋》的序和跋(止庵) 序 起念编这集子时,我还不无兴致;待到汇总一看,原来稍有分量的,不过两三篇罢了,其他说实话写不写两可。——因想起来,惜乎书名为体例所限,必得是“某某序跋”;不然另起题目,就叫《两可集》好了。
盖当初写不写两可,如今出不出亦是两可也。 至于把这些东西归在一起,我也不敢断言就有多大意思。十几年来无非读书作文,未必有所进步;要想由此看出“生命轨迹”之类,恐怕也是徒劳。譬如对散文的意见,现在想的与从前在《樗下随笔》后记中所谈,说来并无区别。
虽然后来写的文章,较之从前也许反倒由“淡”趋“浓”,由“疏”转“密”了。这似乎更坐实了“眼高手低”一说。其实径将《樗下随笔》后记移作此集之序,亦无不可。
回过头去看为几本随笔集写的序跋,除解题的话外,其余议论均可互相调换。 这么说话未免有点儿泄气;但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讲。文章变化不大,自然并非虚言;假若真有进境,乃在写作之前。
我想这对读者,对自己,都是负责任之举。前些时读尤瑟纳尔著《哈德良回忆录》,卷末所附创作笔记有云:“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四十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不足,或者相反,有可能过于看重简单的行政划分、海关或军事哨所。
”所论甚得我心。尽管自己写的玩意儿不能与她的巨著相比,“年过四十”的时限因而不妨稍稍前移;然而未曾在特别幼稚时动笔,至今仍引为幸事。
此集所收序跋,限于自家著述,编校的书则不在此列。我写的书,大致可以分为“集”与“书”两类。相对而言,以后一类较为著力,就中《樗下读庄》、《老子演义》二种,尤其如此。
此外想写的题目还有几个,譬如关于《论语》、唐诗,都想做些研究工作。来日方长,足堪消磨。——这里提到“研究”,或有自夸之嫌;不外乎读书笔记,只是自成片段而已。以上无论是“集”是“书”,一总皆为读书之作。
我是一个普通读者,读什么书纯粹出乎自愿;偶尔发点议论,也是因为确有心得。虽然著之于文,未必有甚价值;然而我自忖也干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事儿了。 话说至此,想起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无奈自己读书经年,尚且不能达此境界。然则他说“会意”,显然不是不“解”;“会意”与“甚解”界限何在,或许惟有此老才能省得。我辈才疏学浅,还是用功要紧。不然不是自找借口,就是为陶公所骗了。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日 跋 今年对我好像不是什么好年头,不是这儿不合适,就是那儿不舒服,光景过去五分之一,稍稍像样儿的文章,才只写成一篇。虽然一向乐得给自己放假,可这回好像也闲得太久了。
不过听说果树亦有大小年之分,树犹如此,何况人乎,不算荒年,斯为幸事矣。近日出版社寄校样来,并嘱补写跋文,以期“有头有尾”。我踌躇再三而不能动笔。回过头去把稿子重读一遍,觉得不无顾影自怜之嫌。
这本是文人的坏毛病,但是比起洋洋自得,总归略强一点儿。话说至此,想起有朋友道,你总喜欢这么讲话,让人觉得“大傲若谦”。对此实在无言以对。或许大话不绝于耳,真话反而说不得了。平生读书不敢懈怠,作文不敢苟且;真有好处,也是止此而已。
然而读书作文本该这样,形容起来只是个“零”罢了。夫有所贡献,方为正数;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则是负数。倘若止此便足以傲视他人,这码事儿怕是根本干不得了。不如焚弃笔砚,另觅事由好了。
从前我写过几年小说,后来收手了;缘由之一,是读了卡夫卡题为《地洞》之作。我一直想写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岂知人家几十年前已经写过了。说来形容那不知名的小动物惶惶不可终日,进而把地洞营造得尽善尽美,这些我大概还能想得出来;看到卡夫卡写它在洞口另造一个藏身之所,守望着入侵之敌到来,我只好承认自己无论如何力所不及,因为做不到那么彻底,或者说那么残酷。
而他的《变形记》、《在流放地》和《饥饿艺术家》,于此可谓一以贯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卡夫卡称为小说的终结者,——起码终结了我的小说之梦。那么我老老实实当个读者罢。 我读好的文章,也有类似感想。譬如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换个人也许能讲那番道理,但就难以写得如此疏散自在。
连他自己同类之作,如《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和《日本美之展现》等,似乎也比不上。我读本雅明的《弗郎兹•卡夫卡》、《讲故事的人》等,还有伍尔夫《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某些篇章,同样觉得不可企及。
以上都是译文,好处未免打些折扣。再来看看原创作品,即以周作人为例,他的《乌蓬船》、《苍蝇》、《喝茶》和《故乡的野菜》,兴许还可模仿;若《鬼的生长》、《关于活埋》、《赋得猫》、《无生老母的消息》等,才真是学不来的。
读罢深觉自家所作之无可夸耀,非但过去现在,将来还是这样。正如《庄子•秋水》里河伯所说:“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 河伯的可笑之处,是先前曾经“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秋水》里另有陷井之蛙,同样讲过“吾乐与”之类傻话,末了也“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要是它们承认自己不无局限,也就不会落到此等地步。
河伯无须听北海若一通教训,陷井之蛙则免遭东海之鳖耻笑。《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可见并非要把它们一笔抹杀,问题只是两位妄自尊大,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即使并非“井蛙”、“夏虫”和“曲士”,未必就不“拘于虚”、“笃于时”或“束于教”,假如自以为不得了的话。
所以“大”如北海若,尚且要说:“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即此便是“以道观之”;比起“拘于虚”等,不啻天壤之别也。
然而河伯也好,陷井之蛙也好,虽然自以为是,毕竟出于无知;而且一经点拨,随即醒悟。是以北海若对河伯说:“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世间或有虚张声势者,较之河伯辈,所差又不可以道里计也。
而《秋水》未尝言及,是乃人心不古,出乎古人意料之外也。对此大约只能用“不可理喻”来形容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与文学打交道已超过三十年,写现在这路文章也有十五年了,如上所述,并无足以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此其一;对此了然于心,而且并不讳言,此其二;所写文章,大多是对世间的好作品——尤其是对心甘情愿承认写不出来的好作品——的礼赞,此其三。
末了一项尤非易事,因为须得分辨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不致混淆是非,乃至以次充好,——这既关乎眼力,又关乎良心;反观自己,于前者不敢妄自菲薄,于后者却是问心无愧也。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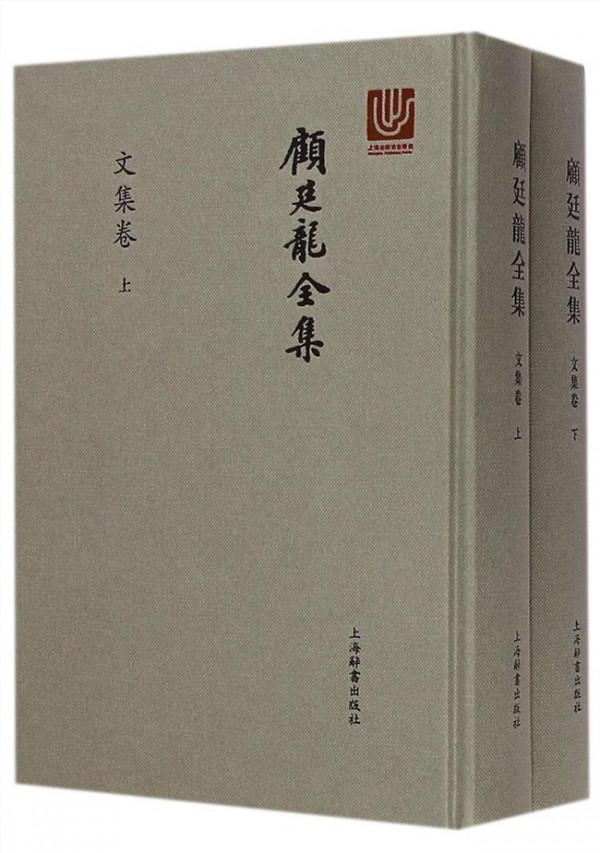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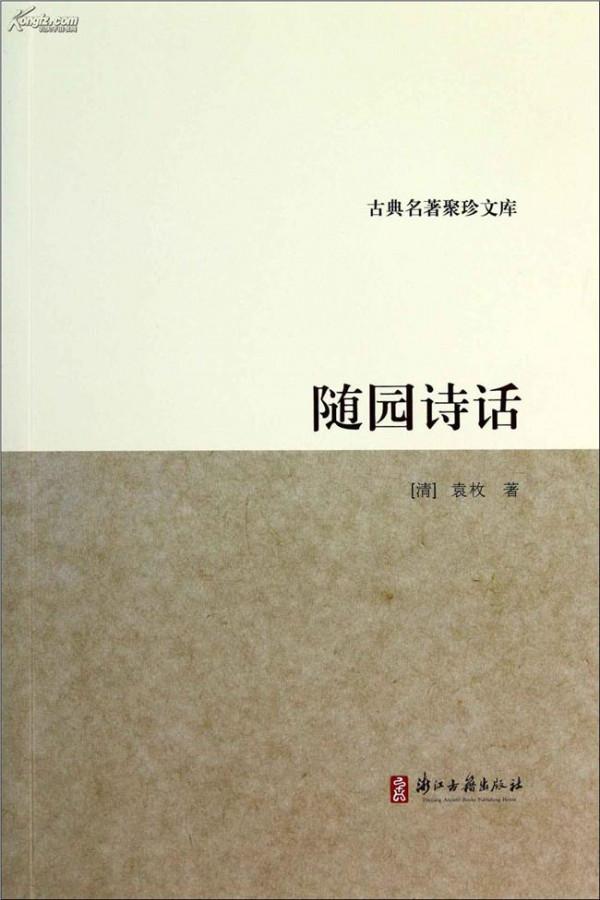


![>袁枚红楼梦 [转载]袁枚 读懂《红楼梦》](https://pic.bilezu.com/upload/1/f6/1f658d2ab03dca68d4e957d1a809993e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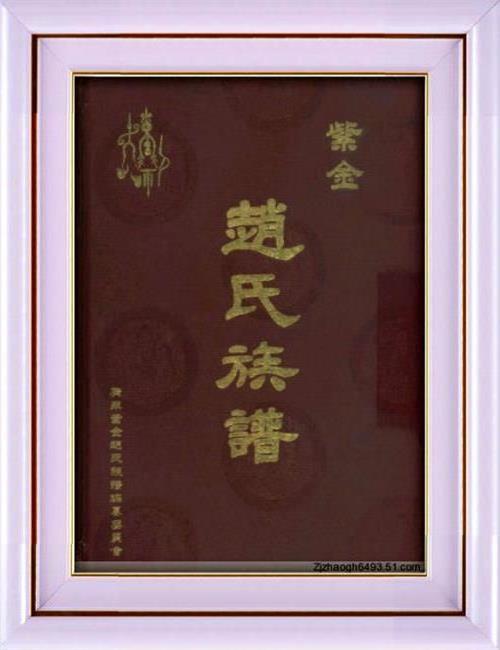
![>袁枚论读书 [转载]袁枚 读懂《红楼梦》](https://pic.bilezu.com/upload/7/94/7943cdf0f5871f77ba640a143382a4eb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