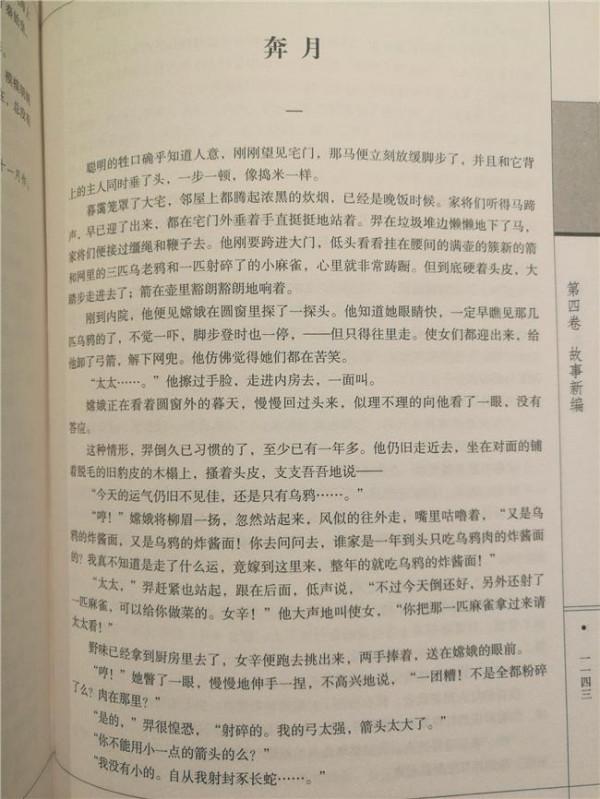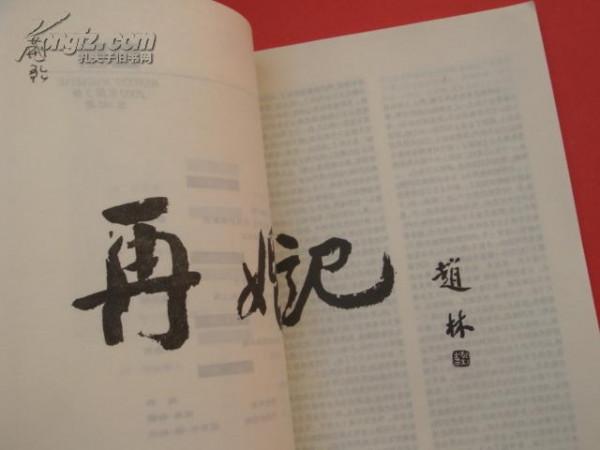贾平凹的资料 儿时玩伴忆贾平凹:平凹是鲁迅的话 我就是闰土
2007年9月初,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问世。《高兴》一书的原型刘高兴,这位和贾平凹一个院子出生又一起上学,共同生活了18年的伙伴,引起了媒体的兴趣。
此前,贾平凹自身的经历和作品,也多次成为他人笔下的素材。但其青少年时期一直是一个空白。刘高兴无疑是这段时期最直接的见证者,这位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的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写了篇描述青少年时代的贾平凹的文章,贾平凹读后,对刘高兴说:你若当年留在西安上大学、会是比我强很多的作家……
贾平凹是鲁迅的话,我就是闰土
这是四五十年前,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贾塬村东街五组一个普通的院落。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和贾平凹先后在这个院子里降生。18年后,贾平凹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大学,再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作家,我则去当了兵,后来回乡种地,这几年则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
虽然我和平凹的生活和身份如今相差千里,但那份情依然在,打他的电话,我只需“喂”一下,他就能分辨出我是“高兴”,无论他是在开会还是写作,都会和我聊上半天。
在西安城里,在这个让我这个乡巴佬格格不入的地方,我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没有任何的景象,只有声音,只有“嗵、嗵”棒槌敲打粗布衣服的声音从一个遥远而又空旷的地方传来。
这两天,贾平凹托人送来了他签名送我的书《高兴》,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一口气将书读完,这本以我为原型的书让我多次流泪,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大作家对一个小人物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怜悯。
如果把贾平凹比作鲁迅,我则是那个在月光下举着钢叉守护西瓜地的闰土。
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
平凹比我小一岁,1952年生,中等身材,从小就略显胖。由于农村的老年人管娃不科学,平凹的头几乎和我们同龄人一样,扁,后面一个把儿,人称马提笼子头。平凹小时候叫平娃,嘴阔鼻直,眉浓,眼泡微胀,脸长而方。长大后自己将“娃”改为“凹”。不过,外面人经常将他喊作平凹(ao)。平凹走路时脚后跟落地很重,这是俗称的“平板脚”,因此,在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平凹从小不太爱说话,农村人讲娃乖,不惹事。平凹的《秦腔》中的清风街就是我们的棣花街。棣花街东西长三里,南北宽一里,往北就是陈家沟,西三塬,巩家河,过了丹江河那个叫南沟的地方,则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
小时候,平凹家算一个大户,总共22口人,上有祖母,父母,伯父伯母,下有哥嫂弟妹,没有分家,家里有三间上房,堂屋两间。人多,饭自然就多,用的是桶子锅,这个锅深而大,能盛两桶水。每次吃饭时,平凹父亲先给平凹的婆(奶奶)盛一碗,然后大家排队来盛饭。做饭烧的是草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平凹下午放了学,就去拾柴。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是最听话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大人们忙着包饺子,叮咛我们几个小娃快睡觉。平凹贪念着压岁钱,睡不着,一晚上醒来好几次,盼着天亮。天终于亮了,平凹一翻起身,先去给婆磕头拜年,婆还没起床,平凹就跪在炕边的地上,连磕三个头,起来再作揖,婆忙说:“起来,起来,算了。
”平凹说:“这是规矩!”婆穿上外衣,从衣衫的小布袋里给平凹掏了三毛钱。平凹高兴地扭头就跑。然后又去给大伯、二伯、三伯磕头。
平凹胆子小,秋千荡得不是太高
“丢窝”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在屋檐底下的地上挖个窝儿,再划条线,每人拿一个核桃往前滚,谁的核桃离线最近,谁就是第一名,用劲太大,滚到线外就是最后一名。后来我在西安,有一次去一个酒店收破烂时,看到了大厅里摆的一个台子,挤了一堆人在玩。保安说那叫沙弧球。保安看我是个农民,让我赶快拿了破烂离开。我出了门,心里想,那玩法和我们小时候的“丢窝”一样。
点天灯,这是平凹父亲在山阳中学教书学会的。我、平凹还有其他几个小伙伴,把白纸用糨糊糊成直径为一米的圆锥形,底子用铁丝拴成十字形,在十字的中间绑一个盛煤油和松香的小圆盘,煤油和松香被点燃后冒出的烟把天灯送上天,穿过村镇,随风吹到很远的地方。
小时候的游戏还有摔泥巴,没有水的时候就用尿和泥,捏成一个中间凹的圆饼,口朝下摔到地上,一声脆响,上面就破开一个洞,比看谁摔出的响声大以及破的洞大,输了的人要挨打。平凹个子矮,劲小,常常是他输得多。我们还用泥捏汽车等。每年的清明,除了上坟外,大人们不定期要为孩子们架一个秋千,平凹胆子小,荡得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