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佩茹马三立 马三立:怀念赵佩茹同志
赵佩茹同志逝世十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
我和佩茹相识于青少年时期,从小在一起玩,一起学相声。他和我同岁,因为他是我师哥焦少海的徒弟,所以比我晚一辈。但是我很钦佩他的艺术,我认为他的捧哏技巧,超过了老前辈。佩茹给我捧哏多年,我们之间非常默契,我不管怎么“入活”,“正使”、“反翻”,他都能逮得着。在我铺垫“包袱”安排“伏线”当中,他既不“挡墙”,更不“落纲”,总是把重点包袱衬托得非常突出,总能让逗哏者感到如鱼得水,轻松自如。
二十岁以后,佩茹被常连安选中,约请他给常宝堃(小蘑菇)捧哏。常宝堃是青年相声演员当中的杰出人才,说、学、逗、唱,无一不佳。得佩茹捧哏,更是如虎添翼,一搭一挡,珠联璧合,锦上添花;也更能发挥佩茹同志的独特专长。
佩茹在掌握包袱中,善于提、兜、翻、垫、挡废纲、补漏洞,逗哏“下海”他能拽回来,把活儿引入正轨,行内无不佩服。
赵佩茹的祖辈,是满族的贵族,祖父姓金,父姓肇,叔姓固,祖祖辈辈都是吃钱粮、受俸禄,养尊处优,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干。一九零零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后,钱粮俸禄停了,坐吃山空,无以为生。父肇熙贤改名赵希贤(没有钱粮俸禄了,姓肇有什么用),挈妇将雏,去张家口。
不料投亲不遇,靠友无望,潦倒于张垣。偶到市场游逛,见常连安在撂地变戏法。不认识,人不亲,口音亲,同是北京人。赵向常谈出自己的来历和处境,常很同情,交了朋友,但是不能长期管饭。
常教赵变戏法,籍以养家糊口。可是赵希贤腼腆、口羞、不善谈,怎能围上一堆人看他变戏法呐?怎么办?结果,学会些小戏法儿,小手彩儿,摆个桌子变戏法(挑除官),一角钱教会一样儿。又认识了焦少海、陈荣启、辛文利,拜了盟兄弟。回到北京,赵希贤“挑除官”不干了,熟人太多,拉不下脸儿来。只好携带家眷来到天津。恰巧,焦少海也在天津。于是把佩茹送给焦少海学徒,三年半出师。
焦家的相声,道儿真,范儿准,教徒的“家法”严。赵佩茹聪明、肯钻,由他师爷焦德海给他捧哏,要求得更严。所以赵佩茹的“活儿”,不但会得多,使得也规矩。
一九五一年常宝堃赴朝慰问光荣牺牲。赵佩茹转而研究单口相声,后来又和李寿增合作,颇受观众欢迎。我的搭伴张庆森,因为双目失明,退休了。领导决定,让我和赵佩茹搭档,合作演出。我逗他捧,这对他当然是轻车熟路。他很了解我的表演手法,尽管我在垫话、入活、叙述铺垫方面有些改动。
但是,赵佩茹仍在包袱的尺寸上,量得很准。例如《对对联》、《三字经》、《卖五器》以及小活儿《拴娃娃》,无论我正铺也好,反入也好,各种使法,他都能恰如其分地抖出包袱,决无落空老泥。
就如同踢足球,无论我中场横传还是盘带到底线传中,他准能恰到落点,接球入网,决无传球失误。佩茹同志工作态度认真,对逗哏者要求特严,要活儿瓷实、路儿正。如果逗哏者入活台词不对、包袱的范儿不准,他不但盖口不接,包袱也不给翻,而让逗哏者尴尬难堪。所以有些相声演员害怕他给捧哏。如果你虚心地、真心地向他学,他会诚心诚意地教你。他最讨厌的是“抄蒙虫子”的入活。
赵佩茹同志,为人耿直,不占任何便宜。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臭架子十足。其实不然,赵佩茹最讲同行义气,一些亲友的婚丧嫁娶、请医购药他总是花钱受累不做声张。
佩茹同志离开我们十年了。他没留下任何文字资料。我们应当从他和常宝堃灌制的唱片中,探讨学习,加以总结,继往开来,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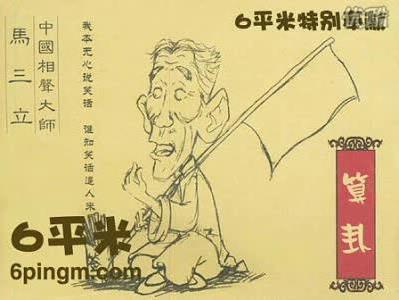
![>马三立相声全集[106段][打包下载]](https://pic.bilezu.com/upload/6/50/650f206f6ddf000fa108fdd5230ea18b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