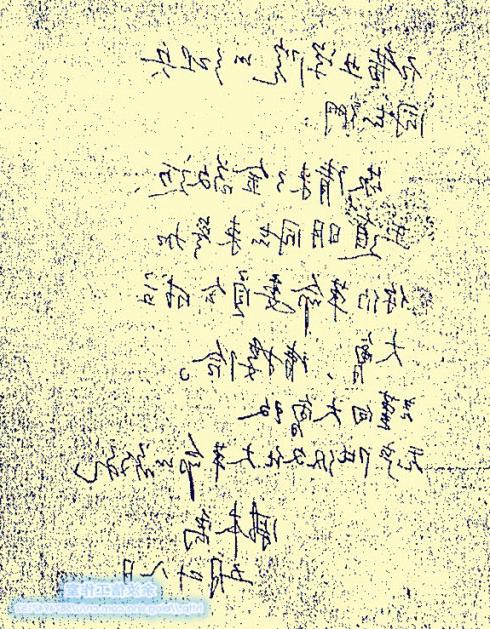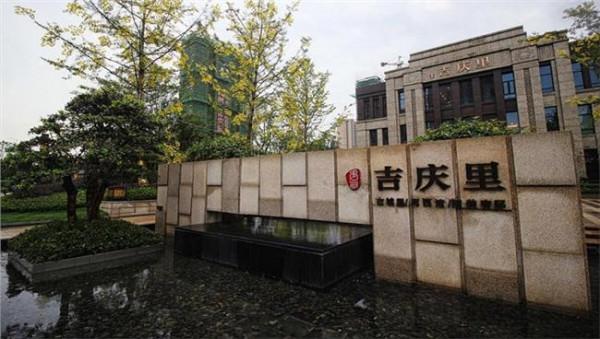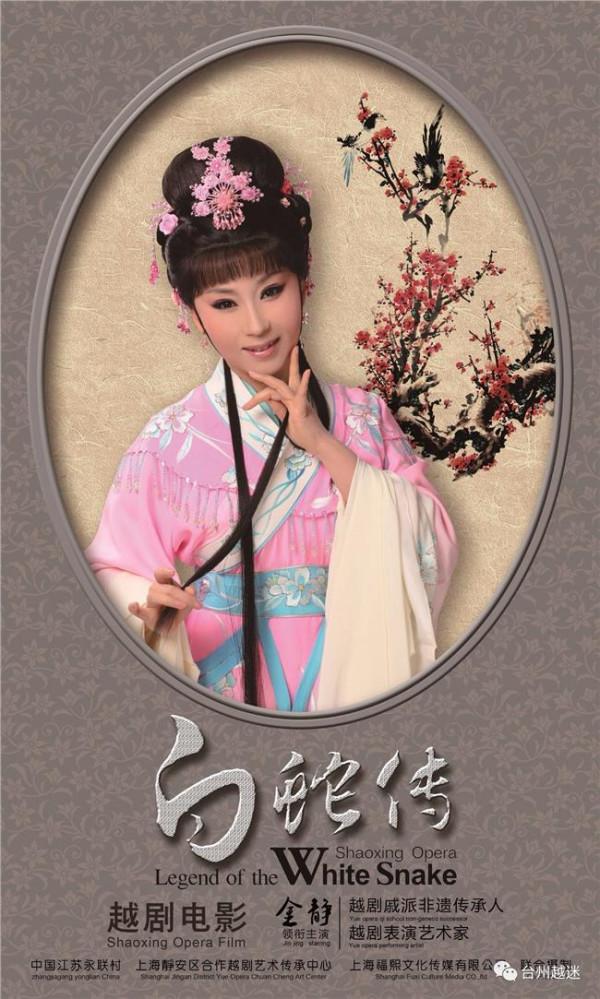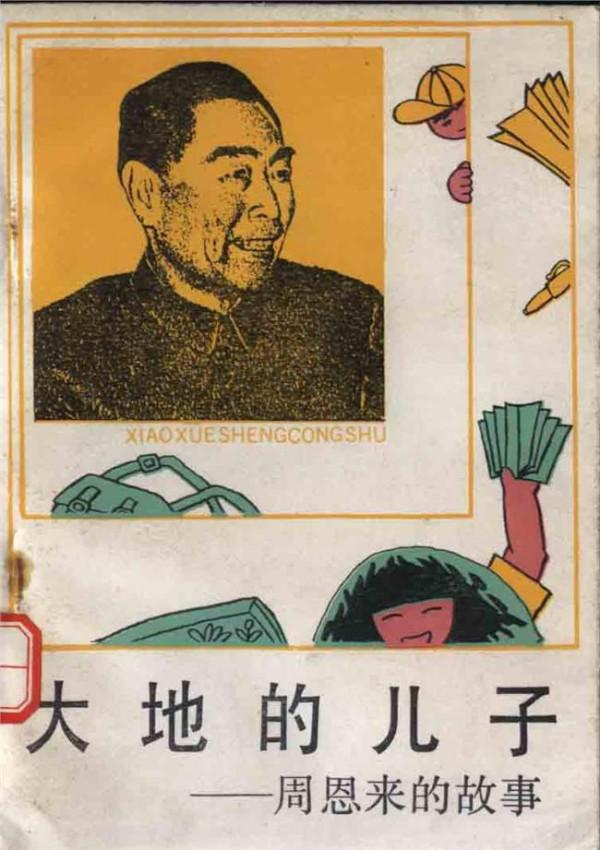逄先知评戚本禹回忆录 萧象:《戚本禹回忆录》之谬——以大跃进内容为例
萧象:《戚本禹回忆录》之谬——以大跃进内容为例
《戚本禹回忆录》出版引发的争议与批评,为近些年来同类回忆录所罕见。这除了戚本禹为文革唱赞歌的价值立场,背离人类文明主流,而触发反弹,最主要的因素是,戚书内容鱼龙混杂,所叙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混淆、错谬和似是而非之处,多有所见,严重误导一般读者。
以讲述个人所经历、见证并参与其中的国家重大历史活动为主旨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真实、准确为第一原则,也是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史学起家的戚本禹,虽然在回忆录后记中也提到,相对于观点立场,“更看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但很遗憾,到底未能知行如一而“实事求是”,却最终跌倒在了这一点上。
戚书最重要部分是文革,关于此一部分已有文革史家撰文指谬辨误。笔者在此仅就《回忆录》关于大跃进部分的叙述与说法,指出其不实与错谬。管窥知豹,一叶识秋,以见戚书之一斑。
[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处理“炮轰金门”这件事上面去了。所以刘少奇那时实际上已经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了,因为他即将就任国家主席]。《戚本禹回忆录》(下)178页
这段有关毛、刘大跃进史实的论断,虚实相间,似是而非,非经还原当时历史背景与了解相关信息,不能辨其虚实与是非。
先说“炮轰金门”事。这是戚本禹引用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原话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指标定得太高。6、7、8、9月,我也热过一阵子。”“但是八月在北戴河开会,没有人提议在我那个地方召集个小会,讨论一下1959年的指标。那时我的主要精力是搞金门打炮,人民公社的问题不是主要的,那是谭老板挂帅”。(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四,页413)
戚语本自毛泽东,乍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若对毛泽东此番讲话甄别考察,再加上前置时间状语,问题就来了。
考诸《毛泽东年谱》,毛泽东1958年上半年经南宁会议(1月11——22日)、成都会议(3月8——26日)、武汉会议(4月1日——9日)、广州会议(4月下旬)和八大二次会议(5月5——23日)成功发动大跃进之后,下半年8——12月,其主要日程行状如下:
8月4——14日,考察河北、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农业;
8月16——31日,主持召开北戴河会议;
9月10——29日,南巡湖北、安徽、江苏、上海一带;
10月14——17日,考察天津并召开会议;
10月31——12月30日,离京外出考察并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0日)、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21——27)和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12月10日)。
以上所有考察和会议内容,均围绕大跃进而展开,其中北戴河会议最为重要。会议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
而“金门打炮”,指的是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发生于金门及其周边的一场战役。国共双方以隔海炮击为主要战术行动,因此被称为炮战(百度百科)。“金门打炮”始于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讲话所称“那时”,显然指的是这一期间。
《毛泽东年谱》显示,有关“金门打炮”的事迹,首现于7月26与27日,北戴河会议期间的8月18、20、22、23日均有记载;其后9月上旬与10月多有出现,11月2日之后不再出现。
据上,不难见出,“大跃进”与“金门打炮”在毛泽东58年8月,乃至整个下半年所占时间精力之权重。
1959年毛泽东说此话时,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与共产风的弊端已暴露无遗,饥荒及其导致的死亡开始蔓延。八届七中全会主旨就是为进一步纠偏与调整指标。作为运动的发动与领导者,意识到问题所在,不能不要有所表示,作出姿态,所以承认“指标定得太高。
6、7、8、9月,我也热过一阵子。”但党的领袖是不能承认错源在己和承担责任的,那么,负责农业的谭震林——“谭老板”就只好受点委屈,作回替身,分担主忧。于是就有了“那时我的主要精力是搞金门打炮,人民公社的问题不是主要的,那是谭老板挂帅”这一说法。
领袖人物这种虚张声势的障眼法,不说在场的中央大员及各路诸侯,稍具历史感的后来读史者都会知道,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更不能当真的。
如果说毛泽东当年这种夸大其词是为了一种面子与权威,那么,戚本禹半个世纪过后为维护领袖的面子与权威,引用此说,且把有特定时限的“那时”扩展为“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以此为令箭,实为一种轻率与不严谨,是以讹传讹,贻误读者。戚所以如此者,是在为引出下文作铺垫。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层面的辨析。党——国体制下的国家主席,乃一象征性的荣誉职位,这是初中生都知道的政治常识。以就任国家主席(顺便一提,刘少奇接手毛泽东就任国家主席的时间在1959年4月下旬)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判断依据,这样的逻辑水平似乎不像是出自长期服务于中枢、深谙中央权力运作机制的戚大帅。
“刘少奇那时实际上已经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这一说法其背后逻辑与隐义就是“毛主席那时已退居二线”。这是否为事实,逻辑是否能成立,前述毛泽东马不停蹄地视察大江南北工农业生产和密集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的日程行状,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澄清是非,有必要对中央一线二线之说做一简要解释。中央一线二线之设想,1953年由毛泽东所提出,但由于诸种原因一直没有形诸明确的正式制度,也没有具体的文字可为考查,因此在党史上这是一个模糊而没有明确时间界限的问题。
但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认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一分界,大会之后中央一线二线之分呈于明显(彭厚文:“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考”,《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7年第3期)。
多年前笔者曾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8——1963年每年的(公)文稿数据做过粗略统计:58年为283件,59年321件,60年187件,61年106年,62年104件,63年99件,从一个侧面可以诠释这一看法。
可以说,尽管一线二线问题模糊,但也还不至于模糊到“直把杭州作汴州”,连共和国史上1958年大跃进这一标志性重大事件是谁领导的都看不清楚,戚老先生这一说法委实让人感到不知今夕为何夕的错愕。
[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点。]《戚本禹回忆录》(下)179页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徐水县考察,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年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十二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两千斤。毛泽东听了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好嘛!”(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4,页162、163)
这是笔者所见“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原始出处。另据李锐,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泽东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34)
至于刘少奇是否也说过同样的话,笔者阅读有限,尚未见及。但刘说“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点”倒确有其事,惟具体语境与戚文有微妙差异。58年9月下旬刘少奇到江苏考察,询问一乡党委书记,试验田的水稻能亩产多少,书记答,可产一万斤,刘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挖,还能多打些。”(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页325)
[陈伯达那个时候也跟着刘少奇的后面,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取消货币与商品,……他的文章一出来,马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戚本禹回忆录》(下)179页
陈伯达那时是否跟着刘少奇后面,事涉党内高层微妙的人际关系,非圈内中人不得其妙,不考。且说陈伯达受到毛泽东批评事。陈受毛批,非因在《红旗》发表有关文章,而是闲说相关见闻被毛视为有取消商品交换之主张。此事发生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
陈伯达晚年对此有一说法,认为毛泽东曲解其意。陈说,会议前夕他受毛泽东指派到河南遂平县调查了解人民公社化情况,听当地一会计说,他们本地用沙子到武汉换机器,大家把这称作“产品交换”,便将此事说给毛听。
毛据此认为陈主张产品交换,取消商品交换,并作为正要纠正的激进左风的典型例子,在大会上予以公开批评。“其实,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什么‘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我没有说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更没有写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我只是闲说了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162——163)
[“浮夸风”所引起的粮食生产的“高指标”,直接导致了1958年秋季粮食征购时的“高征购”政策的推行。]《戚本禹回忆录》(下)180页
戚文颠转时序,倒因为果,将“高指标”与“浮夸风”之间的时间顺序与因果关系完全说反了。众所周知,大跃进是在批判“反冒进”和右倾保守的背景基础上发动起来的,目的就是打破常规,赶英超美,实现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
而要赶英超美,高速发展,首先要制定高指标为指导。一个简单的(时间)事实判断就是,年初南宁会议的高指标(其后不断修改升高)制定在先,6月夏收严重虚报产量的浮夸风兴起在后。此正如《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所指出:“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中央文献出版社,1809页)一言以蔽之,“浮夸风是高指标压出来的。”(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页328)而不是相反。
与“浮夸风”相提并论的,是“一平二调”(平均分配,无偿调走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的“共产风”,它同样是发生在(6月之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种极左现象。所以,第九章第二节小标题[从“共产风”、“浮夸风”到“高指标”、“高征购”]也是错误,与[“浮夸风”所引起的粮食生产的“高指标”]一样,显示戚书对大跃进历史理解的逻辑混乱。
《戚本禹回忆录》关于大跃进,反映其思想倾向的重点内容集中在第九章第二节,在这节字数不过两千来字的篇幅里,包括标题在内,明显错误至少五处。戚本禹所以出此错误,固有年迈记忆衰退之误,文献资料不检之失,但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压倒了历史叙述的实事求是,明显的个人情感偏好影响到对历史事实真实性的认定,以至在涉及一些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史实与问题判断时陷入思想混乱,逻辑颠倒,不辨真实与究竟。
其实,大跃进并不复杂,不像文革等政治运动,云遮雾罩,帷幕重重,它是一场经济运动,从最高领导层酝酿发动到大干快上全民参与,整个过程相对清晰明了,各种文献资料较为齐全可供参阅,历史也早就作出了评定。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对于大跃进有这样一段叙述文字:“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2011年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同样一字不易地引用了这段话。这段代表官史最高权威的表述,不仅指出了导致大跃进失误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三层领导责任的明确。
当然,官史未必全是信史,官方说法也并非代表历史的最后结论。正如前指,历史仍有迷朦未明之处。为澄清历史,揭示真相,区分责任,体现正义,需要也应该对历史重新认定与评说,当然也可以为之进行辩护,但无论是评说或辩护,都应是以真实、准确、完整可靠的事实依据为前提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前提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叙述,才能获得认同,显示价值。
在导致全民狂热的大跃进问题上,刘少奇等诚然同样头脑发热,因而责无旁贷,一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作为亲历者,如实记录这节不无荒唐的历史,以垂训后人,警示来者,乃是一种可贵的历史责任;但如为了坚持一种立场,证明自己一种的观点,罔顾甚至混淆历史基本事实,那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古训,弄巧成拙,走过了头了。
这样的回忆录怎么能取信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