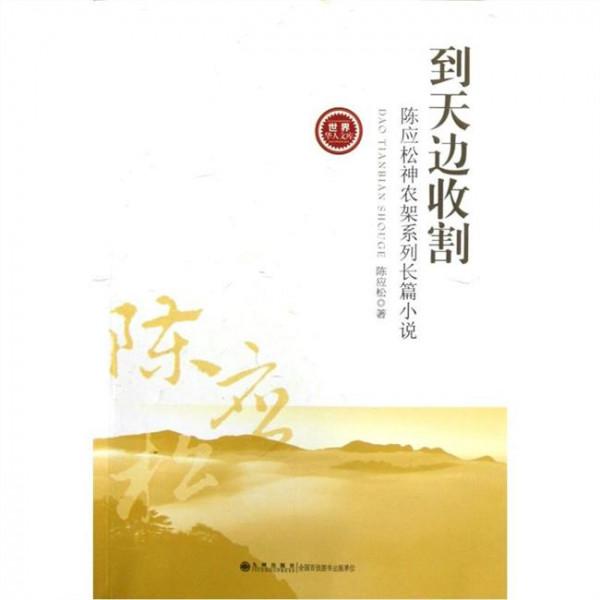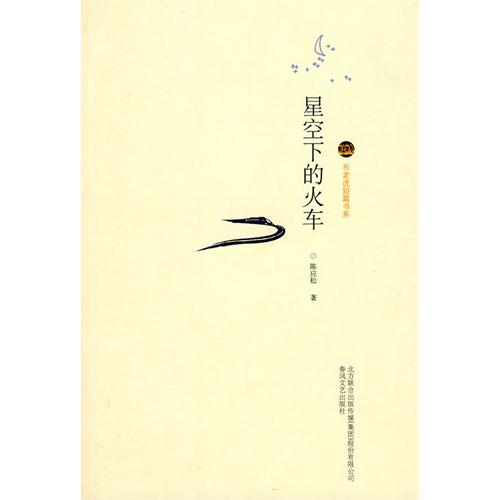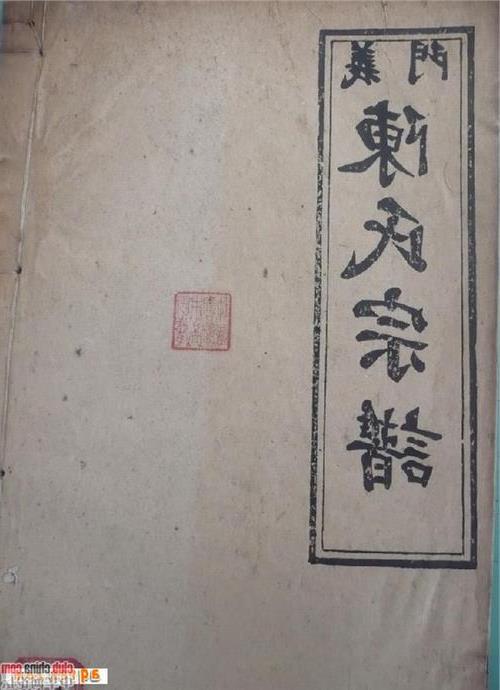陈应松喊树 陈应松:喊树 | 短篇小说
王世堂一共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在多年前就见了阎王。那一年年景不好,这娃子在山上挖蕨根做粑,吃过后头肿得比南瓜还大,王世堂的老婆就在村委会墙上涂大粪驱邪,但还是没保住这娃子的命。王的老婆倒因为这事,被乡里抓去关了半个月。
这死去的娃子眉清目秀,睫毛修长,像个洋种。王世堂另外两个儿子都是在石头上摸爬滚打、忍饥挨饿长大成人的,可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们死去的哥,都长得怪头怪脑。有一个叫王二苕的,是老二,找了个患“巴骨流痰”(小儿麻痹症)的女人结婚,住进了深山后就没了音讯,不知是死是活。
倒是老三,王三苕的,虽不灵光,却读了个技校,到了城里工作,就是没有女人看上他,都快四十了。现在,突然有了信,让王世堂给他打一套家具,那是要结婚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王世堂高兴得快中风。是有人从城里搭信来的。那时他正在山上刨洋芋,有个人喊他,是三苕儿时的伙伴,告诉他这事。他跌跌撞撞跑回家去,对着老伴的遗像就高声说:“娃他娘,老巴子(老婆)哎,三苕要结婚了,在城里结婚哩!搭信要我给他打家具。还说怕是媳妇怀上了,要得急。这可有孙子了!……”
王世堂哗啦哗啦地吃饭喝酒,让高兴出声,眼泪直往下掉。可静下心来一想,这可到哪里弄木材去?你这娃搭个甩信一说我就要办,没捎一分钱回来,老爹我哪有这多钱买木料呀?过去要一口柜子,或者一口箱子,还能找点存料或借点木头来做,现在,你有钱也买不到木料。
家具要大料才行,山上哪有这样的大树?王世堂放下筷子望着山,山上也就是一些能做筷子的树了。江浙人烧炭的全回去了,没回去的留下来收板栗香菇;重庆偷树的农民来过几个,听说没树好偷,只好顺手牵羊弄走了一些党参苗。
林业站的人种了些日本落叶松,材质不好不说,让羊吃了针叶嘴肿得嗷嗷叫,树底下寸草不生。这可是毒树,打家具害人的。要说打家具,最好的是樟木,苦楝也不错,都不生虫,紫杉也好,湘杉过得去,过去铁桦红桦也坚实。可这些全没啦。大点的樟树都有人收,挖掘机来挖的,城里人买去的,开价还高。有的一棵银杏,几百年的大树,万把块钱买走了,听说一到城里几天就死了,水土不服。
王世堂背着斧头,钻进深山里去找树。五天后回来,人已经冻得不行,脸色青黄,四肢抽筋,给腿上拔旱蚂蟥的力气都没了。回来用刀刮,才把满腿吸血的蚂蟥刮下来。他好歹弄回了一筒木头,是红桦。在一个山沟里,多年前别人砍伐后估计忘了,或是沟太深背不出来丢了。有几筒,有的腐烂了,选了一筒,拖到路口花了两天,晕厥过三回。这可要力气,力气都耗在了这筒足有一两百斤的木头上。差点丢了命,可又能打什么呢?
这还不说,刚进入臭娘子坳自家的院子,头上忽然掉下一坨东西,一摸,一大坨鸟屎。那个臭呀!抬头一看,是那些对他瞪着铜铃眼的苦哇鸟。这种鸟鬼头鬼脑的,不是因为经常衔些小鱼给他吃,早把它们连窝端了。它们的叫声阴阳怪气,心怀鬼胎,仿佛大有深意,对世界了如指掌。
把白天叫成黑夜,把开心叫成灾难。特别是到了要下雨时,这种鸟叫得如丧考妣,凄凄惶惶,满树乱蹿,又哭又笑。树上的苦哇鸟,鸟窝至少有一二十个,可它们会叼来一些不知是哪儿的鱼,长条的,白净净的,通体透明。
有人说这是从山洞涌出的一种鱼,无鳞,小眼,鱼腮里有一颗硬虫,懂这个的说是鱼虱,后来有人说这虱可以治噎死病,就是喉癌,他就留着了,送给患了此病的乡亲。山里人喜欢抽烟喝酒,又一年四季吃腌制的腊货,加上整天在火塘边烟熏火燎,爱得喉癌。
自从有这鱼虱,上门讨要的不少,救活了十里八乡的不少人,有的还是晚期。鸟们衔来的鱼吃不完,就爱藏着。有一天王世堂发现树底下的小水洼里有鱼游动,捞了不少,却捞不完。
院子里本来会散落些缺头断尾的鱼,后来发现鸟吃不完就藏在水洼里,这就留下了这种凶鸟,也算是它们前生欠王世堂的。这鱼当地人叫羊鱼条子,做火锅,放点酸菜,那个鲜呀,没东西比!麂子汤、果子狸,都靠边去。
但是,这一泡屎太腥臭,往上一看,那些苦哇鸟都坏心眼地望着他,狞笑,喉咙里发出呱哒呱哒的声音。王世堂当时那个气呀。他踢了一脚地上的木头,做什么呢?做张桌子却缺凳子。这泡鸟屎晦气!一块石头砸过去,鸟扑楞楞飞起来,有的飞走了,又落在树上,叫得更凶,像哭一样。
就落下几片臭娘子树叶来,桃形的,绿英英的,油光闪亮的。人望高了,头就发晕,加上又冻又饿,差一点倒下去,扶住了树。树太大,抱不住,一屁股跌坐在了水洼里。
从没砸过鸟,这下闯了祸。苦哇鸟“苦哇,苦哇”的聒噪声像沾水的绳子,一圈一圈捆绑着这个夜晚,捆绑着王世堂。月亮从树缝里透出来,鸟在月亮里奔蹿跳跃,把月光撕得羽毛纷飞。月亮是一只大鸟,打不赢这黑压压的苦哇鸟。
这时候,水洼里的两只小红蛙也呱呱地叫起来,两条小红蛇也从树洞里爬出来,游进水洼里,乱跑乱颤。他睡不了了,再捡起一块砖头往上砸去,这一下,砸中一只,或者几只,几声凄厉的惨叫,一阵更大的混乱,后来总算停止了,安静了,只有一两声的啜泣,在清寂的夜空里飘零。
妈的,是要老子发狠的!他说。世界静了,小红蛙的嘀咕也很轻,两条小蛇也平静下来,慢慢划水,激起一圈圈的涟漪。这两条小红蛇从来就这么大,从来不吃红蛙。到了繁殖的春天,也没见有蝌蚪,红蛙也就是两只。这情景持续了至少二十年,仿佛时间停止了,仿佛这个梦境永远在梦里,没有醒来。
人也产生了不会老去的感觉,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儿,半斤的酒量一点不减。老婆死掉,人过花甲,也没有让他被悲伤和苍老打倒。说起来,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儿。
这蛙,蛇,还有鸟,鱼,与臭娘子树共生的一些古怪生灵,还有这树上一到春天就会孵出的一树毛茸茸的雏鸟,就像春天开出的满树鸟花,淡黄色的(羽毛丰满就变黑了)。还有更神的,这臭娘子树叶子,是可吃的,老婆发现的。
她把这树叶打下来,用开水一焯,放一瓢灶灰,放在纱布里包着揉,揉出的汁是绿的,一会就凝固了,半透明的,就像碧玉,切成条,再加上酱油、醋、辣子、蒜末、姜末,就是别致的凉粉啦。这树叶,密密匝匝,啥时候胃口不好,啥时候做上一盘,辣凉辣凉的,入口爽滑,清凉透心,这日子!
蛇在水里游动舞蹈,就像爪子在心里挠着痒痒。那一圈圈的波纹扩散着向树根荡去。这树蔸的根凸出土石有一尺多高,像虬伏的巨蛇,生瘤子,有人称为龙根。于是有乡亲在下面供了香烛,树枝上缠了许多红布条。
苦哇鸟在树上叫得怪瘆人的,拉出的屎又臭,满树做凉粉的叶子哪还能吃,全是鸟粪,当然择出一些洗了还是可以对付口里的馋虫。但鸟的叫声让王世堂这天彻底地烦了,他坐起来对着遗像说:
“老巴子,只好这样,我把树砍了给三苕打家具,我王世堂老了,只有这个能耐啊。”
老婆好像在考虑,也许在想别的事,看别处,目光躲闪他。
“三苕催得急,媳妇娃都怀在肚里了……我去山里转了几天,到哪儿找这大的树去?有也不让砍……”
她不同意?她肯定不会同意的。就凭这个,她要给王世堂做臭娘子粉吃,还要等儿子媳妇孙儿回来做臭娘子粉他们吃。到了夏天,多大的荫凉,还有鸟叫(虽然不中听),六七月间,这叶子做出的凉粉最好吃了……
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晚上他不想跟她吵架。只有当他磨斧头的时候,他才会与这个死去但时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女人摊牌。
早上起来,阳光打在树冠上,院子里一片明亮,苦哇鸟纷纷飞来飞去,直往水洼里丢鱼。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估计哪个泉洞里涌出来了不少的鱼。但人是不知道的,在很深的峡谷和山沟里。有一个来要鱼虱治病的乡亲,他要别人把鱼全捞去了。
但他不好说这是最后一次。树真的很大,平常不会太在意,真的大啊,屋顶上全是伸展去的大枝桠,落叶一层层盖着屋顶,上面又长出草和厚厚的苍苔。完全可以打一整套家具,挂衣柜、双人床、五屉柜、电视柜、春台、梳妆台、碗柜、八仙桌加四条大长凳、摇窝,一些枝桠可以打两口箱子。
他的眼睛过于贪婪,甚至每一个部位每一根枝节做什么都有了想法。但不能让树猜到心思。这么老的树,鬼精了,心里比人还精。老子一锤子的买卖,想就想了,没别的路可想。铁了心想,不能让老婆跟自己辩理,没理,老子的斧头就是理。老婆是个很倔强的人,大儿子患病不是她去村委会泼粪的么?半个月回来,腰也打歪了,双拇指吊去了一层皮,可不低头,昂首挺胸,英雄凯旋。
说干就干。因进山时间耽误了几天,我得为三苕把事办了。儿子在城里不会再回来,我又能活多少时间?那这树不也是别人家的了吗?与其如此,不如我先下手为强。就这样!
磨斧。
这就是要给树下马威了。他决定要下手时,煎了盘腌晒的羊鱼条子,还炒了个蕨粑,备下五六斤酒,准备与树拼命的。酒壮胆。他估摸着要对着树喊三天三夜,把它的魂喊死,否则不能动斧头。这是山里砍树的规矩,特别是大树。
臭娘子树呀,不怪我不客气了。娃子要活,你就活不了了。没谁与你有仇,相安无事几百年,几代人待你不薄,你也看家护院。娃子要你,你就贡献出来吧。这话过去没谁说,我是老了,说说你听。要是年轻,火气大不信邪,大吼几声就下斧。不吼也行,你能把爷怎地?
斧头摆在桌上,跟酒杯碰杯。几口把酒倒进去,鼓动起整个人,让肠子先烧起来,连着喉咙哩,再喉咙里喊。
磨刀的斧刃直对着树根。把阳光寒闪闪的抹在刃上,贼娃子亮。那个磨斧声,整个坳子里都听得到,就像要砍一百个野牲口似的。“嚓嚓——嚓嚓——嚓嚓——”斧头是用炮弹壳打的,钢火没得说,砍石头也不会卷刃。为啥要磨呢?吓你!先杀你的威风。不说话,哼哼着,吐出的气像石头,在水洼里直打滚。坚持磨。一个动作。就一个动作。这是聚气,气沉丹田。聚的是杀气。
斧头在磨刀石上发出那种很硬气的、阴沉沉的声音,短促、干脆、简捷、森冷、硬碰硬。斩尽杀绝的、削铁如泥的气概。不知怎么,这么磨着磨着,突然一阵空虚,心里空落。咋越磨心里越空哩?
“妈的,不就是臭娘子粉吗?老子不吃不就是了,你跟老子咕个么屄!”他大骂。心里。心里挑起了与老婆的争吵。一定要大吵一架。是的,要大骂!这气提不上来。老婆在说砍你个死狗日的,今后没得臭娘子粉填你的屁眼了,没本事的!
老婆那张核桃脸就在门框子边上,大叫道:“它还有几个干儿子哩,以后到这里拜你啊?你是树啊?”
这里有这个习俗,不好养的儿子就要拜寄个干爹,不是人,是拜石头或者大树,每年还要上礼,提果品山货来,打的麂子啊獐子啊竹鼠啊。
“你装尸也没有这么高啦,你个矮趴尿罐!”死去的老婆跳脚骂。
“鸡巴干儿子,今年风调雨顺,有几个来看它的?啥鸡巴树爹,自己的亲爹都不养,捏到鼻子哄眼睛的!……”
内心惊涛滚滚。这种无声的驳斥增添着王世堂的勇气和力量,烧灼着他。
“你个臭婆娘滚一边去!都给老子滚远点!”
他骂出声了,他要爆发了,要把一切挡开。接着他要喊树了,要吼叫了!
他在空中挥舞着斧头,跳起来就对着树张口大喊大吼。这是从胸腔里发出的最强音,这是要压倒一切的声音,咆哮,歇斯底里,像是挣扎和绝望,是咽下最后一口气,吐出最后一口气的声音:
“嗷嗷嗷——嗷嗷嗷——”
他磨刀的时候树上的苦哇鸟依然在浓密的树叶间跳跃聒叫着,这一声大喊有点作用,如晴天霹雳,让树上立马噤声,安静了。是短暂的安静。
这一声好疼,嗓子。太猛,喉咙里火烧火燎,像是拖出来一个干枯的丝瓜。连肚脐眼也因为喊叫鼓成大包,牙齿龇开,带着酒馊味的浊重胃气冲向树巅。
但是,声音何其短促,喉咙何其狭窄,撕裂开也不顶事。旁边是深沟大壑,周遭是悬崖绝壁。这个臭娘子坳,在这些巨大石头和沟壑的深处,说是村庄,其实是一坨鸟粪,一块苔藓,可以忽略不计。这棵大树,从山上看,就是一棵小草。人呢,当然就是只爬虫。
这一喊,还唤来了风,山风飒飒,一会鸟声又活跃起来,鸟们一阵风似地飞走了,拉下一些鸟屎。留下的腾跃在风中,腾跃在自己一如既往的叫声中。它们个体多,叫得比王世堂长久。王世堂只有再吼喊,要连续吼喊,要把这树喊死,开弓没有回头箭。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日头落山。他几乎气绝。他抓着树,手上攥着斧头,还不敢砍。他也没这个力气了。树叶还青碧油嫩的,枝桠坚挺,造型张狂,不露声色,在流散的晚霞中高高在上,所有的鸟都围绕着它飞,哇哇乱叫。在归巢之前,这些苦哇鸟每只都要绕树三圈,就像某种神秘的仪式,就像是对黑夜的敬畏和惧怕。
然后,星星跳出来,树枝冠盖变成巨大的黑翼,覆盖住整个院落,覆盖住整个坳子。也像巨大的守护神,让所有的一切,暴露在天空、大山、野兽和千古荒凉的村庄与人,在它的卵翼之下,安然入梦。
他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歪歪倒倒地向屋里走去。没有点灯。倒上一杯酒,咋喝不进去咧?喉咙疼,呼出的气都像是刀子划在喉咙上。
树睡了,树在嘲笑他。树太大。到了半夜,月亮偷偷摸摸地跑出来,在床上望着院子里的水洼,蛙出来了,蛇也出来了,跟没事一般,一样的跳跃,一样的游,一样的嘀咕。他的喊声消失了,一切跟过去一样。黑夜很深,山影很厚,风很狂。
酒醒之后他明白,这不是一两天的事。过去砍一棵枯皮松,皮奓得像凤凰展翅,喊几遍,皮就收拢了,像条夹了尾巴的癞皮狗,你再下斧。这树,哪吓得住它?不过也不怕,往脏处想,含口粪了喊,不由你不怕。你就是个山混子,树精,还能不怕人整的!
再喊再吼。
歇了一夜,喉咙滋软了些,喝了从屋后接的冰凉的山泉,他端出一把凳子,站上去,腰扎牛皮带,握紧斧子,喊。
从早喊到晚,没停。撒尿就对着它,头上的鸟屎往树上抹,吐痰,擤鼻涕,全对着它。站,坐,叉腰,擂拳,跺脚。眼睛喊凸,肠子喊断,心脏乱停。树还是树,还是青枝绿叶,稳如磐石,岿然不动。树皮,树桠,树冠,叶,根,连树上的鸟,鸟粪,都是原样,还是臭。鸟还是那样,站在高枝上,或偎在窝里,闲庭信步,吊儿郎当。叫,吃鱼,也丢几条鱼在水洼。掉些鱼渣。发些叽叽咕咕的梦呓。
这让他很受羞辱。打不死你呢?指鸟。这鸟是鸟类中最贱的鸟,苦哇苦哇,传说是旧社会死了男人的苦媳妇,这么叫着哭着,变成了苦哇鸟。全是童养媳的后代。不是有鱼给我吃,有鱼虱能治些噎死病,我让你们在这里筑巢做窝,娶妻生子的,弄得一院子腥臭,家里像死了一屋人似的。结果呢?不想则已,一想是他娘的不吉的凶鸟。大儿死了,老婆死了,二儿不知生死,三儿快四十了才找个二婚女人。这些死鸟,瘟神鸟!打死你们!打死你们!
一根竿子就朝树上扑去。这是哪门子闹的?鸟自在歌唱,吃香喝辣,突然临头一棒,打得折羽乱飞,连哭带喊。随手还捡了一把屋檐下的破夜壶丢进水洼,“咕咚!~~~”让你们藏鱼去,臊死你们!
他感到喉咙里开始咔血。
这个晚上,他想做臭娘子粉。就是准备做最后一顿的。打鸟打下的树叶,捏捏,新鲜,有汁水,树还是活的。就做些臭娘子粉吧,润润嗓子。一连喊了三天,喉咙完全嘶哑了,破了。揉着树叶,揉着搓着,咳嗽起来,一口血丝水涌出。喉咙里一定是血糊汤流了。
老婆在旁边帮他揉搓着,一只手那么不停地上下起伏,像搓板上搓衣的样子,边揉搓边拧,绿水就流下了盆子……
这是幻觉。没有老婆。没有人帮他。老婆在桌子上,在一张镜框里。老婆走了,不跟他吵了。接着将是什么离去?都会离去……好空虚呀……
杜鹃鸟划过夜空,叫声渐行渐远,“哥哥烧火——哥哥烧火——”
杜鹃啼血。那声音淒伤无比,也喊出了血,跟他喊树一样。
第四天,开门出来,突然一群苦哇鸟向他俯冲,用尖喙啄他,啄他的头,脸,眼睛。要将他啄瞎!王世堂猝不及防,眼睛一阵生疼,鼻腔被鸟喙拉出一块肉来,耳膜快啄破,他嚎叫躲闪扑打。我的个娘呀,为何要攻击人呢?立马就想起这几日他做的事。
那还不是断子绝孙的事!这群鸟有记恨心,好样的,全线反击,屎弹如雨。王世堂左支右绌,手忙脚乱,捂住眼暴露脑袋,头发嘶啦啦扯去了。去拿竿子和扫帚,奋起反抗,乱扑乱打,满院子撵鸟。鸟向更高的地方飞,更加狂烈暴躁地聒叫,愤怒地拍翅,到处是直朝他咒骂的猩红的雀舌,到处是屎弹。
王世堂吃惊这些鸟的癫狂执着,强烈的报复心。
一场搏斗。筋疲力尽。
“王世堂狗日的,你可做的好事!”老婆在门框还是在镜框里骂?
树却一动不动。树像石头立在那里。
“豁嘴哥……”
嘶声哑气的王世堂指着他端去的臭娘子粉,用自己也辨不清的声音唤尤豁嘴。
尤豁嘴住在岩壁旁,搭的个芭茅棚子,风不吹雨不淋,冬暖夏凉。他是个老鳏夫,吃惊地看着王世堂给他端来的辣味扑鼻的凉粉。这么好吃的凉粉王世堂为啥子给我吃?
“我喊不死这棵树……”他指了指碗里。
因为听不清楚,又指着碗里,树?粉?喊不死?全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话,主要是完全没有声音,放个屁也比他响亮。尤豁嘴不知道王世堂喉咙怎么了,只见他指指戳戳对着喉咙。
“世堂,我看看……”
一口血水出来。慢慢讲。是树……娃子三苕……要打家具……要砍那棵臭娘子树……喊了三天还得罪了鸟……喉咙溃破了……
尤豁嘴总算听明白了,尤豁嘴嘴里嚼着臭娘子粉说:“你那棵树还不是树精!老树精,你不敢下手啊,费这大的劲,走,我有治的法子!唉,是说这几天坳子里狗咋叫得这么凶哩。”
尤豁嘴提起当年在伐木队的板斧,就去了王世堂的院子。
尤豁嘴围着树气宇轩昂地转了几圈,也不说话,瞅着什么。后来他把手按住了一个地方,说:“就是这——”
说时迟那时快,尤豁嘴手起斧落,照准大树的瘤根就是一斧。这一斧,扎进去足有三寸深,拔出斧来,登时从砍开的口子里流出殷红的汁水来。
“你看,准的!你要放它体内的精血和灵气。”尤豁嘴晃着斧头说。
“嗷啊——”
尤豁嘴再陡然一声朝树怪喊,是那种稀奇喊法,像道士先生做驱鬼法事。这一声,连王世堂都吓了一跳,魂差点吓掉了。
这天,王世堂守着这刀口流出的红汁水。看它流。细细地流,不断线地流。
刀口里的红汁水足足流了一夜,把水洼全染红了。这是树血。
这一夜,苦哇鸟叫得忒凶,满树都是哭号声。
就一夜,整个树叶蔫了,霜打过一样。鸟声没了,只有有气无力的几只。到了下午,完全静了,树安静了,风声都是软的,发出干涩的、枯燥的挣扎声。
“王世堂呀王世堂,快去请木匠师傅,准备酒菜啦!”
回过头去,老婆在叫。她好高兴,变了个人似的,不再骂他。儿子三苕有家具了!
一房家具打得结结实实,新新崭崭。上了油漆后,光彩夺目,满院生辉。
王世堂把家具运到城里,把儿子媳妇高兴得不行。真是及时雨啊。铺上新床的当天,媳妇就在床上生下个大胖小子。这家伙,这么急着出来哩,你爹你妈还没扯结婚证哩。不是个四苕吗?管他四苕五苕,爷高兴!王世堂虽然喉咙伤痛说不出话,但喜得眼泪四溅,喉咙里发出咕哝咕哝的欢呼声。
有一天晚上,王世堂喉咙火烧火燎,起来到儿子的厨房找冷水喝。有一口囤水的大缸(因为经常停水),他舀了一瓢水正喝时,一低头看那缸里的水面上,竟映出一棵大树来,青枝绿叶,迎风摇晃,片片叶子都是桃形的。王世堂惊出一身冷汗,这不是那棵砍倒的臭娘子树吗?做成了家具的,它的魂没死,跟着木头跑到城里来了?
王世堂以为是幻觉,定眼看,分明是树影,清清楚楚,倒映在水面上。王世堂没有出声,这事儿不能说的。他推说有事,告别儿子媳妇胖孙娃,悄悄摸回老家。回去就在那个砍树的大坑旁烧香磕头。小水洼变成了大水坑,却没有了漂亮的红蛙红蛇,更不消说有鱼了,一坑死水。
过了几个月王世堂咽不进去东西,喝水都难下喉,喉咙里像塞了块火炭一样。一直他就是这样,自从喊树破嗓后,常出现吞咽困难,说话嘶哑,咔血。也自采了些草药如八角莲、七筋姑、开口箭泡水喝,有点缓解,不几天又是原样。当病情越来越严重后,被三苕接到城里去看,最后确诊为喉癌。
喉癌就是山里人所说的噎死病。为不给儿子添负担,王世堂只好回到臭娘子坳想办法。
噎死病城里的高科技奈何不了,但有羊鱼条子腮里的鱼虱可治。这鱼虱现在到哪里弄去呢?
鱼没了,是鸟没了;鸟没了,是树没了。讨厌的苦哇鸟死哪儿去了呢?那么多,说不见就不见,一只都没了。你们是在哪儿叼来的这种鱼呀?问好多乡亲,都说不知道这鱼的出处。还有患噎死病的家人不知情,跑来继续找王世堂讨要鱼虱呢。王世堂哑哑地摆手示意没了,他现在也要这个东西。
王世堂只好拖着虚弱的病体进了深山去寻找鱼和鱼虱。打进山后王世堂就不知所踪。鱼虱找到没有,不清楚。人在哪,也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