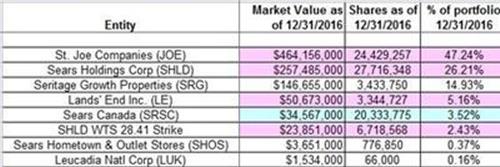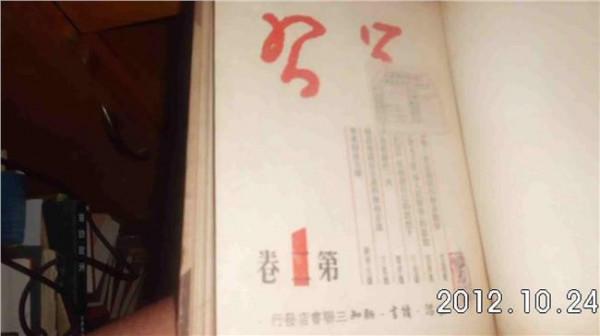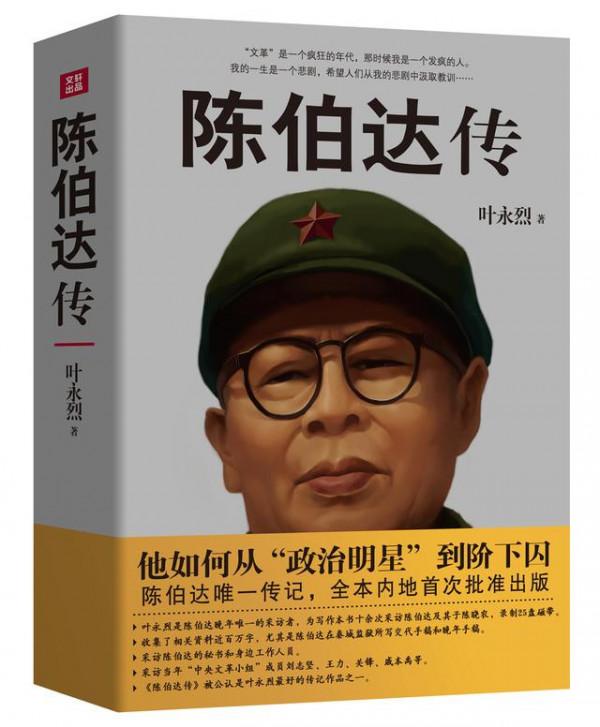陈布雷书法 萧象:陈布雷与陈伯达:书生从政之命运
萧象:陈布雷与陈伯达:书生从政之命运
20世纪的中国政治,书生从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而陈布雷与陈伯达又是书生从政的两位具有典型和比较意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一个为蒋介石文胆,一个为毛泽东秘书,在蒋、毛先后君临天下的30——40和50——60年代,曾备受主公信任而位居权力中枢,参与党政机要,传达领袖旨意,权重一方,红极一时。但最终均出人意外地以悲剧而结局——陈布雷自杀身亡,陈伯达被打入监牢。陈布雷和陈伯达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固有个体人生的喜悲丕变莫测和性格悲剧因素使然,也未尝不是一个风雨飘摇时代与动荡不安年代的背影折射。
陈布雷,189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属于清末民初一代读书人。由于科举废除和工商社会的兴起,学而优则仕不再是这一代读书人惟一的价值追求,人们可有各种方式选择自己的人生出路。陈布雷最初的人生选择是新闻记者。1911年,21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担任上海《天铎报》撰述记者,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布雷以敏锐的识见和雄健的笔力,大胆撰文,鼓吹革命,轰动京沪,一举成名。其后,陈布雷归隐故里,做起了教书先生,直至1920年才重返报界,重操旧业。此时的陈布雷历经丧母、丧父、丧妻等一系列人生变故,老成持重,锋芒内敛,但为文论政不改本色,主笔《商报》,立场鲜明,思想尖锐,笔锋犀利,议论透彻,不仅深得读者喜爱,也成为中国报界“四大主笔”之一。
1927年陈布雷的一次南昌之行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这一年年初陈布雷应邀赴赣晤见率军北伐而进驻南昌的蒋介石。此前一年,邵力子衔命先期自粤北行,联络沪上报界人士,并转赠陈布雷一张蒋介石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其推重、结交之意尽在其中。在庐山陈布雷会见了这位对自己释放善意、且即将登上中国最高权位的蒋介石,并由蒋介绍参入了国民党。此行南昌彻底改变了陈布雷的人生轨迹,使其从新闻生涯转向政治人生,由一名自在逍遥的纯粹的新闻人变为替人“捉刀代笔”的幕僚和复杂的政治人。
弃文从政、投笔从戎,古今中外所见多有,不足为奇。但像陈布雷这样热衷于新闻且已享有盛誉的人,发生这种变化,做出这种改变,仍不免让人感到好奇,而觉颇有可探之处。那么,何以一次南昌之行就改变了陈布雷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就让其“一见倾心”而“以身相许”呢?
晚年陈布雷对部下诉说过这样一段话:“先总理所说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问题,在民国16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早就问过胡汉民先生,胡先生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我又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提出此问题之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为他服务。”大致可以反映其当年的心曲,人们不难从中窥见其所以弃文从政、追随蒋介石的内在缘由。
其实,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人“得君行道”价值理想的一次现代演绎和体现。“士志于道”、“士以天下为己任”,自古以来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追求。在这一传统与价值追求的熏陶与感召下,读书人普遍怀抱这样一种人生模式,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锻炼,通过参与“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与天地立心、与生民立命、与往圣继绝学、与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
尽管到了陈布雷这一代,“做官”不再是读书人惟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与人生道路选择,人们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参与“治国、平天下”,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
但比较于其他途径,不得不承认,以“做官”为征象的“政治”途径,是通往“治国、平天下”的最直接、最得力的途径,也就是士志于之“道”得以实现的最可能的方式,如果再遇上一位“明君”,则“道”的实现就更为可能。
显然,在陈布雷看来,蒋介石是“明君”,是当时中国政治的最大希望,且礼贤下士,对自己恩惠不薄,跟随蒋这一“明君”,借助于“政治”这一通道,士子之“道”庶几可以达致。于是,在蒋的邀请下,受宠若惊的陈布雷,接过权力的聘书而走上政治的不归路。
当然,陈布雷是纯粹的书生,他追随蒋介石而涉足政治,原于“得君行道”的理想,也出乎感恩图报的忠诚,做官非其素愿,权力更非所求。“行道”和“忠君”是支配其政治人生的主要因素,并贯穿其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无论是前期扮演客卿角色,担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次长等职之时,还是后来充当幕僚进入权力中枢,出任侍从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之际,陈布雷始终谦恭自抑,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恪守本职,克己而不张扬,奉公而不弄权。即使在权力最为显赫、同时又是生活最为艰难的重庆抗战时期,依然安贫守道,为政清廉,保持了书生从政志于道的本色与尊严。正是这一难得的品行与品格,使其在蒋介石身边一呆就是十数年,成为蒋最为信任的心腹幕僚和须臾不可或缺的文胆与智囊。
毫无疑问,陈布雷在道德上是理想主义的,但性格上却又胆小懦弱。道德理想使他能洁身自好,端持清高,如一枝出泥不染的芙蕖,独立于浑浊不堪的国民党政坛而放出光泽;但胆小懦弱又使他缺乏坚强有力的意志,不敢于担当,不勇于任事,在黑暗而复杂的现实政治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莫可奈何,而感到失望。这种无法克服的内在性格矛盾,源自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让陈布雷常常纠结不已,痛苦不已。只不过,当其处于失望而痛苦之时,因有理想的支撑,尚可看到一线未来的希望,还不至于陷入绝望。可是一旦理想破灭,希望无有,脆弱的生命意志就无法承受理想的失落之重,就会轻易导致悲剧的发生。
1948年陈布雷因国势危阽前途渺茫而信念崩溃,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这一年国共内战军事势力攻守互换发生根本性转变,国民党的表现让陈布雷彻底失望。原本以为“我们国民党…… 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自信乐观,被急转直下的局势击得粉碎,国军兵败如山的战报和物价飞涨经济濒于崩溃的消息,令身处中枢的陈布雷瞠目结舌,不寒而栗。
国民党败局已定,陈布雷陷入了绝望。他没想到从政二十余年,鞠躬尽瘁,一事无成,最后竟是这种局面;二十余年中,支撑他生命的理想信念已与他为之效劳的党国事业融为一体,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党国事业就是他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党国事业,党国在,他的信念在,党国亡,他的信念灭。
如今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厦将倾,陈四顾茫然,阴郁黯淡,心灰意冷,去意萌生。
而此时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原来心心相印的亲密无间因对时局看法的歧见而出现裂痕。陈甚至因进言不合蒋意而受到斥责,这是从蒋二十余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陈布雷陈言再次受到蒋介石斥责,被指为“书生误国”,成为压垮陈布雷这头骆驼的的最后一根稻草。两天后,油尽灯枯、万念俱灰的陈布雷吞药自尽,诀别人世。
1904年生人的陈伯达,已是五四一代的知识人。五四一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为传播,使共产主义革命成为20世纪与国民革命竞争和对抗中后来居上的主流革命,无数知识人受此影响而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陈伯达便是其中之一。陈伯达于1927年在上海在国共分裂之后加入中共。此前,1921年毕业于厦门集美学校的陈伯达,当过教师,做过记者,参加过北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作品,一度欲以文学创作为职业。加入中共后不久便被派往苏联,攻读马列。归国后,1930年代,陈伯达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主要活动于平津两地之间,从事党的地下文化宣传工作,一度在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抗战前夕,陈伯达与张申府、艾思奇等左翼文化人士发起新启蒙运动,对宣传抗日具有积极影响。
抗战甫一爆发,陈伯达即于同年8月进入延安。在一次纪念孙中山的研讨会上,陈伯达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会后单独受到接见,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首次相识,其后两人多有学术上的切磋往来。1939年春陈伯达调任毛泽东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从此,跟随毛泽东不离左右,从延安到北京,从政治秘书到政治局常委,前后长达31年。
中共从来就是人才济济,即便在延安也不乏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从中脱颖而出为毛泽东看中任为秘书已是不易,做到30余年跟随前后不离左右更为难得。除开忠诚这一基本要素,敦厚、内敛的书生性格应是陈伯达长期为毛泽东信用的重要原因,陈在党内素有“老夫子”的雅称,可以说明其性格特征。他的这一性格特征决定了49年之后他在党内长期只是作为笔杆子,扮演秀才角色,起草重要文章,阐释领袖思想,而难以担纲为政,独当一面,独任一方。所以,尽管八大之后他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地位不低,还先后兼任过中宣部副部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但多是为了解工作、熟悉情况的挂职,并不握有什么可以实际操作的政治权力。这就使得陈伯达在文革前历次重大运动中没有留下什么不良记录。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改变了陈伯达的政治人生面貌。陈伯达被推上政治前台,置于运动的风口浪尖。在这场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中,陈伯达担任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命前驱,推波助澜,写下人生最具争议、也最为不堪的一页。然而,也就在陈伯达擢升为政治局常委,走上政治人生的最高点之后,随着文革迅猛发展,在诸如对待上海工人罢工和一月夺权等重大问题上,陈伯达表现出了与毛泽东的不合节拍,引发毛的批评和不满。在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中,陈伯达提出发展经济生产的主张,与毛所要求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是大相径庭,令毛泽东尤为反感和愤怒。毛陈关系由是出现裂变而最终导致陈伯达被打倒下台。
陈伯达跟随毛泽东数十年,以最能融会贯通毛泽东思想而著称,又以忠诚顺从而为毛泽东长期所信用,故此,在毛泽东决意发动文革,却手中已无用人可供前驱时,陈伯达以书生之身得以受以重任,而更上层楼。可是,在此之后的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开始发生变化,陈伯达对毛泽东没有了一如既往的配合默契,紧跟顺从,而时有不合节拍,不遂毛意,最后导致关系破裂。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陈伯达前后所扮不同角色,所处不同位置所致。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位置,有不同的身份要求和不同的历史责任担当,因此也就出现不同的行为表现。
文革前,陈伯达大致不脱幕僚身份,处于秘书位置;文革中,担任常委,进入决策层,而文革组长又是具体执行者,处于复杂多变的第一线,临事发表讲话与表态,不能事事预闻上意,如此,难免不合节拍,不出差池。但这并不意味着陈因地位上升而变得自以为是,不再听毛话,甚至对毛不忠与背离。
综观陈伯达一生,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始终谨守君臣之道,忠诚不渝,即使被无情打倒、关入监牢十几年,在毛身后,对毛崇敬,一如从前。可以说,陈对毛惟有尽忠之心,绝无犯上之意。
即便有时违背毛意而明知故犯,仍不出传统知识人的尽忠之道,在主君不智之时,尽臣子职责,明是非,辨真理,以期达到影响主君之目的。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主张发展经济生产是这样,庐山会议支持设立国家主席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