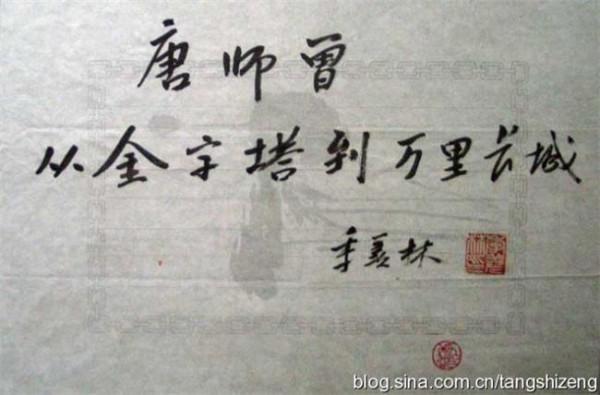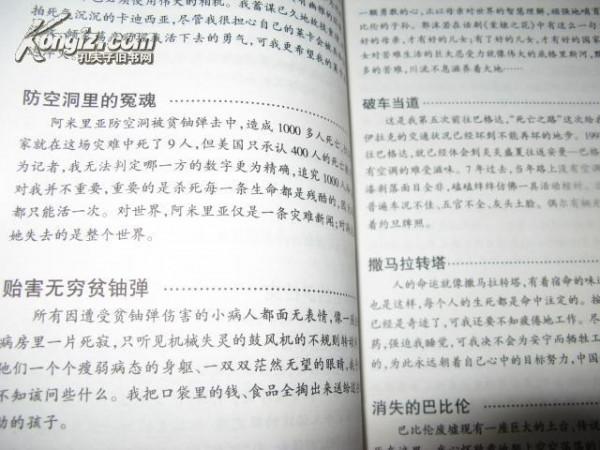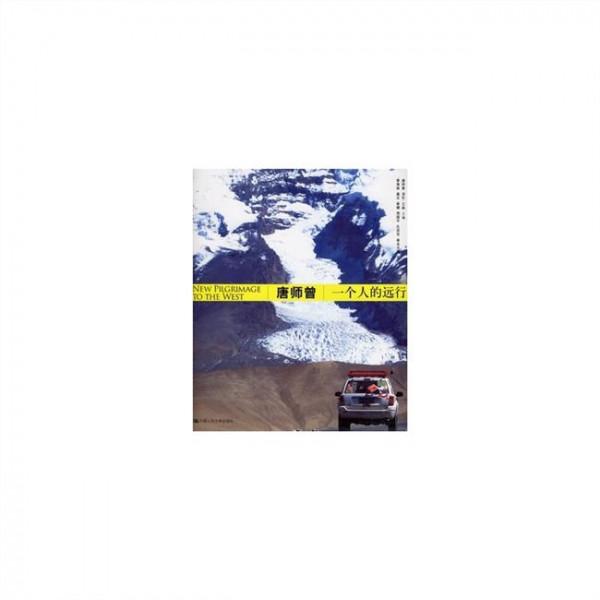唐师曾老婆 季羡林走了! 唐师曾回忆往事缅怀季老
人民网文化频道7月11日电 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今晨九时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记者连线了新华社著名记者唐师曾,正在外地出差的唐师曾听闻此讯后,连称痛惜!说他特意把1995年为季老写的文章重贴上来,以缅怀季老。
[此文约写于1995年,为新华社专稿。现为纪念季老重贴于此。]
年届90的季老先生,老僧入定般呆坐未名湖畔已近4个小时,可他那只心爱的小白猫仍端坐树端,丝毫没有下树回家的意思。老年白内障、顽固的耳疾使东方哲人耳不聪目不明,但这绝不妨碍他认真护卫树顶上嬉戏的小生命。“土猫能活十几岁,洋猫也能活七、八岁,就是得严加看管,现在人心不古,有人吃猫,也有人以贩猫为业,猫贼太多。”
整整20年前,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学兄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
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棒书本,悉心照看地上懒洋洋的行李。学兄对老者千恩万谢,庆幸自己吉人天象,头一次出远门,就碰上好人。
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学兄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学兄再次差点吓死过去。
许多年后,季老对这段故事记忆犹新,他说一位由穷乡僻壤乍到京城的穷学生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铺盖,能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托付给素昧平生的我,不亚于以身相许,是对我的极端信任。对信任,得认真对待。
季老对事认真,对人认真,对学问更认真,事事讲资料、讲考据。一日我与人民出版社、中央电视台两位校友到季老先生家闲坐,一学兄说起张中行应算季老同学,季老侧首思索半天,认真答道,张中行年龄比我大,上学比我早,毕业比我晚,应称校友,不是同学。
该学兄又问钱钟书学问如何,季老再次侧首思索半天,说虽是同学,但隔行,从未研究过。对未研究过的东西,无法评论。这种刻板的认真,也许是季先生早年留德的印记。季羡林现在能操8种语言,印度梵文、小乘巴利文、隋唐古土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德文、中文。问其哪种外语最最擅长,答曰应该是德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季羡林在德国住了十年,身上的语言功夫,大多是当年在德国奠定。
1911年8月,季羡林先生出生在山东临清一个“五代赤贫之家。”按季老的说法,山东是西边穷东边富,临清在山东的西边。临清是西边穷东边富,季老家所在的村子在临清的西边。村子里的住户是西边穷东边富,季老家住在村子的西边。
季老的父亲、叔叔都是孤儿,靠在枣树林里“捡落枣”长大。幼年的季羡林跟叔叔流浪到济南,千辛万苦才读完小学、中学,再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大、清华。1935年,季羡林考取政府官费留学生,留学德国歌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南亚古语,获博士学位。
说到留学动机,季老戏言是为了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我说梁溟明、鲁迅没有博士学位也在北大当教授。季老笑道,鲁迅是盖世奇才,可以不读博士。可他季羡林不是,普通人想在一流学府当教授,非如此不可。
季羡林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回国,立即被北大校长胡适、傅斯年聘为教授。在北大前一代大学问家陈寅恪影响下,季羡林走上印欧古典语言的治学之路。以后历任东语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现在人常讲机遇,佛家叫‘因缘’,我的一生全然由于因缘。”至于选中梵文“全因偶然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梵文课”。一直到现在,每说到恩师陈寅恪都免不了珠泪潸然。“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燕园教学生涯里,季老在东西比较文学、原始佛教语言学、印度中世纪语言学、吐火罗语义学、梵语文学诸多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奠定了泰斗地位。
几十年来,季老每天凌晨4时准时工作,直到晚10点,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作为总编之一他参与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100多卷的《传世藏书》,目前正领衔主编1000多卷的《四库全书存目》、编辑数十卷的《季羡林文集》。紧张工作之中,季老对国内外来信,每信必复,透着贯穿一生的严肃认真。
对学问如此,对生活亦如此。季羡林将文化大革命中在北大蹲牛棚的血泪经历仔细回忆,认真撰写后,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命名《牛棚杂忆》,意在教育国人。他坦率道出北大知识分子,受文革社交运动“派毒"之深,用自己双手造出牛棚这一阿鼻地狱。
季羡林认为文革中最可怕的就是“派性”,在伟大口号下,人们分成不同的革命派,互相争斗。“派性”就像一条大蛇,谁被缠上都无法脱身。他说,弄不清这是什么社会心理,在革命的旗号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朋友成仇……。
季老扪心自责,说自己也有派性。本来政治运动的浪头早已越过他,他本身也没有政治问题,大可以做逍遥派,可偏偏不甘寂寞,看不惯学校里掌权者的“老佛爷”作风,自己跳出来说话,才落得蹲牛棚的难,不能怨别人,只能怪自己。
为此,季羡林呼吁,希望当年斗过人、打过人的人能自己站出来,写些反省内心的真实文章,说说自己当时的心态。反省文革,反省自己。季老认为,我国各种运动很多,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学费,可我们真的学到教训了吗?他引用圣严法师的话“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他衷心希望中国能朝提升人口素质的方向走。
毕生认真的季羡林也曾因为过份认真饱尝苦头。1968年被打成黑帮之后,劳苦致病,甚至不能行走,自己爬行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医生。事事认真的季羡林尊从革命指示,主动自报家门“是黑帮身份”。不料原本满怀阶级感情的医生闻言立即变了脸,由春风般的温暖转变到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一脸的革命人道主义,更不用说治病救人了。
一年前我大病,后住院……由认真而慈悲的季老几次向我在北大历史系教书的大嫂转达关心,祝我康复,其认真宛若对待他自己一只心爱的病猫。江泽民访问北大,我带病去拍照,季老见状连称生命宝贵,三次劝我尽快回医院去,其认真如是。
1998年11月7日,人民出版社在北大勺园举办《世界文明史》发行式,我因为迟到而缩在门口,不想神目如电,还是被季老发现。他让助手李玉洁教授两次过来,问我是不是唐老鸭,怎么生病得忽胖忽瘦七十二变,都快认不出来了。
1979年,我在北大国政系上一年级,社科院一位前辈托我给季老家带东西,推开朗润园北面某某公寓一扇木门,季老先生正坐在重叠如千山万壑的书堆中用功。堆在桌上的各种参考书比我还高,书中夹着纸条、卡片、种种索引,一副做大学问的认真样子,令我肃然起敬。
我冒失地往沙发上一靠,竟压着一堆睡觉的猫咪。季老是中国的国宝,猫咪是季老的家宝。20年弹指过去季老还是当年那身蓝布中山装“我很保守,到哪都这么穿”,季老的猫或死或丢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他撒在未名湖后湖朗润园一带的莲子已是一片残荷。日月荏苒,可季老侍弄小动物、接人待物、研究学问依旧认真如故。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吧,季先生过生日,我记得在二教。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来祝寿,说:“我是搞数学的,对季先生的学问不太懂,为此,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季先生在北大一辈子,对他的人品,你们比我还了解,为此,我就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