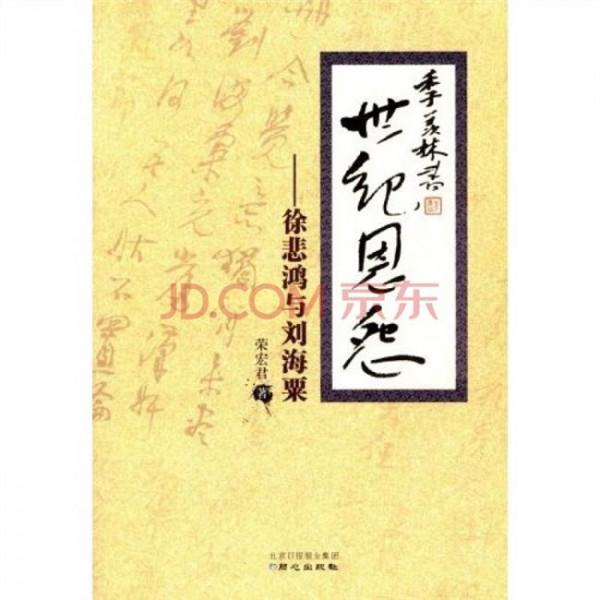张悦的照片 张悦然新篇《茧》创作谈:生命的魔法 时间的意志
——“有时候我会想一想,程恭和李佳栖(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现在在干嘛?他们在聊天吗,在吵架吗?在吃蛋炒饭还是炸酱面?”
一个是受人敬仰,光环笼罩的院士;一个是瘫痪在床,意识全无的植物人。一根生锈的铁钉如何造就两个家族截然不同的命运?荣耀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悲剧?两个生于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同样遭受着缺失父母之爱的痛苦,追寻着上一代的足迹,线索却指引他们发现一个庞大而不堪的真相。1967年的雨夜,废弃的德军建造的水塔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八零后代表作家张悦然最新长篇《茧》发表于近日出版的今年第2期《收获》,引起评论界高度关注。与张悦然以往如同空中花园般唯美而梦幻的作品不同,《茧》是一部以80后一代人的视角直面祖辈、父辈恩怨纠葛的转折之作,通过一桩骇人罪案层层抽丝剥茧的漫长过程,将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展开在读者面前。
《收获》主编程永新评价这部作品说:“青年作家不仅挑战自己,更挑战历史和记忆。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评论家张莉则说:“整部小说叙述绵密,丰盈,元气淋漓,作为读者,你会在阅读时不断感叹,这部长篇很可能意味着张悦然另一个黄金写作期的到来。”
第一次写到家乡济南
张悦然说:“《茧》包含着一些对历史的思考,以及如何看待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并且对于爱的继承、罪的流传做了一些探究。这些都和我之前的小说不一样。像《誓鸟》或者再以前的小说,和现实关联很小,但是《茧》是结结实实长在地上,并且扎根很深的。它不仅写了历史和现实,也写了世俗生活。”
在这部小说里,张悦然第一次写到了她长大的地方——济南。正如她在这部小说中所采取直面历史创伤的态度一样,张悦然没有以J城或N城等代称去模糊这座城市的形象,但也没有以强调特有的风物人情去加深它的形象。“我只是很自然地进入回忆,把那种小时候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感觉带到故事里来,”张悦然说,“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的个人生活距离很遥远的故事。
但是随着写作的进行,个人记忆不断被召唤,来到小说里,拉近着我和故事的距离。到了快写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相信这好像就是发生在我童年的事。”
张悦然透露,这部小说用到很多她的个人经验。例如小说中主要故事发生的场所“南院”,就是张悦然小时候生活的山东大学的家属院。“死人塔”、“小白楼”等小说中的地标也都有原型。
取材真实历史事件
张悦然表示,《茧》的整个故事都是杜撰的,除了位于故事核心的那起悬案。它发生于“文革”期间济南的一家医院,张悦然从父亲那里听说了这件事,随后做了很多调查和采访。“使我感兴趣的是受害人和作案者仍旧生活在同一座医院的职工大院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甚至他们的孙辈,他们是邻居,可能会一起玩,可能会成为朋友。
而他们的孙辈,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如果知道了当年的事,他们会怎么看,怎么做呢?这是否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影响呢,这是否也会改变他们,或者塑造他们呢?这些问题是我很想去探讨的。”
写完这部品之后有一段时间了,在张悦然的意识里,小说中的人物似乎还在前行,而他们年轻的生命还将遇见什么,她也十分好奇——“有时候我会想一想,程恭和李佳栖(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现在在干嘛?他们在聊天吗,在吵架吗?在吃蛋炒饭还是炸酱面?”
《茧》的完成对张悦然的写作生涯而言几乎相当于一次重生。她感悟道:“我曾经执迷于所谓的悲剧性,觉得那是某种审美的至高追求,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撼动人心的是那些卑微人物身上所发出的光芒。他们被一束光照亮了,生命抵达了更深邃的层面,这些也许才是重要的。”
评论家金理认为:“某种意义上,《茧》提供的是一部关于创伤记忆‘代际传递’的小说。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一位是负罪者,一位是复仇者,因袭着巨大的创痛,既徘徊在历史边缘,又主动与周围世界疏离……”他观察到,与张悦然此前的作品相比,《茧》的结尾更多显露出作者的善意,“这部小说如同病历档案,同时也提供了一份康复记录”。
从“流连幻想”转向“扎根现实”
从流连于幻想,到扎根于历史与现实,张悦然的“转向”让许多长期关注她的读者和评论家感到惊喜。
评论家张莉说:“小说对历史的贴近与同情的理解态度使人意识到,张悦然创作的某个节点已经到来。她不再执拗地只对‘我’和‘我的情感’,‘我’和‘我的现实’感兴趣了,她开始对‘我的纵深’,‘我的历史’有不一样的理解。她找到了属于她的历史挖掘机。”
对此,张悦然曾表示,她的“转向”并非“断崖式”,而是有迹可循。“现实就在眼前,如此巨大,我就生活在现实里,对于这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思考一直持续着,到了《茧》,或许有了一种推进和延展。”
谈及视野从“我的现实”扩展到“我的历史”的动因,张悦然坦承:“在度过了叛逆的青春期之后,我渐渐发现我们和我们的父辈、祖辈之间紧密的联系,意识到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甚至知之甚少的历史事件也在影响着我们,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但是间接的影响未必微小;这种影响可能是看不见的,像一些隐形的线,牵系着我们,绑束着我们。”
由于上述原因,在《茧》的写作中,张悦然采取了让两个年轻的主人公轮流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过去的结构方式,她说:“我想我不能把视线移开,必须记录下他们怎样去探知真相,知道以后的态度,又是如何在它的影响下成长的整个过程。而且作为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后代,他们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起去面对祖辈、父辈的恩怨,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勇敢、坦诚面对历史的方式。”
个人视角与国族历史的绵密榫合
阅读《茧》之前,评论家李壮曾有些为张悦然担忧。他说:“近年来,中国文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诸多青年小说家为跳出青春语调和私人经验的囹圄,开始在写作中尝试涉及历史题材。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巨大的题材和架构盖住了作者自己的声音,辨识度下降;再比如写作者也容易‘为历史而历史’,尽管在时空跨度上颇显宏阔,却无法将这种宏阔的背景榫合于人物的内心纹理。
初看《茧》时,我本也有这种担忧,但值得庆幸的是,《茧》在故事上同历史紧密关联,但书写的重心依然是最具触感的个体命运和精神生活世界——国史、家史与个体精神史的血肉,在这部作品中真正生长到了一起。
并且,一如既往,这部作品继承了张悦然标志性的‘冷艳’,显示出一种凌厉甚至残酷的才华,却又不失节制。它浓烈而独特的美学氛围仿佛凭空结构出一片磁场,将读者瞬间抛掷到了另一个虚拟的时间刻度之中。”
在张莉看来:“《茧》的新鲜并不在于它对历史的复原和对罪恶故事的讲述,而在于张悦然书写的视角。这是逆流,是追溯,是由近而远,由此及彼,它与许多年长者、历史在场者的回忆与见证视角相异,这样的追溯中掺杂着疏离、审视以及好奇,那是基于对自我,对家族的好奇,也是对国族历史的一次重新认知。”
作家简介
张悦然,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作品刊载于《收获》、《人民文学》、《天涯》等文学期刊。 著有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西班牙语、日语、德语等多国文字。
曾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散文奖”、“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评选的“未来大家Top20”,长篇小说《誓鸟》入选“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集《十爱》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2008年创办了文学主题书《鲤》系列,并担任其主编。2012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