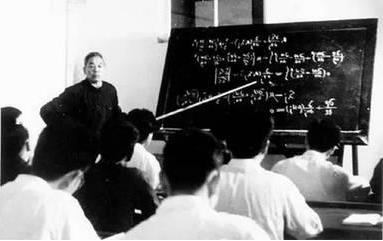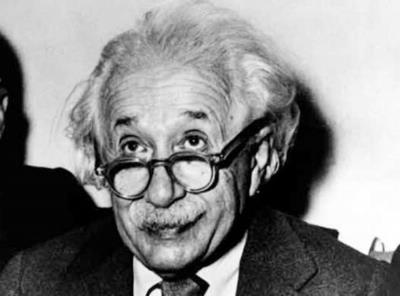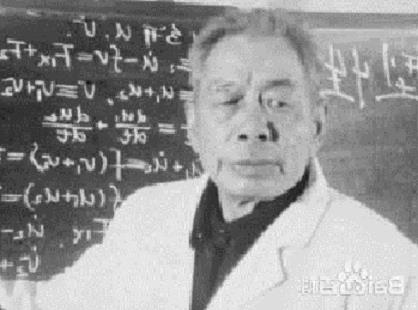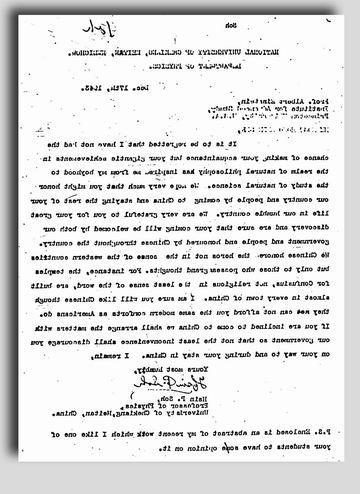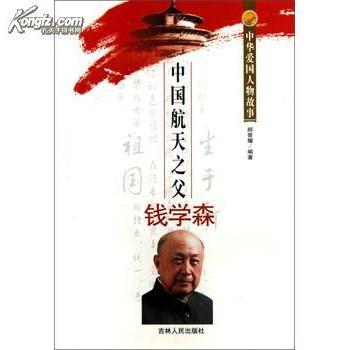束星北的贡献 真实的束星北与真实的新中国科技事业
作为物理学家的束星北,2005年以前大概很少有人听说过。但2005年刘海军著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以下简称《档案》)出版后,引起了人们广泛注意和评论。不少人对一个天才物理学家湮没如此之久产生了浓厚的探究兴趣,纷纷各抒己见。
其中有些文人学者的观点颇为引人注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题为“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该文作者认为,如果束星北不回国,“得诺贝尔奖也未可得知。”“可惜,中年以后的束星北不能拥有这样一片土地,而他所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也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科学奖。”
那些文人学者或许忽视了国内外的物理发展历史,所接触到的印象只停留在《档案》中的对束星北的描述上,诸如:“天下第一才子”和“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等等。当然,一些媒体将束星北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也可能对这些文人学者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束星北的“天才”与“土壤”问题,到近年仍然被一些文人学者提起。例如,有人在《档案》出版十年之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束星北的苦难与思考》(网络转载曾用标题《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是如何陨落的》)。
该文认为,“这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还沉湎于活跃的思想火花碰撞中,等待着创造力爆发的那一刻。但他再也等不到了……”“这是物理学天才束星北生命中永远的遗憾,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关于束星北是“天才”物理学家一说,只出现在刘海军这样的传记文学作品和一些文人学者的文章中。海内外对他有所了解的物理学界的同行们,特别是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物理学人士,一般都承认束星北在物理教学方面的水平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对于物理学研究,尽管束星北有过一些很有远见的想法,但遗憾的是未能坚持下去,因而没有作出什么有重要影响的贡献。
早在2006年7月,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就指出:《档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我们这些‘圈内’人士的关注:我们只知道束星北教授是一位在课堂上颇受欢迎的学者,却从没听说,这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
那么,“圈内”人士是不是这样看待束星北的呢?
作为教育家的束星北令人非常钦佩
束星北1907年出生在江苏。1926年自费赴欧美留学。1931年回国后,于1936年至1952年担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和教授。1952年起任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1960年至1967年因政治原因被下放到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1978年被聘为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得以平反。1983年10月因病逝世。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期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浙大的学生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还有李文铸、李寿木丹、许良英和周志成等学界名人。另外,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王淦昌,在浙江大学期间是束星北的同事。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圈内”人。
这些“圈内”人对束星北的授课水平非常钦佩。王淦昌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基础坚实,思维敏捷,对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他指出束星北在当时物理系里,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王淦昌自愧自己“无论如何也学不来”。李政道说,他是在和束星北、王淦昌接触多了,才“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
他在1972年给束星北的信中写道:“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寿木丹在《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文中指出,束星北“讲课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培养了一批优秀理论物理人才”。
2008年获得美国物理学会“安德烈萨哈洛夫奖”的许良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他对束星北的授课水平也非常佩服。他说:“束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
◆束星北在授课。
实际上,就教学水平而言,应该说束星北和王淦昌难分伯仲,只是风格有所不同而已。李政道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这种早期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曾有过的讨论以及他们使我激起的对物理的热情。
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教授还特别慷慨地给予我关心与指导,尽管我当时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李政道与束星北和王淦昌的交往,是物理学界流传的佳话。曾任浙江省科技协会副主席的物理学家李文铸和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志成都特别提到了李政道是怎样转投到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门下的。
1944年底,日军逼近黔桂,李想参加青年军,因车祸腿骨折断,束星北得知后就打电报给王淦昌,让他看住李政道不让他走动,更不让他去青年军。当时日军打到贵州独山,浙大已在风雨飘摇中。束星北等李政道腿骨长好后,把李政道介绍给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吴大猷。
作为科学家的束星北的弱点
有意思的是,吴大猷对束星北在物理研究上的评价相当一般。这在吴大猷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90年代中期,李政道向吴大猷和王淦昌提出,希望他们把193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物理学萌芽时期这段历史写下来,“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面貌”。吴大猷接受了这个建议,从1997年3月开始,每周分别到台北台湾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讲述这段历史,但还没来得及整理成文字出版,就因病于2000年3月在台湾逝世。
于是,两岸物理学界知名学者黄伟彦(曾任台湾大学物理系主任)、叶铭汉(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学科创建者)将吴大猷的讲述内容整理成书,以《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以下简称《回忆》)为书名,先后于2001年和2006年在台湾和大陆出版。
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几位学者加了很重要的“注”。
沈君山(物理学家、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在该书的《繁体字版序二》中强调指出,“凡吴先生在讲演中提及的人均经叶、戴两位详细精确地考证,简注其生平,这一部分本身就是珍贵的史料。”(见《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关于束星北,吴大猷在《回忆》一书中说道:“有一位先生叫束星北……这位先生在欧洲和美国这两边跑来跑去,所以,也没有真正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过研究……据我所知,他写了一两篇文章,把地心引力跟电磁场联合起来,这个东西是爱因斯坦做了一辈子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
该书人名注释中的“束星北”词条下的有关物理研究的内容为:“束星北早年从事相对论研究,探索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虽然他未能取得实质意义的进展,但他的有关研究在当时还是有启发性的。”“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束星北研究了波动方面的解,也研究气象学,1970年代后期,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回忆》 第172页)
现在一般人都是通过《档案》那本传记文学知道束星北的。关于“由于种种原因,他受到很大冲击,遭到很不公正的待遇”(见王淦昌《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的那段历史,也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命运很值得同情。但这与他在物理学研究上未能取得重要成果,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的,更谈不上是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
《回忆》无疑是一部关于物理学比较权威的著述,该书对物理学家的评价也可以说是代表了物理学“圈内”的主流看法。如果要印证书中对某位物理学家的评价,还可以参阅其它的有关史料。例如关于束星北,就可以看看海洋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胡杨之魂 束星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这本文集中的束星北生前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王淦昌的《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就收录其中。
必须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这些回忆文章中,作为“圈内”人的李政道、王淦昌、程开甲等,没有一个称束星北是“天才”物理学家,是“领军”人物。现在流传的程开甲的“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那段话,虽然没有出现在《文集》程开甲的文章中,但通过《文集》中的程开甲的《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思想》一文,还是可以看出束星北的物理天赋和才华,特别是作为一个教育家。
不过,程开甲也直率地指出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束星北的弱点。
程开甲在肯定了束星北对一些物理学问题有“深入远见”后又指出:“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去的其它研究工作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程开甲举出了当年束星北和王淦昌讨论核物理(包括击破原子核等当时世界物理很前沿的课题)的例子,说:“1941年夏天,他组织讨论如何击破原子核。
当时,束先生回上海,此事就停下来。”程开甲还指出:“……束先生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
他认为物理学要有深刻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跟着做计算。这一点可能有片面性,没有计算的实践,就没有理性的认识依据。这方面束先生偏离自己的实事求是,从事实逐步分析的信念。正是在这里,可能妨碍着束先生自己在具体工作上的成就。”(《文集》第28页、第30页)
束星北的另一位学生李寿木丹在《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文中,也遗憾地指出,束星北对一些课题创造性的尝试“未能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文集》第37页)在举出一些例子后说:“可惜上述这些工作,当时都没能进行到底,没能写成文章发表。”(《文集》 第43页)
束星北的性格对他的物理学研究的影响很大
不像一些文人学者和许多网民的推崇,“圈内”人士中对《档案》中涉及到束星北在物理发展史上地位方面的典型言论,基本上都未予肯定。更有人坦率指出了书中的“浮夸”之处,例如《档案》出版后不久,当时的中山大学物理学教授关洪,就撰文认为束星北够不够得上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还是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专家樊洪业在《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见2005年9月15日《南方周末》)一文中,指出在当年浙大校长竺可桢心目中的束星北,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人。
“对束星北之为人,竺在日记中赞语无多,批评的话倒是不少”。“从竺可桢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个心多旁骛的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44年跑到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去作高级打工,受了那1万元高薪的诱惑而离开了浙大的教研岗位。”解放后束星北自己曾也反省过这些有关自己的“品质”问题。
许良英是束星北在浙大期间最欣赏的学生之一。许良英同意樊洪业文中的竺可桢对束星北的看法。他在肯定束星北科学造诣很深,为人坦诚豪放、有正义感后指出,束星北是一个轮廓鲜明的人,优点非常突出,缺点也非常突出,而这些缺点使束星北在物理学研究上难有大的成就。
据许良英回忆,束星北对钱看得比较重。1941年夏季束星北回去为母奔丧(也就是前面程开甲说的束星北中断核物理讨论回上海一事),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回来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去上海想靠炒股票生活,结果全亏了。
还有1944年春主动去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工作。因为这个单位是军统特务机关,稍有开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束星北却主动去了,因为工资高,每月1万元,而当时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
后面这件事对束星北后来遭到一系列麻烦留下了隐患。解放后束星北遇到的第一个麻烦也是因为这件事。好在有许良英、周志成和李文铸等几位昔日的中共地下党员学生的据理力争,才暂时保了平安。
许良英是中国科学院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他不认为是“土壤”扼杀了束星北的天才。但他认为“土壤”造成了束星北心灵的“扭曲”,最明显的事例就是束星北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的争议。
关于这个“爱因斯坦的助手”的争议,又来自于许良英作为主译的一套《爱因斯坦文集》。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许良英看到后,给束星北寄去了一套《爱因斯坦文集》,请其批评指正。
但束在回信中说“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了。“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时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
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许良英的理解是,“惟一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
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心灵被扭曲了,原来的是非标准都会颠倒过来。
特别是1957年开始,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的得势,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会‘觉悟’到,你们都大说假话,我为什么不可以?”(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 2005年12月23日B3版)
但实际上,束星北并没有不重视《爱因斯坦文集》,而是另有原因。据束星北女儿束美新回忆,束星北肯定了许良英的努力,但“可惜这本书好多地方都翻译得不准确。”(《文集》第263页)当时束星北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主办进修班,在谈到翻译的重要性时也向学员说过:“比如我早年的一个学生曾寄给我一套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我觉得他对原文的有些意思未完全搞懂就翻译了。
”(《文集》第162页)束美新还说,束星北希望等有机会见面时再向许良英指出这些问题。
束星北的子女和一些浙江大学的老校友,例如杨竹亭、王彬华、孙沩等都对许良英的说法反应强烈。他们说,不是解放后、反右后,而是在上世纪40年代,就知道或听说束星北担任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事情。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的采访记者宫苏艺回忆,他是通过时任《光明日报》科学副刊组长的金涛,获知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助手的信息的。
由此可见,把这件事归咎于“土壤”造成束星北心灵“扭曲”,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
因为即使束星北有意伪造,那也是解放前的事情,这与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又有何关系?有一位后来成了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夏综万先生,曾在海洋第一研究所听过束星北的课,非常佩服束星北的学问和做人。
他在2007年5月撰文道:“最近竟然有个别人对束老师1979年春天对记者讲曾当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的这件事有怀疑,认为是受到‘十年动乱’坏风气的影响而说的谎,因而引起对他人格的质疑。
我们要说,这些人对束老师20世纪30-40年代的情况不去作进一步调查、对他1979年所处的环境一点也不去了解,仅凭主观臆测,就乱下结论(甚至是对着他们过去尊敬的老师)这是很不应该的。”(《文集》第202-203页)
不过,许良英也认为,束星北之所以未能在解放后做出像王淦昌、竺可桢等人那样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是因为束与王、竺不是同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和竺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
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他还举出自己经历过的事例,说明束星北不关心科学前沿。当时的科学信息的载体是专业期刊,而束有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不看科学刊物。许良英指出:“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
◆1980年束星北(左)与挚友王淦昌在青岛合影。
的确,束星北一直没有能够把整个心思放在某个单一领域的科学探索上,这从《文集》里的诸多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除了他受到政治问题的波及外,他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他不断变动努力方向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早在抗战时期,他曾偷偷跑出来练拼刺,准备直接上战场。
解放初期,觉得国家急需抓农业问题,他又潜心研究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气象问题。王淦昌对束星北能很快在气象这个全新领域作出成绩表示钦佩,说:“我还是钦佩星北对新的业务接受得很快。
”(《文集》第20页)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出自于什么因素导致的改行,束星北干一行钻一行,始终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他晚年为我国的海洋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临去世前,他一再叮嘱身后一定要穿着海洋服(当时准军事单位国家海洋局系统的制服)。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一生的追求。
两本书的启示
通过《文集》中束星北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可以使广大读者了解到束星北的方方面面。比起传记文学,应该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文集》也收集了一些文人学者的评论,其观点带有作者较强的主观意识也是不足为奇的。比如《天才需要怎样的土壤》所说的“至今也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结果屠呦呦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就给予了最好的回答,而且屠呦呦是新中国成立后土生土长的科学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前。
顺便提一下,樊洪业、关洪和许良英的文章均未收录在《文集》中。因此,阅读这类文集,首先应该注重的还是亲朋好友的回忆。如要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事人,以及所处的历史背景,最好与其它比较权威的著述进行印证。
《回忆》是一部比较权威的物理学史著述。从这部著述中,读者不但可以了解到“圈内”人士对束星北本人的评价,还能了解到新中国物理发展的真实情况。此书注释中的物理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一直在海外,有的去了台湾,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回到大陆的共计49位。
这其中,包括束星北在内的6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受到不公正对待,其中4位还在“文革”期间死于非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教训。另外43位,则都在工作岗位上较好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其中有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钱三强、彭桓武、赵忠尧、郭永怀、还有王淦昌、程开甲等等。他们都为物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了著名物理学家。
◆两本书:《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胡杨之魂 束星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樊洪业在谈到中国近现代的物理学史时指出:“像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那一批后起之秀,虽然在1940年代已露尖尖角,但他们真正在中国物理学界担纲带队,还是在1950年代。在这张物理学的先贤榜上,束星北自当有其应有的地位,但他绝对没有达到《束》书中所称中国物理学‘领军人物’的地位。”樊洪业还指出,“在1949年以前,他没有像王淦昌那样对科学研究的锲而不舍,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像王淦昌那样的骄人成绩。”
1992年5月31日,北京举行了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包括大陆的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王淦昌,台湾的吴大猷,美国的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顾毓秀等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当王淦昌发言时,李政道问道:“王老师,在你所从事的众多项科研工作中,你认为哪项是你最为满意的?”王淦昌考虑片刻后回答说:“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
”对于王淦昌那些物理学家来说,“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做我想做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王淦昌:《无尽的追问》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第140页)
李文铸在《怀念束星北老师》一文中写道:“我在解放后,虽然一直担任各项党政领导工作,不断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但我一直坚持工作在物理学的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从来没间断过,一直到70岁离休,这都是由于束老师培养教育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做到的。”(《文集》第56页)
从王淦昌和李文铸身上,可以看到,总的来说,新中国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好平台。但从束星北的身上,又反映了党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经历过的一些曲折。一个是主流,一个是支流。通过《文集》,读者应该同样可以发现,实际上束星北本人也是这样看待新中国的那段历史的。
束星北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亲身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经常受到的屈辱。他说:“那时受到的屈辱,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超过白人,为中国人争光!”作为一个对核爆炸早就非常熟悉的物理学家,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非常清楚一个国家拥有核威慑意味着什么。
束星北在1964年向有关组织提出研制核武器以防止核战争的建议,并曾两次向统战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他有三个在国外熟识的核物理学家,他“可以协助党动员他们回国。
”当1964年10月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束星北立刻嚎啕大哭起来。他为自己不能与王淦昌、程开甲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但他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
对于长期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束星北鲜有抱怨。他更没有失去对这个国家这个党的希望。1982年,他对他当年在浙大的学生、地下党员周志成说:“说来也怪,划右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划了右派,却了解了党。我曾经问过把我划为右派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划为右派不可?他说:‘你这个人看上去就像反革命,越看越像’。
可见整我是主观主义,与国民党的勾心斗角还有原则区别,这其一。其二,是发现整错了,就登门道歉,这很了不起,是国民党绝对做不到的。”
应该说,这的确是束星北的情怀。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谈的,但我爱国,也爱共产党,因为我束星北经历过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内外的事情见的多了,心里明白中国共产党最好,这一点可以告诉任何人。”
因此,王淦昌在介绍束星北时说:“解放后,他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致力于物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历经人世沧桑。”(《文集》第18页)(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