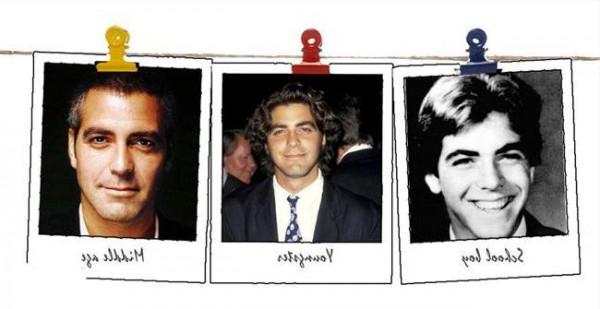牛玉儒真相 妻子谢莉:我与玉儒相濡以沫走过25年岁月
我叫谢莉。同玉儒相伴携手25年,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在他生命最后的90多个日夜,成为我和玉儒一生相守最长的日子。
2004年4月26日上午,忽然接到市委一位领导打来的电话。告知我,玉儒在内蒙古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肠子上长了一个东西,需到北京作进一步检查,有住院治疗的可能,要我作好一同赴京的准备。顿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多少年来一直令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这架不停运转的机器终于出现了故障!
简单收拾之后,我与刚走出市人代会闭幕会场的玉儒乘中午的班机赶往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告诉我他已是结肠癌肝转移。
听到这可怕的结果,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医院一个僻静的角落,我失声恸哭!
我怨他、气他;也怨自己、气自己。他平时从不听我一句相劝,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不吝惜自己的身体。都到这份上了,他还在与大夫交涉:要尽量在“五·一”长假期间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地,7天拆线,10天出院能回家安排工作。
我强作镇静,但玉儒还是看出了我的悲伤。反倒安慰起我来,他说:“我会没事的,怎么也得再活3到5年,我对呼市老百姓的承诺还没有兑现,要干的事儿还多着呢……”
5月3日,主治大夫被他的执著打动,为他进行了切除手术。3天后,玉儒果真下地行走。尽管进食对他已经非常痛苦,但为了恢复体力,能早日回去投入工作,他在以顽强的毅力抗衡着。
多少年来,我早巳习惯和适应了玉儒的工作节奏。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是如此。他每天躺在病房里,从早到晚不停地通过电话安排布置工作,不停地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商讨从电话里反馈来的情况。他的忙碌对我来说似乎都习以为常,在医院与在家里仿佛没什么两样。
同玉儒生活25年,我深深地了解他。从1980年我们结婚那天起,我就明白,他是一个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的人。我们仅有的3天婚假,就因工作忙而一天也没与我共享。
在我的印象中,玉儒永远有开不完的会,出不完的差。细算起来,25年来,我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5年。
特别是去年玉儒到呼市任职后,工作节奏更快了。上任的第三天,呼市的非典疫情迅速蔓延。他一连40多天没回家,吃住在办公室里。我每天只能从电视上追寻他的踪迹。可每次看完电视,我又是一夜的担心与害怕。他天天步履匆匆,不是到医院慰问医护人员,就是在最危险的一线视察工作,别人都“全副武装”,而他连个口罩也不戴。这能不让人担心?疫情结束了,玉儒回到家,我把他拽到人体秤上一称,他竟整整瘦了6斤。
本想这回该歇息几天了,可他更忙了。自治区两个文明经验交流会在呼市召开,全市上下都在为“迎会”备战。玉儒回家的时间更晚了。有几次我曾电话催他早点回家休息,连打几次后,他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后来,我就向司机求助。哪知回家后,他进门就大发脾气,要我不要干扰他的工作。
那些日子,我看他实在太累了,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一到晚上我就早早地为他备好洗脚水,挤好牙膏,等着他回来。可他回家的时间根本没个点。有时等回来了,当我把洗脚水端到床前时,他已呼呼地睡着了。我只能在他睡熟的时候为他擦把脸、洗洗脚。看着他像孩子一样沉沉酣睡的模样,我常常整夜坐在他旁边悄悄抹眼泪。也许只有此时,玉儒才完全属于我。
玉儒回来得晚,可早上起得特别早。经常我醒来时,他人早走没影了。上班前“微服私访”是他的惯例。对此,我常常疑惑不解,他这样当领导是不是有点傻啊?可他安慰我说:“请你多体量我一些,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干,上有组织的重托,下有对老百姓的承诺,我这个市委书记别无选择。等将来我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着你,给你做饭,干家务活儿……”
有一次,玉儒外出招商引资,因飞机晚点,回来得很晚。我等他到12点钟还不见影子,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发现他的行李包在,但人早已不知去向。我急忙给他打手机,他已在去往包头考察的路上了……
玉儒在包头任市长时,也是一个地道的工作狂。有段时间他每到晚上就发高烧。当时正值包头城中村改造进入关键时期,他忙得连到医院检查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总是回家很晚。早上起来,两片索密痛下肚就又匆匆上班了。不久,他到上海出差,返回时,打来电话说当晚就能从北京转飞回到包头。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得知他依然在晚上发高烧,更严重的是还在便血。我苦苦哀求他到北京后去医院好好作一次全面检查。可他固执地说转乘机票都买好了。我当时急坏了,放下电话,就赶到飞机场,连夜到了北京,硬是在北京机场把他拦了下来。到医院一作检查,诊断为腺性膀胱炎。第二天回到家,烧一退,他就又匆匆上班去了。
那些天,他每天晚上高烧不退,时时浑身发抖,用两床棉被捂着还冷得瑟瑟发抖。看着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我哭诉着向他乞求,别再这样没白没夜地干下去了,就是一台铁做的机器也有停转、检修的时候,何况你一个血肉之躯呢!
可他自信地安慰我说:“没事的,我这命硬着呢。小的时候,我都死过两次了,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
玉儒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诉他苦难的童年。在他7岁那年,母亲突然病逝,留下他们兄妹6人。最小的妹妹刚刚6个月。大哥也只有11岁。工作繁忙的父亲根本无力照料他们兄妹,就把玉儒以及二哥和一个妹妹送到了乡下的二叔家来寄养。
50年代未的东北农村,生活依然穷苦。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靠二叔一个人的工分来支撑。玉儒兄妹的到来让二叔家的日子更显紧巴。在玉儒儿时的记忆中,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与寒冷中度过的。哲盟的冬天异常寒冷,他不记得自己穿过棉衣和棉鞋,脚上满是冻疮。冬天与哥哥们出去拾粪,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到路边沟里的背风处取取暖。他曾两次病重,高烧不退,几乎死去,可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二叔特喜欢他的吃苦劲儿,农活没有他不会干的。玉儒17岁时,到通辽农村插队。他是最受村民欢迎的好知青。逢年过节从不回家。不是在村里帮助村民义务磨面就是帮着干其它农活。玉儒25岁就被推选为通辽县莫力庙人民公社党委书记。
那时的农村自行车已开始代步,社、队干部骑自行车已很普遍,可玉儒凭着自己的一双硬脚板踏遍了公社20多个大队,生产队方圆近百里的田野、村落。他对工作热忱负责的态度赢得当地百姓的拥戴。村民都把他当亲儿子来看待。他特别喜欢吃农家饭菜,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觉得回味无穷。更让他值得回味的是与老百姓那种永远难以割舍的亲情!正是这种亲情支撑着他义无反顾地献身党的改革事业。
玉儒后来调到自治区政府工作,特别是担任政府办公厅秘书长期间,我们家里接待最频繁的客人就是那些素昧平生的上访群众。玉儒从来都是一一热情接待,要我给他们沏茶倒水。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些群众既然能找上门来,他们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否则,素不相识的,怎么会上门求助。咱们可千万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再冷了他们的心。”
多少年来,他为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办过无数实事儿、好事儿,可在他的亲戚当中好多认为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官。他的5个兄妹至今仍在通辽老家,其中两个妹妹和妹夫都下了岗。他的姑妈自从母亲去逝后就包揽了他们兄妹所有的针线活儿,给过他们兄妹很多关照。
可他的姑夫至今还在通辽火车站靠蹬三轮车来维持生计。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他当大官了,都来投奔,可玉儒总是让人家高兴而来,扫兴而去。他说:“我的权利是人民给我的,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随便支配。”
其实,在玉儒心中,他并非没有亲情。他念念不忘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二叔。今年春节,他回老家专程看望了二叔。二叔还是住着当年的土坯房子。盘腿坐在二叔的土坑上,玉儒依然能找到儿时的感觉。听说二叔要盖新房子了,就让我把身上剩余的三千元全部留给了二叔。回家后,他一脸悲伤,遗憾给二叔留的钱太少。他说二叔对他有养育之恩,却从来没图他报答什么。整整一个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次,玉儒到通辽开会。父亲得知后要他抽空回家吃顿团员饭。一家人高兴地从一大早就开始张罗。饭菜备好了,整整等了两天也没等回他来。爸爸颤抖着手指头计算着,自85年春节后,玉儒还再没有回来过。其实,那次不是玉儒不想回去,是他随团又到别的地方考察去了,实在抽不开身呀。
今年已81岁的老父亲对玉儒一直寄予很高的期望。几年前,父亲在给玉儒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我从不担心你会犯什么错误,就担心你能不能永远地去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
多少年来,玉儒一直把父亲的教诲铭记心间!他以事业为重,以人民为重,常常忽视了自己。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实现着他的理想和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
住院三个月,玉儒曾回呼三次。每次回呼都是在化疗后的5、6天,身体刚刚开始恢复。记得第一次回呼,是他专门回去检查城市建设情况。下午6点半下了飞机,第二天一早,他就组织人员乘中巴车到市区各处观看工程进展情况。快中午12点了,还不见他回来。我非常焦急,与秘书联系后立即打的赶往视察点。可总是晚一步。秘书说,这些视察点都是玉儒随机选定的。我最终也没能追上他。
7月16日,市委召开九届六次全委会议。为了能在大会上发言,玉儒作了长时间的准备,记得是第二次化疗刚结束,他特能吃东西,精神状态好的让大夫都感觉惊奇,他每天积极地去量体重。可当他发现自己的体重在直线下降,竟不到110斤时,就生气地说:“怎么这个化疗就像在吃我的肉。”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去量体重了。就是大夫催他去量,他也不去。
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要召开了,他提前一天回到呼市。进了家门就让我给他准备第二天参加会议的衣服。翻遍衣柜,他的衣服大都不能穿了。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都不到2尺3寸了。他说就多穿几件内衣吧,尽量别让人们看出我身体上的变化。
他兴致很高地一件一件在衣镜前试穿着,还让我和女儿从后背看看他的肩膀是否还是那样显得干瘪。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在极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里三层、外三层到底穿了多少件衣服,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数。7月的天,正值酷夏,这对一个刚刚做完化疗的病人来说是多么的残忍……
第二天一早,他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地走出家门开会去了。我的心也跟了去。整整一个上午,我无数次到院门外迎他回来,可小巷内总定空无一人。等到12点过了,他才脸色惨白、被司机搀扶着回到家。
他无力地倒在床边,双眼紧闭,连调整自己合适姿势的力气都没有,好久好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和女儿都被吓坏了。后来才得知,他在大会上作了2个小时10分钟的即兴讲话……
第二天,稍微缓过点神来,他又去城建委听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工作汇报……
住院三个月,他从来没把自己当病人来对待。就是在进入肝昏迷状态,他的心里还在牵挂着他手头的那些工作。
有一次,女儿为了分散他的精力,故意给他讲笑话,解除他的疲劳。他眼睛盯着女儿,看似在认真听孩子讲。可突然间从他嘴里冒出一串手机号码,并要女儿马上给他拨通。看到根本就没有把精力从上作中分散出来的父亲,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着跑出了病房。
8月10日,玉儒已深度昏迷。他已不大能说话了。在又一次昏睡醒来后,他发现我红肿着双眼坐在他床边,嚅动着双唇仿佛要向我表白什么。他的眼神那么温和,恋恋不舍,却又显得那样无奈。他的眼眶很快溢满了泪花,仿佛在向我暗示,就要离我而去了……
从这以后,玉儒就一直昏迷不醒,双目紧闭。在他离开的前两天的一个早上,我从一大早就跪在他床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他的名字,他却浑然不知。直到会8点半,我附在他耳边轻轻地喊到:“玉儒,8点半了,要开会了……”
他竟猛地一动,睁大了双眼,死死地盯着我好一会儿,又慢慢地闭上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睁开……
玉儒走了,留下了他未竟的事业。但我深知,他是不忍的。他永远不能割舍他的事业、百姓和亲人。
玉儒走了,他一身清廉,光明磊落,他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留下了用之不竭的财富——那就是他的精神。
玉儒,我为有你而骄傲,百姓也会因你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