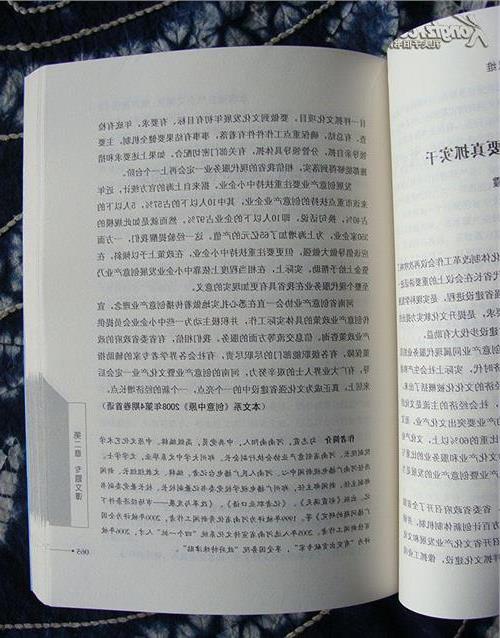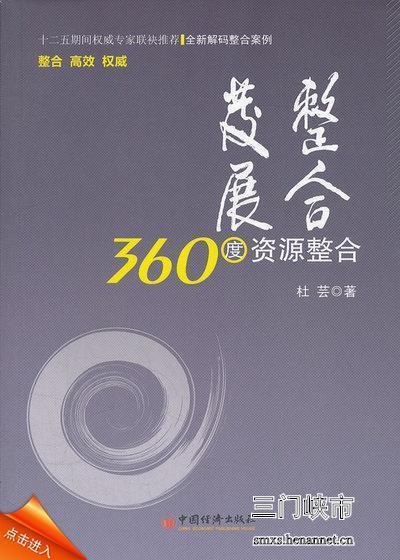说说老大哥王明义
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看!够吓人的!)我们的那股子热情,那股子对文学、对理想的执着和痴迷,真是既甜蜜又感动。那时明义也才三十多岁,是我们这一群中的老大哥。他这个老大哥,才是真正名符其实的老大哥:宽厚、仁德,包容性极强。
我从小顽劣,天性中充满反骨,许多时候不按常理出牌,难免不有造次的地方。每每遇到此种情况,明义的办法是,——他多是笑笑,之后一摊手,他的口头禅是:“这有什么办法?他就是这种性格。”明义厚宽地笑着,极其诚恳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在那个时代,我们讨论文学,有时大半宵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大家叼着香烟(明义不抽烟),抽得乌烟瘴气,一屋子都是烟雾,你我都纷纷抢着讲话。有时说到激动处,难免争论,每到观点不一,骑虎难下之时,明义的办法是:“你这样讲,我就没有办法了。
话给你都说绝了。这样讲就谈不下去了”来收场。他依然是他的风格,笑中还带无奈和羞涩。明义的通达和宽厚,使你没办法和他红脸。回想几十年来的交往,从来没和明义红过脸,一点也没有。
明义不抽烟,但是喝酒。明义还是有一点酒量的。喝一壶正好,两壶也可以,三壶也能喝。但三壶下去明义就有点偏多了,他开始自个笑,开始出汗。明义喝酒好出汗,额头出汗。据说好出汗的人是能喝点酒的。每每出汗,明义就说:“怎么办呢?胖人就是这样,胖子好出汗,胖子怕热。
”明义有点胖墩墩的,他年青的时候就是这样,几十年了,他变化不大,还是这样墩墩实实,和他的性格颇为一致。我出来工作之后,与明义的接触要少了些,但每年总是要见面的。现在明义鬓角多了些白发,其余变化不大。多些白发也可理解,毕竟人过六十了。
明义近些年来搞书画,据说搞得不错。明义的字是不错的,这些我年青的时候就知道,至于画,是后来搞的,就不甚了了了。他的文学创作,我是有发言权的。在天长,在滁州,在安徽省,明义的创作,是产生过影响的。他的短篇小说别具一格,是很扎实的一路,他的《打扑克》一直打到中央电视台,不说小品,就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打扑克》也是中国小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
一个人写一生,能有一篇作品让人记住,一篇作品留在人间,这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了不起的了。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一下。1989年,我想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其实那时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可还是将发表的仅有的作品和个人创作简介填好寄给明义,由明义推荐。然而当年的三月,眼看开学在即,我却没有收到通知,情急之下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就从滁州上火车赴北京。
明义到火车站来接我。要想想,那时从天长上一趟北京多么不容易,我却说走就走了,可以说,这是我真正第一次到北京(有一次到承德从北京路过过)。到鲁院,明义就带着我找负责的老师,边找老师我还边听课(听了有两三节课)。
有一天,又去找老师,找到张玉秋老师,张老师说:“没有床位了,同学你迟了。”明义说:“他来了好几天了,都听了好几节课了。”语言之肯切至今听来都令人感动。
正巧这时,一个姓邹的老师过来,说:“某某不来了,单位不让来。”张老师望着邹老师:“你这消息可靠?”那姓邹的老师说:“肯定没问题,他单位反馈的。”这时我和明义都眼巴巴地望着张老师,都是一副急切的模样。这时张老师没有了办法,说:“那,这个名额就给这个同学吧!”
鲁院的学习,是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我能去进修,得归功于明义的引荐。鲁院几个月的学习,对我是刻骨铭心的。
以上拉拉杂杂的一番话,难成体系,但是真诚和由衷的;只不过是一个作家的重感觉少逻辑之言罢了。我相信,读者是能从这些文字中体会出明义的为人的。看后也会同意我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