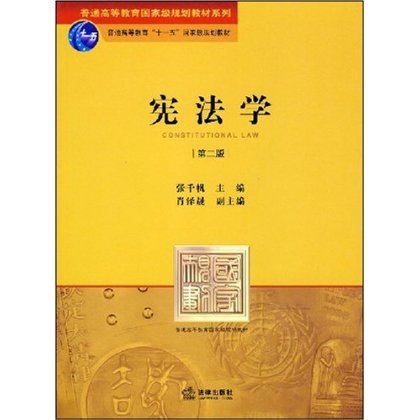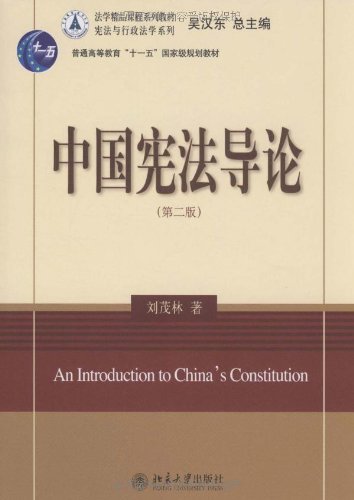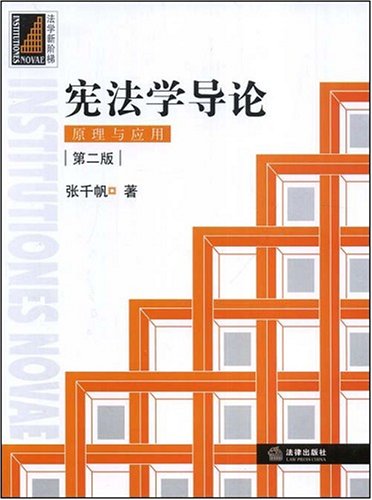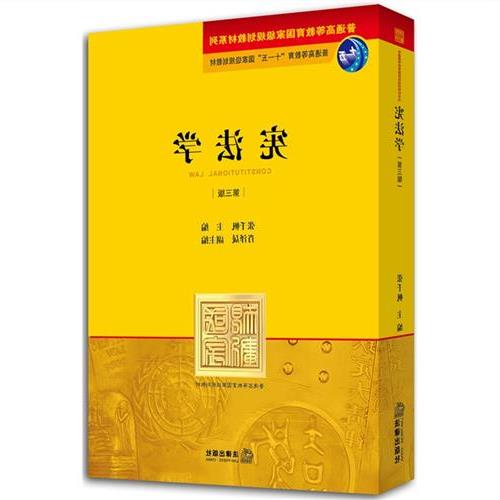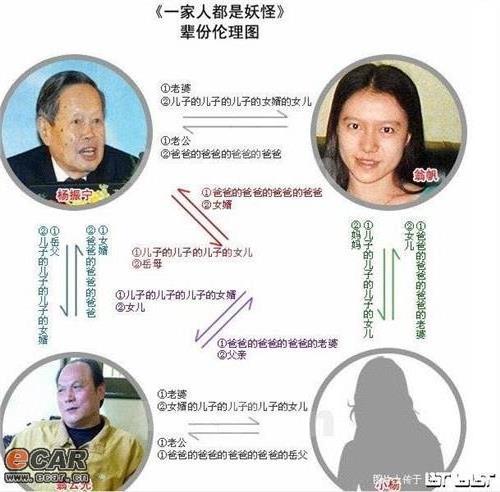张千帆宪法学导论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读后感
公共选择理论把利己性假定扩展到所有人的行为。……利己性是置根于每个人深处的不可磨灭的人性……公共选择理论把它简单作为一个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对宪法学尤其相关的是,政府或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们只是代表着一套由具体的人占据的机构,而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是有私欲和野心的“小人”,因此不能轻易被委以信任;由于纯粹的德治是靠不住的,这些人也必须受制于某种形式的法律约束。
作者承认人并非纯然理性的动物(张千帆,2002),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元假定是一种更为简单实用、同时也是安全、经济的思路。正因为如此,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元假定成为是法治、民主、分权制衡制度的基本理论依据。
在知性方面,人所具备的只是有限理性。在以往的许多宪法学研究当中,教条主义色彩相当浓厚。许多制度、观念、行为方式被奉为“绝对真理”而不得加以怀疑、挑战。对此,张千帆认为有必要敲一下怀疑主义的警钟。因此,人既不能盲从他人,也应当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的易错性。
没有对他人的怀疑,就没有自我的独立;没有对自我的怀疑,就不会有对他人的宽容。历史表明,人类曾经坚信过的许多富有战斗力的信念都被无情的时间最终证明是虚妄。
作者指出宪法学考虑的是关于国家体制的宏大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最艰深的社会科学也难以像物理学对力矩的分析那样给出个确定的答案。因此,认为宪法学能为宪法提供一个绝对正确的“科学”依据.或证明特定制度的先进性与合理性,无疑是自欺欺人;事实上,一旦陷人这种误区,宪法学就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科学,而已经沦为一种教条,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
......宪法学者应该采取开放与开明的态度,欢迎不同观点的自由争论。
实证的研究当然离不开对宪法规则的研究。实证研究除了经验实证研究外,它的另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规范实证研究。问题在于不光要研究纸面上的宪法条款,更要探究宪法判例中的规则。完全脱离宪法规则,那不是宪法学,而是政府科学或政治哲学。
在宪政实践比较发达的国家,“宪法学主要就变成了案例研究。它更注重宪法规则在现实生活中的解释与澄清,而不是分析与评价规则的合理性。”(张千帆,2004:45)当然,这些规则还应当经受更高理性的检验。 此外,作为实证宪法学的倡导者,作者还强调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实证科学的知识或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的灵活运用。早在1897年,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即在著名《法律的道路》一文中断言:“在对于法律的理性研究,懂得法条的人可能掌握着现在,但掌握未来的人则是统计学与经济学大师。”(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2000) 今天,随着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的兴起,应当说霍姆斯的预言已经基本实现。
事实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很多已经应用到宪法学研究当中,有的甚至应用到法庭的审判中(张千帆,2004:40,41)。在张千帆的《导论》中,诸如对宪政文化的功能、“杜瓦杰定律”、“孔多塞原理”、民主和规模的关系、选举成本等问题的论述都反映出其它实证科学的影响。
这明显深化了我们对上述宪政问题的认识水平,从以往的静态的抽象的认识走向一种动态的具体的认识。
也许,上述实证研究方法在发达的宪政国家并不十分新颖,但将这些方法引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却具有开拓和创新的意义。例如,公共利益是法律中常见的、有用的,同时也是经常被滥用的一个术语。由于其极具抽象性,台湾学者陈新民称之为“罗生门”式的概念(陈新民,2001:181)。
作者在《导论》中运用方法论个体主义对“公共利益”进行了具体的解析,将其界定为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之和。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
然后,他根据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主要是自私的,也是自身利益最好的保护者,并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民主政治至少在理论上说必定最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公共利益)(张千帆,2004:9)。
在宪法学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于“激活”中国宪法学乃至中国宪法具有重要意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将促进中国宪法学的研究重心发生迁移,从条文规定到实施机制、从抽象原则到具体问题,推动中国宪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进而为“激活”中国宪法作好学术准备,促进中国宪法的发展。
当然,正如一个孤独的“齐玉苓案件”不可能造就一个传统,一本孤独的《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也不可能完成建构中国实证宪法学的全部使命。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来,从主义到问题的转变正在发生,意识形态成分在宪法学论文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宪法学者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社会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尝试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实证科学的知识或方法。可以说,中国宪法学正在从传统的意识形态走向一种实证科学。”
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张千帆先生在此前的《西方宪政体系》等著作中论述的主要是西方的宪政原则,那么《导论》则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正面阐述了现代宪政的普适性的基本原则:法治与分权,民主,权利与自由,联邦主义。而所有这些原则都统一在人格尊严最高价值之下。
在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导论》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分别阐述了这些基本原则,而在于指出了诸多基本原则相互之间以及这些原则与宪政之间的复杂关联而非孤立存在,并用人格尊严这一最高的宪政价值加以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政是诸多基本原则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 在法治和分权原则上,作者首先分析了法治与宪政之间的联系。法治是宪政的基础,而宪政则必然要求法治。宪政本身是法治的最后与最高阶段,因此法治自然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意”。没有法治作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宪政。如果政府与公民不能认真对待普通的法,那么他们也必然不能认真对待“更高的法”。
分权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没有某种有效的分权模式,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作者认为(张千帆,2004:51):
分权成为宪政与法治国家的一项共同原则——不见得一定要采取美国或法国或任何特定国家的“三权分立”,但至少是某种形式的分权。这是因为和德治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它所强调的不是官员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尽管这是极为重要的,而是人民对官员的控制与官员之间的相互控制。因此,它要求在政府内部建立相对分散与独立的权力中心,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
与法治一样,民主也是一种“他律”,也就是人民在选拔官员过程中对政府的一种直接决定与控制。但法治并不直接限定制定法律的统治主体;法律可以由人民代表制定,也可以由国王或少数规则制定,且没有理由表明后者在法律的实施上就一定不如前者。
法治和民主具有分离的可能性,法治未必是民主的。但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法治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至少是多数人的利益。因此,现代国家普遍接受了民主原则,民主和法治和谐共存(张千帆,2004:
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普遍倾向。没有建构在民主之上的法治,多数人的权利无从得到有效和可靠的保障。宪法不仅保护多数人的利益,
而且也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自1835年托克维尔在其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后(托克维尔,1988:第七、八章),人们时常将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联系在一起,对民主心怀疑虑。甚至在民主尚未成为充分事实的国家,也有人奢谈“多数人的暴政”。其实,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张千帆,2004:53):
尽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权利可能发生冲突(我们将看到许多这类例子),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并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和民主原则相矛盾;事实上,两者更经常是一致的。作为自治的惟一方式,民主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尽管主要是指多数人的自由。
况且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权利并不一定发生冲突,而且即使发生冲突,只要所涉及的权利不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那么民主原则要求少数人的利益可以受到法律限制。因此,作为宪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数主义民主原则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发挥作用。
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也要求分权。由于个人权利在政府权力面前总是显得过分弱小,只有分解政府权力,使得公民能够利用政府分支之间的相互制衡,这样才能维护其宪法或法律权力。
联邦制是纵向的一种分权的一种形式。作者这里所说的“联邦”不是指任何特定的纵向分权模式,而是指一种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分配方式。只要地方政府在宪法上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就都具有联邦制的某些特点。联邦制一般适用于幅员辽阔的大国。这是因为大国出于其地方差异和自治的需要,尤其需要纵向分权。作者认为联邦制有助于促进和保障上述的三种宪法价值——法治、民主与人权(张千帆,2004:54):
首先,联邦制实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权力分配的宪法化,因而有助于实现法治,也是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次,联邦制也有助于民主,因为它加强了地方自治。联邦制充分保障地方政府的立法权,并使之不受中央政府的违宪或违法侵犯,而地方政府和选民的关系最为直接与密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联邦制有助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通过使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制衡,联邦制有助于防止地方民主及其所形成的多数主义势力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在《导论》中,张千帆先生在论述了上述宪法原则之后,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抽象问题:“在这4项宪政规范背后,是不是存在‘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