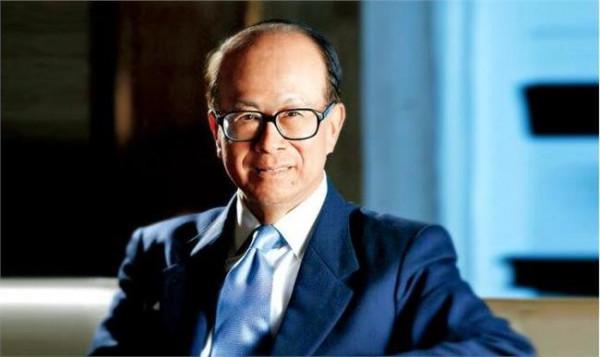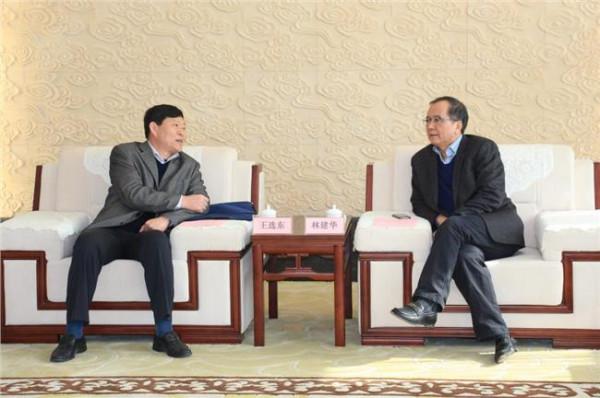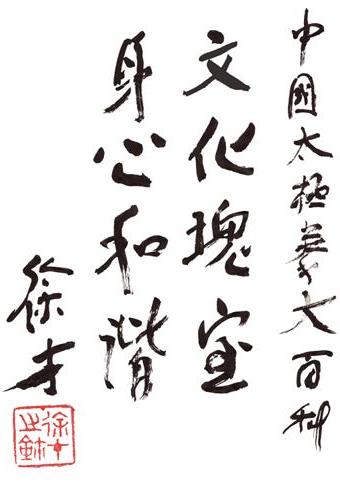李范五李明娜 【李范五】于济川:李范五“牛棚”700天
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被拉下马,经过多次批斗、游街示众、甚至入狱,最后于1975年初夏被投入绥棱农场,度过他一生中最难忘的700个日日夜夜。1977年因患多种疾病,经过几番申请才获准迁居到他爱人黎霞工作的绥化地区,在绥化南门外林业科管辖下的一个苗圃的小干房里定居。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平反。李范五在“牛棚”700天这段史料,很少被人知道,笔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过冲击,同李范五有邂逅之交,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之一,有责任把当时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以供专门从事史料工作的单位和同志参考。
笔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恐不能写尽当时的重重云雾、斑斑血泪,希读者见谅,还须更知内情修补。本文蒙当年经常和李范五在一起劳动生活的霍广兴、范垂忠、郭健、胥永山、张华,还有刘景齐、姜凤岐、李俊卿、刘广惠等同志积极提供情况,在此—并表示谢意;
二、省长下“牛棚”
在绥棱农场场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1975年5月,省委定案组林善庆来场指示:原黑龙江省长李范五转交到场,对李范五的管理原则:一是和群众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二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三是接触革命群众,经常汇报思想学习情况。
四是遵守场内规章制度,政治思想管理从严、生活适当照顾,每月给生活费50元,看病用款到省核销,党内生活没有恢复。” 他身犯何罪?无从知晓,将来如何?虚无缥缈。一省之长就在这样“莫须有”的情况下,就在这样一个山沟沟里,渡过他一生中难忘的700天“牛棚”生活。
“文革”前,绥棱农场是个劳改农场,1967年将全部犯人调出,又调入近千名刑满释放和解教就业人员。1968年开始接受下乡青年,1970年又接受部分强劳分子。
农场成员复杂,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李范五到场后的具体安排,当时的场领导也费了一番思索。宽、优唯恐违犯“原则”,招来洗不清、说不明的麻烦,严、苛又觉得情理不通,大可不必。
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把李范五安排在农场的一个实验站,这个站占地面积小、人员少、闭塞、接触面不广、地理环境好、有山有水、劳动强度不大,各方面条件比较合适,对于李范五的住处,当然不能和四类分子一起住大工棚,给一间房显得太小,两间又怕违犯“原则”,于是决定给一间半,可谓不大不小。
李范五到农场时,除了两名“护送人员”外,陪同他来的有老伴黎霞、女儿李黎立,还有个10岁的外孙女叫“大愚”。李范五自己也没想到堂堂一省之长,竟在一夜之间撤职罢官,在武装看押下,头顶“10大罪状”,在全省所有市县到处七斗八斗,挨过多少棍棒拳脚,受了多少诽谤凌辱,最后被送进小兴安岭脚下的这个“牛棚”。
三、林业部长栽树
李范五进农场那年已63岁,患多种慢性病,更严重的是多次拳打脚踢、弯腰低头,什么“燕子式”、“飞机式”等肉体摧残,肢体倍受损伤,已不适于从事任何一种体力劳动。完全不叫他劳动又不行,可能是考虑到他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实验站分配他到这个站的林业组劳动。
林业组的任务是培育各种树苗,在附近田际道旁造林栽树,组长是范垂忠。老范听说叫他管省长,心里忐忑不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是1956年从4野38军转业的军人,长期的部队生活,养成了他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那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在他思想上有较深烙印。
现在突然叫他这个21级干部去管理支配一位六级大官,这种乾坤倒置,上下移位的奇特现象,使老范茫然不知所措。
可是李范五对这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到农场后只休息一天就出工了。他直挺挺地站在范垂忠面前,听侯分配劳动任务,并且表示对栽树既有兴趣,也有粗浅研究。那天在场区道旁栽樟子松,李范五载的树比任何人的质量都好,他一边栽一边滔滔不绝地讲发展林业的宏观意义,还讲了一些林业基础知识和育苗移植技术操作方法。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这是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发展我们林业资源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否实现就要具体到一颗颗地栽好、栽活、管好、管成。
李范五的这番话给实验站林业组的同志们在树立事业心上起到很大作用。 范垂忠看到李范五在栽树时双脚跪着操作,还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腰眼,他的面部肌肉每隔几秒钟就抽搐一下。
在劳动休息时老范问他什么时候患这种病,李范五只是笑笑不答,后来日子长了他才说出这是被殴打的后遗症。老范告诉他:“早晨可以晚出来一会儿,中午多休息一会儿,什么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可以不出工。”可李范五从来不耽误工,除住院治疗和严重犯病外,都坚持出工劳动。
除正常劳动外,他还利用节假、星期日或业余时间上山采集橡树籽,在实验站水库边沿种橡树。他还用绳子,量弓测量了实验站周围的地形,绘出一张林带分布图,并对农场发展林业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
为了把绥棱农场的林业搞好,他结识了当时主管全场林业的郭健同志。李范五多次到场部找郭健谈全场防护林带的分布规划,并提出许多远见的建议。在林业的总体发展上李范五强调以红松为主,他说:“黑龙江省以伊春的五营为采种区,大力发展红松,因为红松干直、材质好、出材率高、经济效益大、用途广。
对于农田防护林主张采用橡树,橡树可以就地取种、寿命长,树冠大,防风和绿化效果好,橡子又是很好的猪饲料,树木长期不腐,冬天可做牛羊饲料。
”郭健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干部,他从李范五那里学到很多林业知识。事后郭健对人说:“以前我认为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一定都有专业知识,和老省长接触后我算服了,不但知识渊博,看起来可称得上是专家。
”直到现在,郭健主持的农场林业科还珍存着李范五亲自绘制的农场防护林带规划图。 李范五曾因病到场部住院,在治疗期间,他还在病房周围栽了许多鱼鳞松小苗,现在有21棵已有碗口粗了。
他在实验站亲自栽的树现已成材成荫,当人们走在场区的马路上,或站在水库边观赏风景时,很自然地回忆起这些高大成行的绿树,是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一省之长亲手栽的,这也是绥棱农场的一份自豪和一篇有趣的史话。
四、走资派和右派
李范五在农场时,先是在实验站职工食堂买饭吃,后来自己做饭,当时霍广兴是职工食堂的管理员,对于李范五主副食的供应,全得通过老霍。霍广兴原系哈市公安干校的教师,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到绥棱农场当管理员。
一个是走资派,一个原来是右派,政治上一色黑。如果在生活上对李范五特殊照顾,很自然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同情,或曰:“反革命共鸣。”如果老霍借着对李范五的苛待以表现自己与“走资派”划清界限,向革命靠拢,也许可以捞到点可怜的政治资本,两者必居其一,老霍选择了前者。
李范五在职工食堂买饭吃,每月无论如何也达不到50元的标准,那时食堂的主食只有馒头1种,而副食:白菜、萝卜、土豆3大样循环上桌,鱼、肉每月也许有一两次,也许没有,烙一顿油饼算是改善伙食。
李范五身体非常虚弱,又患多种慢性病,急需在生活上调养,霍广兴就想法额外卖给他一些肉、鱼、豆油叫他自己做点菜吃。这种对走资派的特殊照顾,也招来一些人的非议甚至责难,本文不打算叙述那些不愉快的事,恕不费笔。
李范五是个严于律己的人,他意识到老霍有压力,告诉他:“以后有啥吃啥,不要因为我给你找了麻烦”。老霍只是摇头,背地里对黎霞说:“每天晚上8点后您到食堂拿东西,无论如何也得保住老省长的身体。
”炸好的鱼、鹿肉、鸡蛋、瘦猪肉等由公开供应转入“地下”。李范五爱吃野味,老霍到老乡家去买野鸡野兔,自己家的咸菜、大酱也给他拿。李范五到农场后由于水土不服,经常有地方病症反映,头晕、呕吐、高烧。
老霍把自己家的“维C”、樟脑注射剂拿去,还到农场附近的公社卫生院买了牛黄安宫丸送去。 李范五从来也没有对老霍表露过将来报恩的意思,黎霞铁骨铮铮更没有许愿、乞求的习惯,而霍广兴从来也没有寄希望于李范五。
“走资派”能救右派吗?这只是一种建立在革命这个广义的思想情感上产生的同情心理,一种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反映。 李范五的头发长了,实验站没有理发员,要么就得走十五华里到场部去理,要么就得找人。
霍广兴拿来理发工具说:“我来试试,反正理不好”。李范五苦笑着说:“来吧!现在我的头好剃多啦!”这一语双关的玩笑话,包含着多少信任和感情。黎霞也接着说:“请你给我也剪一剪,只要不剪成鬼头就行。
”3个人都笑了,这笑声中有多少酸、辣、苦、咸!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由于形势恶化,李范五的生活状况也恶化了。在食堂买饭改为在家自己做饭。农场不比城市,一切生活供应当时还保持着统购统销、定量供应的原则,李范五想吃一点有营养的食品就难了。
虽然霍广兴还偷着给一点,但迫于形势,只能是一星半点。这一时期是李范五生活最困难、思想最沉闷、精神最衰退的时期。经常犯病,起初,到场部医院看病还能要来小车接送,后来只能搭运粮的大汽车,没有运粮车就坐手扶拖拉机,实在不行就坐马车、牛车,也曾徒步到场部。
实验站有个好心的小卫生员叫窦宽勤,对李范五特别照顾,可惜笔者没有打听到小窦的下落,如果小窦能看到这篇史料,请原谅我没有把你对革命老前辈的深切关怀书诸竹帛,但你在那种非常时期,敢于不避疑忌,挺身而出,精心护理李范五的事实是尽人皆知的。
当时小窦只是个所谓的“赤脚医生”,对于复杂的病症,不能也不敢投药和施行针灸等治疗。
吉人天相,这时好心的胥永山医生夫妻俩介入了李范五的生活。 胥永山、张华两位医生,1964年毕业于牡丹江卫生学校,夫妻双双分配在绥棱农场。李范五在农场时,他俩在第四生产队医务所工作,距离实验站有两华里,李范五夫妻经常找胥、张两医生看病,渐渐成了要好的朋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文将在后边叙述。
五、闭门追悼会
1976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难忘的年代,也是血与泪交织的岁月。1月8日,一股强电波载着摧心裂肺的哀乐,给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撇下一场沉痛的灾难,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了!砥柱突陷、泰山骤颓!我们的民族承受着忍不住、咽不下的痛苦。
李范五在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当收音机里播出那难以叫人置信的消息后,他一下子瘫倒在田间,各种潜在的病症同时袭击上来,血压突增,心律过速,神经各部失去控制,他躺倒了!这个64岁的老人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吗?黎霞也泣不成声,此时此刻的沉痛是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劝慰不了谁的,只能相对掉泪,心情一样沉重。
当天晚上霍广兴去看望李范五,夫妻俩正默默地挂起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周总理像片,闭起门来开追悼会呢!
老霍悄悄地肃立在他俩背后,连10岁的外孙女大愚也低声呜咽,沉痛的气氛充满这20平方米的小屋。 “安息吧!总理:活着的还得继续革命!”这是李范五在周总理像前说出的一句近乎誓言的悼词。 那些天,李范五吃不下、睡不着,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被这意想不到的噩耗击碎了。
六、大胆的秧歌队
1976年底,虽然已经响了10月的春雷,但10年浩动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那种极不正常的与人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糊涂的人仍然沉浸在噩梦中,人为的鸿沟仍然阻碍着同志间的情感交流和思想交融,冤的、假的、错的还没有得到纠正。
虽然如此,但人的手脚似乎脱离了桎梏,他们敢于表露自己的爱憎和感情了。 那年春节,附近公社的生产队都组织了秧歌队,庆祝冲出黎明前黑暗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双岔河公社双泉大队距离农场实验站大约有10华里,大年初五,这个大队的一支秧歌队一行百余人,乘坐两辆拖车、4辆马车,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地开进实验站!
憨厚朴实的农民完全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说得很明白:是专程给老省长拜年的,领队的是大队支部书记郭俊。
此时,此刻,此种局面,此种举动是否合适?谁说得清楚?10年浩劫的风未停、雨未住,造反派还在基层掌权,李范五的一切全没恢复,他还是一个被监督的“罪人”。实验站有人想把这支秧歌队劝阻回去,可能吗?要知道农民并没有那么多瞻前顾后的考虑,他们刚刚从8分钱一个劳动日中解放出来,虽然还没有象现在这样财大气粗,但已经有些扬眉吐气了。
谁也没有胆量去说服这支大胆的秧歌队。锣鼓、唢呐响成一片,折扇、花束上下翻飞,径直奔向李范五那一间半小屋。
李、黎老夫妻俩听说有一支上百人的秧歌队专程来给他们拜年,这突如其来的激动使老夫妻俩手脚无措,没有工夫思考该不该接待,也用不着考虑应不应承受。李范五和黎霞穿戴整齐地迎出来了。
大队支部书记郭俊用他那大嗓门高喊:“老省长,我们给您拜年来了!”一嗓子喊出李范五夫妻一串滚热的眼泪!群众的这种纯真无瑕、朴朴实实的潜在感情,一扫李范五夫妻心灵深处的愁云,在一片鼓乐和欢笑声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党的形象的存在。
黎霞把仅有的几合好烟拿出来招待秧歌队。秧歌队里有50开外的老头,也有焕发着青春美的青年男女,还有10几岁的小孩,这老少不同的笑脸象无数朵报春花一样,预告着一场暴风雨后,新的曙光就要升起。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七、敢冒风险的人
一个革命者,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大约有这样的体会:在平坦的大道上前进容易,在进军号的鼓舞下冲锋容易,在千军万马的行列中挺身而出也容易,在坎坷的小道上独行难,在全无鼓励的寂静中孤身作战难,在漫漫长夜中顶着霹雳闪电、茫茫雨雾去寻找朝阳更难。
笔者在撰写这篇史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几位敢冒风险的人。他们在史无前例的环境中,在随时都可能毁掉自己的危机中,泰然自若,漠然处之,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在李范五、黎霞最艰苦、最危难的时刻,默默地、偃旗息鼓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指导他们思想的不是恻隐之心,更不是攀龙附凤,而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党性。他们是几个很普通的人,但他们的革命精神与对革命老前辈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是可贵的。
刘景春:当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现在的县政协主席。 徐宏志:政府办公室主任,布置给县总务科“给李范五一家提供一切方便,要保障他们的安全,照顾食宿、就医、安排车辆,接送要有专人陪同……” 姜凤岐:当时的总务科长,现在的县物价局长。
于俊卿:当时的县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刘广惠:当时的县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现在的文化局长。 就是这几个人,在李范五的700天“牛棚”生活中,冒着当“保皇派”的危险,为李范五和其家属,在生活上给提供了很多方便。
一次黎霞从“牛棚”回绥化,半道上昏了过去,姜凤岐立刻拦住了县革委的车,及时把她送县医院。于俊卿、刘广惠,明里暗里给李范五传递过多少信件、电报和邮包,他们也记不清了。
八、啥时候也不能忘记了党
笔者最难忘的是1976年7月1日。那段时间我在实验站替班放鹿。7月1日那天我和一个姓王的工人把鹿赶到实验站水库附近的草滩上,这时李范五从大堤上走过来,以前他们已经很熟,经常见面,也聊过天,但从来没涉及过政治问题。
今天他很高兴,拿着塑料袋,里边装着一下子采集来的橡子。他走过来和我们一同坐在草地上。 “您去采树种啦?”我问。 “采点饱满的,种在林带上,这种树,树冠大、叶茂盛,防风效果好。” “您这么大岁数了精神真好。
” “这几年不行了。今天你们吃什么饭?”他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吃什么饭,普通饭呗。 我说:“有家的老婆做啥吃啥,没家的食堂卖啥吃啥。” “今天是什么日子?难道忘了?”他笑着问。 日子对我们来说,一年365天都一样,吃饭、干活、睡觉、挨斗,四大内容周而复始,从来不管什么初一、十五、星期、节假。
“这会儿还记什么日子。”那个姓王的工人说。“啊呀!真糊涂,今天是党的生日——‘七一’!” 他笑眯眯地盘腿坐在草地上,下意识地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大腿,眼睛看着远方的蓝天,自言自语地说:“党是1921年成立的,到现在55年了。
人过50教训该不少了吧……”他突然不往下说了。 多好的话题,说实在的,我早就希望和他聊一聊政治方面的问题,很多理论问题我实在理解不了,很想请教这一省的决策人。
可是4次接触只是谈栽树、谈作物套种、谈农田基本建设。有时青年们围着他要求说说“文化大革命”的事,他总是想法把话题岔开,给他们大讲“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
今天他提到党的生日,提到经验教训,我立即把话题往政治上迂回。 “老省长:您过去很胖,现在怎么瘦成这样?” “你怎么知道我过去胖?” “报纸上看见的。好象是您接待苏加诺总统。
” “有钱难买老来瘦嘛,瘦点血压就不高。” 说完,他就站起来,从衣袋里掏出4个咸鸭蛋,塞给我们每人两个。 “党的生日是好日子,改善改善,记住,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党啊!” 他大步往堤上走去。怎么好意思吃他的东西呢,我追上去想把咸鸭蛋还给他。他头也没回,只向后摆了一下手说了声:“吃吧!”便大步流星地走了。
九、迁“棚”绥化
1976年下半年到1977年春天,是李范五最艰苦的岁月。健康情况恶化,经常犯病,除严重的肺气肿外,面部神经麻痹、关节风湿症,痛起来满头是汗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胥永山、张华两位大夫,经常找他们注射、针灸。
胥永山个性沉静、寡言少语,对李范五存在一种由于敬重而产生的畏缩心里,针灸时怕李范五承受不了疼痛,不敢下针,手发抖。李范五看出他的心理活动,就给他讲医生对病症应该象对敌人一样,必须稳、准、狠三结合。张华医生性格开朗,好说好笑,李范五就给她讲中国妇女为什么缠足的故事,以减轻她扎针时的紧张心理。
两位医生见李范五身体虚弱,缺乏抗病能力,劝他想法多吃点青菜,多锻炼。初春,农场根本没有什么青菜,黎霞就到野外挖刚出土的“曲麻菜”,为了李范五能吃上鸡蛋,黎霞还养了10几只母鸡。
范垂忠家养鸽子,老范爱人关鸿珍要送给黎霞几只,鸽子肉是富有营养的,但李范五怕给老范找了麻烦,坚持不能要。1977年春,李范五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肺气肿使他喘不上气来,腰脊损伤使他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巨大的疼痛。
不能站着劳动他就坐着搓麦穗、选良种,麦芒刺进肉里象针扎一样。他消瘦多了,想吃的东西没有,不想吃的难下咽。真是祸不单行,哈市有位同志托农场的汽车给李范五捎来一小箱急需的食品,偏偏没有收到,老霍、老范都帮助找,始终没有找到。
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在10年浩劫中人心变异的现象。 在这期间,李范五曾多次给省打报告,写中请,要求到哈市养病,却没批准,李范五沉痛地说:“也许我要长眠在这小兴安岭脚下!
”黎霞见李范五病到这种地步,就积极设法营救,最后以投奔爱人养病为理由,获准到绥化居住,1977年6月初,李范五迁到绥化,先住在绥化县电业科的一个招待所里,后来迁到绥化南门外属林业科的苗圃居住。
李范五在农场期间,给广大干部职工留下深刻的影响。首先是他的事业心,在那种特殊环境中,还为一个小小农场的发展、测量、规划绘制蓝图,这一切都是他在精疲力竭的业余时间,忍受着病痛干的,直到现在人们谈论起来还赞不绝口。
再就是他那刚毅的政治抵抗力,两年多他在农场接触了不少人,没有一个人听到他对党对革命有什么怨言。他严于律己,生怕自己的灾难株连别人,给其他同志找来麻烦,他带病坚持劳动,拒绝别人的馈赠,多次到绥棱县,不进办公室,只在传达室或站在门前等候办事。
他虽身陷囹圄,但看不出半点颓唐表情,他说的、想的、做的都是向着未来,连农场的家属都这样说:“人家老省长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对那些患得患失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身教。 笔者在1987年4月就着手撰写这篇史料,5月写完初稿,5月8日专程到哈尔滨人民警察学校找霍广兴核对有关情节。听老霍说,李范五和黎霞曾于1985年夏季回省小住,口述了很多抗联史料,到镜泊湖游览几日后回京健康情况良好。
没想到5月11日就听到范五同志在京逝世的不幸消息,悲痛之余产生力量,一夜之间完成修改任务。这篇不成文的东西是在绥棱县政协和绥棱农场党委的支持下写成的,只是限于笔者才疏学浅,不能把先辈的革命情操和当时的情况和盘再现纸上。谨以此文作为我献在范五同志灵前的一纸祭帖。
【转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绥化农垦志》(1946-1985)第690-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