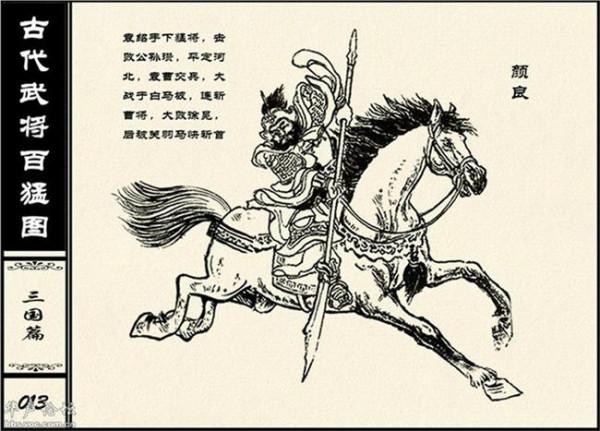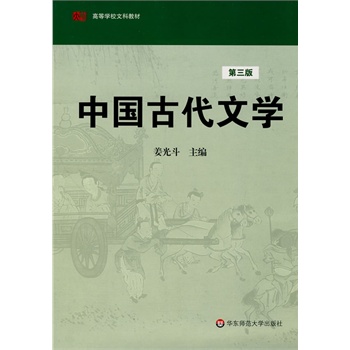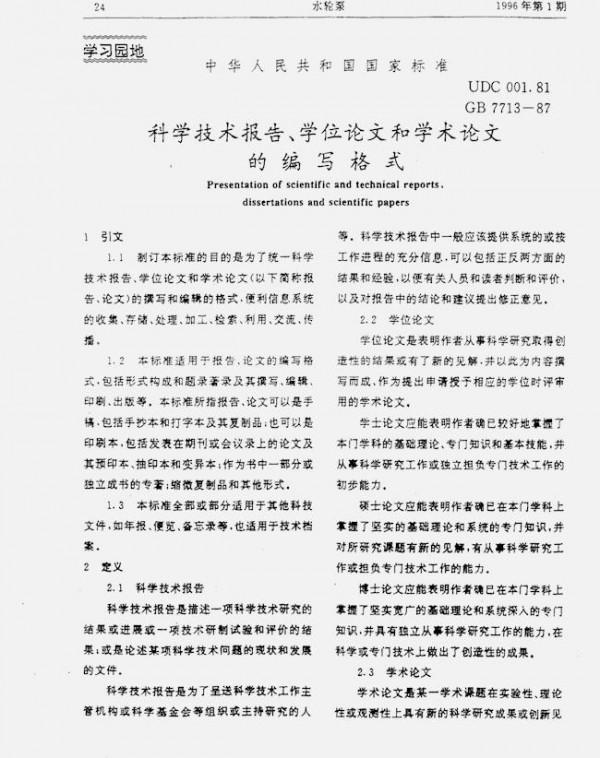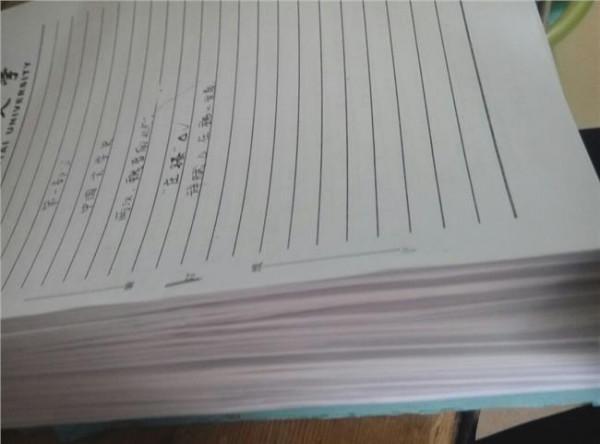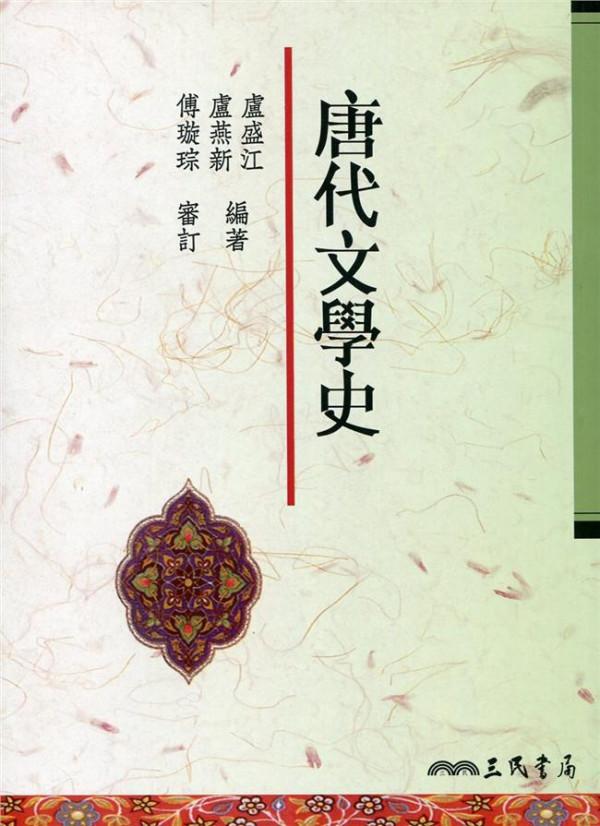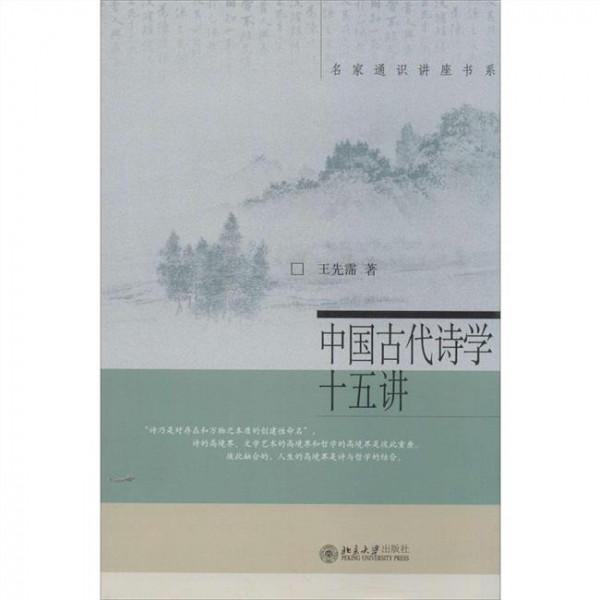郑志强签名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郑 志 强
摘要: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
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
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
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有“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统治了一千余年。
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以笔者的见解,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现具论如下。 一、《诗经》学史上对《诗经》中“六诗”的误释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上有这样一段著名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而“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① 这是古典文献中最早将上古诗体分为六类的记载。
因为有此记载,战国以后的诗歌研究者就开始在经典诗歌选集《诗经》中进行“诗体”的研究和分类,试图找出二者的对应关系。其中,以《毛诗故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最为引人注目。
然而,自《毛传·诗序》出现后,对《诗经》中“六诗”的解读逐渐开始误入歧途。因为《诗序》不仅明确认为《周礼》中的“六诗”即在《诗经》之中,而且首次将“六诗”改为“六义”,它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在这里,虽然风、赋、比、兴、雅、颂与《周礼》中“六诗”的顺序一致,但“六诗”变成了“六义”;同时,对“风”、“雅”、“颂”作出了相当详细的解释和发挥,而对“赋”、“比”、“兴”却未作深入细致的理论阐释。
这客观上开了将《诗经》中的诗歌类型与《周礼》的记载相矛盾的先河。《毛传》还在《诗经》中的160篇诗歌首章次句之下,首次标上“兴也”的字样(也有少数标示在首句或第三、四句之下者);至于另外145首,哪些是“风也”,哪些是“赋也”,哪些是“雅也”,哪些是“比也”,哪些又是“颂也”,却一首也没有标示。
从此,对《诗经》中的诗歌应如何分类,以及对《周礼》中“六诗”应作何解,在阐释上开始产生混乱。
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撰成《毛诗传笺》、《毛诗谱》,对《毛传》中包括“六义”在内的许多《诗经》学中的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阐发,《毛传》由此大兴于世。
然而,由于郑玄在“笺”、“谱”《毛传》中采取了“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②的态度,遭到了三国今文经学大师王肃的全面批驳和否定,由此,关于“六诗”、“六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愈加南辕北辙。
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中试图对《毛传》中只标“兴也”而未标“风也”、“赋也”、“比也”、“雅也”、“颂也”这一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解释,他说:“《诗》文宏奥,包蕴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③言外之意,“赋”可以包括在“风”里,而“比”与“兴”的区别也不大,所以毛公在《诗传》中只阐述“风”、“雅”、“颂”和“兴”亦未尝不可。
而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则又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④如果说,先秦时代的“六诗”先由汉儒变为“六义”,而后在“诂训”中只留下了“风”、“雅”、“颂”、“兴”四种;那么,到了六朝刘勰和钟嵘这里,“六义”蜕变成了“三义”。
至此,就连对风、雅、颂、赋、比、兴的定义和概念的理解,也莫衷一是了。
隋朝出现了刘焯、刘炫两位《诗经》学大师,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隋书·儒林传》对二人评价甚高。然而,在初唐经学家眼里,二刘“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
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⑤。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下,以初唐“凌烟阁二十八学士”之一的孔颖达为首主持编纂的《毛诗正义》问世了。
由于《毛诗正义》被列入唐太宗诏书所颁《五经正义》之一,并被列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化教材,从而成为大唐政府颁布的一部官书。因此该书在唐代影响之大,到了“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的地步。
而《毛诗正义》中关于“'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并得为'六义’”⑥的论断,从此定为一尊。尽管南宋出现了另一位《诗经》学改革大师朱熹,对《诗经》中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见解,但对《诗经》中的“六诗”问题,却一本孔颖达之说而引申之。
在《诗集传》中,朱熹明确提出:“'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
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⑦然而,无论孔颖达也罢,朱熹也罢,对《周礼》中“六诗”如此平行而又错综排列的根本意义,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述。
尽管如此,孔、朱二人把“风”、“雅”、“颂”视为《诗经》中的不同诗体分类,把“赋”、“比”、“兴”视为作诗的艺术手法的见解,却从此成为主流观点。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就明确赞同“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清代另一位《诗经》学家方玉润对《诗经》中“六诗”的解释,仍认为“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⑧;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也认为:“'风’、'雅’、'颂’以性质言,……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是为《诗》之三纬”⑨。
直到当代,这种雷同的观点一致占统治地位。 但是,一种观点长期成为主流见解,并不意味着某一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不同的见解存在。
以现代为例,朱自清先生就不认同“三经三纬”说,他明确提出:“'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
”⑩当代《诗经》学著名学者萧华荣先生也认为:“《春官》明言'六诗’,同篇又有'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的记载,则'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皆为诗体。
”因此,他又一次发出了这样一个《诗经》学史上的千年疑问:“至于'赋’、'比’、'兴’三诗何所指,为什么不见于今本《诗经》,甚至在其他先秦典籍中也毫无踪迹?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笔者不敢臆断,只得存而不论。
” 学术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主流观点很流行,而另一方面疑问又顽强地存在。这说明什么?这很可能说明主流观点有逻辑断环,确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进一步讲,这种主流观点也许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应解决的实质性问题。
以今天的眼光看,把“六诗”解为“三经三纬”,把“风”、“雅”、“颂”视为三种不同的诗歌体裁,而把“赋”、“比”、“兴”视为三种修辞方式的传统主流观点,当然是一种“误释”。
原因有三:第一,《周礼》与现存《诗经》必有内在联系,后者当是前者的制度性成果的一部分,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妥的。第二,如果第一点成立,那么“大师”所教的风、赋、比、兴、雅、颂,当与“大司乐”所教的兴、道、讽、诵、言、语有概念上的区别:作为诗、歌、曲、舞四位一体的“乐歌”,兴、道、讽、诵、言、语才是适合歌曲的旋律特点和舞蹈节拍需要的六种语言艺术表现方式;而与此相区别,风、赋、比、兴、雅、颂就只能是六种不同体裁的诗歌类型。
这六种体裁的诗创作出来后,要合乐、合舞、能演唱,还必须分别进行兴、道、讽、诵、言、语六种艺术形式的处理,方能变成“乐语”,以适合演唱。第三,就修辞方式而言,现存《诗经》文本中当然不仅仅只有赋、比、兴三种,还有其他许多种修辞方式;如果将《诗经》中的主要修辞方式仅仅归纳为“赋”、“比”、“兴”三种,那既不符合《诗经》文本的实际,又大大降低了《诗经》这座经典宝库的文学艺术价值。
站在修辞学的高度来看,传统主流观点并不能完整归纳《诗经》中所包含的全部或主要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也只能是一种误释。 《诗经》学史上出现对“六诗”的误解并不奇怪。因为从《诗经》传播史的角度看,它并不是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地传播下来的。
其实际情况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及高皇帝诛项籍……平定四海,亦未遐遑庠序之事也。……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至孝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悦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赵绾、王臧的老师鲁申公,是当时“最为正宗”的《诗》学大师,因两位高足弟子被杀,“申公亦疾免以归”,“终身居家教,复谢绝宾客……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
”自此以后,虽有“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但“其语颇与齐鲁间殊”。这些史料明确告诉我们,自秦始皇下“焚书坑儒”令(前213年)到河间献王上《毛诗》、以小毛公为博士(前135年),《诗经》的传播由于秦和汉初两朝官方的严厉打击以及其间多年战乱兵燹的干扰,前后中断了约80年。
这在以口耳和竹帛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古代,对于一部经典的准确传承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由此,自《毛传》出现后,在一些《诗经》学上的重大问题上出现误解和误释乃至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诗经》学总要前进。对任何重要的传统经典,每一代人总应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新阐释。
对《诗经》学中关于“六诗”这一重大问题的阐释也不例外:只有摆脱旧说的窠臼,换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式,才有可能找出解决这一“千年疑问”的新途径。为此,我们有必要找出“六诗”误释的历史根源及造成这种理论认识误区的“症结”所在。
二、“六诗”概念误释的历史根源 及理论误区的“症结”剖析如上所述,现存文献中首次对“六诗”一词作出解释者,为《毛传》中的《诗序》。
《诗序》的作者解释“六诗”一词为“诗有六义”。那么,“义”在此又作何解?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中对“义”字列举了225条古代例释,其中与文艺有关者主要有以下几条:(1)《礼记·礼运》:“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
”(2)《礼记·表记》:“义者,天下之制也。”(3)《国语·周语下》:“义者,文之制也。”(4)《吕氏春秋·贵公》:“遵王之义”高诱注:“义,法也。
”综合上述四条解释,将“六义”解为诗文的“六种体裁”当不为错。因此,假如说将“六诗”解为“诗有六义”不为错的话,那么“六义”的确切的解释就应为“六种诗体”。对于这种观点,汉代及汉代以后的一些重要史学家和文论家也是明确认同的。
如班固就认同“赋者,古诗之流也”;萧统也说:“《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
”我们可以明确看出,萧统亦把“诗”有“六义”理解为“诗”有六种体裁。 那么,对“六诗”的歧解出现在何时呢?笔者认为,亦当以《毛诗序》为肇端。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主流观点认为,《毛诗序》始创作于卜子夏,最后润色定稿于卫宏。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依笔者之见,现存《毛诗序》当不是卜子夏始创的全文,只能是留下的“断简残篇”;而卫宏在“定稿”时,已经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因为我们以今天的逻辑常识来分析现存《毛诗序》,就能发现它在内容结构上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亦即缺乏对许多内容进行阐释的必要环节,文句的间断性、跳跃性很明显,作为一篇文学史上的“名篇”,却根本算不上是一篇内容层次环环相扣、分析阐发井井有条的严谨论文,倒像是几组“论点摘要”的简单拼凑。
比如:既然开篇提出了正确的观点“诗有六义焉”,那么接下来的解释当不限于“风”、“雅”、“颂”,亦当有“赋”、“比”、“兴”,但文中似乎是丢了对这部分内容的阐述(当有断简);再如,既提出了“四始”这一概念,亦当解释何为“四始”及其意义如何,当不会让读者自己从司马迁《孔子世家》中去找“四始”的解释(当有断简);如此等等。
这篇“定稿”如果真出于卫宏之手,那么这种现象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汉代及其以前,“经学家”们自有其“家法”,那就是重师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师留下来什么,学生就传述什么,不敢任意发挥。
假如卜子夏留下的正是不完整的“断简残篇”,那么卫宏辈最多也只能做一些订正文字、拼合简文次序的编订工作,这当然也并不奇怪。但后来的盲从者却并未将《毛诗序》作为“断简残篇”来读,而是作为完整的“经典”来读,对其中的疑窦,亦开始“下以己意”进行自我发挥。
在钟嵘《诗品》里,“诗有六义”开始变为“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其他三“义”莫名其妙地被抛弃了。同时,我们通读《诗品》全文可以发现,钟嵘已明确地将“义”视为诗歌中的修辞手法;这一认识又被同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加以认同和强化。
由此,经过刘焯、刘炫的“照本宣科”,初唐孔颖达在编纂《毛诗正义》中对“六义”“定于一尊”式的“述而不作”,也就属于“有所本”而非独创观点了。
然而有意思的是,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留下了一篇十分珍贵的论文。这篇论文详细地解释了他将“六诗”、“六义”解释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的原因和根据。
因此,认真分析研究这篇论文,有助于我们找出对“六诗”产生误解的根源所在: 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
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逸见风、雅、颂有分段,以为比、赋、兴亦有分段,谓有全篇为比,全篇为兴,欲郑指摘言之。
郑以比、赋、兴者直是文辞之异,非篇卷之别,故远言从本来不别之意。言“吴札观诗已不歌”,明其先无别体,不可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明其先无别体,不可分也。元来合而不分,今日“难复摘别”也。
言“篇中义多兴”者,以毛传于诸篇之中每言兴也。以兴在篇中,明比、赋亦在篇中,故以兴显比、赋也。若然,比、赋、兴元来不分,则唯有风、雅、颂三诗而已。《艺论》云“至周分为六诗”者,据《周礼》“六诗”之文而言之耳,非谓篇卷也。
或以为郑云孔子已合于风、雅、颂中,则孔子以前,未合之时,比、赋、兴别为篇卷。若然,则离其章句,析其文辞,乐不可歌,文不可诵。且风、雅、颂以比、赋、兴为体,若比、赋、兴别为篇卷,则无风、雅、颂矣。
这篇论文虽短,但有论点,有论据,亦有论辩与论证。论点即是:(1)“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亦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2)六者虽大小不同,但能“并为六义”,前三者与后三者的关系是“用彼三事,成此三事”,并非六者各自成为一种诗体及各自“别有篇卷”。
这里面已明确包含了风、雅、颂是三种诗歌体裁,而赋、比、兴是这三种诗歌体裁均可使用的艺术表现方法的观点,也包含了《诗经》内并没有“赋、比、兴”三种体裁的诗歌的观点。
接着孔颖达引用了一段史料作为论据。孔氏引用这段史料首先要告诉人们,他和参与编纂《毛诗正义》的几位专家所提出的上述论点,并非得自他们的独创,而只是继承了大师郑玄已有的定论而已。
从文中所引《郑志》这段史料看,在汉代,已有“六诗”究竟是六种独立的诗体,还是其中有的是“诗体”、有的是“艺术表现手法”的疑问。张逸显然是把“六诗”理解为六种不同的诗体的,但他又难以在《诗经》中分辨出赋、比、兴三种体裁的诗歌,因此他问老师:“何诗近于比、赋、兴?”出乎我们今人意料的是,老师一下子竟被问住了。
可以推想,听了学生的疑问,郑玄当时肯定沉默了片刻。
这个沉默的话语意思也很明白:这个问题你现在问我,我一时也给你讲不清,因为我也没弄明白。当然,虽然在沉默中,老师似乎听到了学生的进一步发问:作为老师,您为什么会弄不明白呢?所以老师必须申述自己的理由,因此他便说:“(因为)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
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不回答则已,一回答倒让我看到了这位郑大师对这一重要问题“极端糊涂”之态,可谓活灵活现。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虽然我讲不清楚,但也难怪我,你们不是熟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吗?那里面明明记载着吴公子季札“请观于周乐”,而“工”只为他歌了“风”、“小雅”、“大雅”和“颂”,并没有记载“工”也为他歌了“赋”、“比”、“兴”。
由此可见,并没有“赋”、“比”、“兴”这三种体裁的诗。至此我们不禁恍然大悟:原来郑玄把《诗经》中的乐调分类“风”、“雅”、“颂”与“六诗”中的诗体分类“风”、“雅”、“颂”混淆为一了!
然而郑玄也许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回答苍白无力,因为“吴札观诗已不歌”并不一定说明就没有这三种体裁的诗歌,况且《左传》上明言“观”的是“乐”而不是“诗”。因此接下来的申述既带搪塞意味,也近乎主观臆断:即使有“赋”、“比”、“兴”三体诗,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如今也难以重新将它们分离出来独立分类,况且《毛诗》早已分析过,明确讲《诗》篇中“义多兴”。
在这里,郑玄已不是在传授历史,而是在讲自己的猜想,因为任何现存史料都没有记载孔子把“六诗”其中的“三诗”合于另外“三诗”之中。
倒是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写得明明白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从司马迁这段记载中我们可知:第一,“去其重”和“取”、“采”等工作,是因其三千余篇中内容庞杂且有许多不可施于礼义,况且这种“重”既有来自“大师”一系之诗(原诗之词),又有来自“乐师”一系之乐语(改编后的乐歌歌词),因此必须彼此参详、考订、编删,以适于进行“诗教”;第二,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云云,说明孔子在《诗》的“正乐”上下了很大功夫,他要把原诗和原用乐调重新准确地配合起来;第三,所谓“四始”包括《诗》中各篇的排列次序,当是由孔子按一定的目的编订的。
但是,孔子决不可能把“赋”、“比”、“兴”“三诗”合于“风”、“雅”、“颂”的各首诗之内;要是那样,孔子就要把整个《诗经》中的原诗进行重组和再创作,而这样显然大大违背了孔子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
所以,孔颖达等想补上郑玄这个“失语”的漏洞。因此,论文在下面论辩和论证一部分说:郑大师讲,吴札观诗已不歌、证明本来没有“赋”、“比”、“兴”三体诗,这是对的,因为“不歌”当然说明它们“不可歌”;至于郑大师说,孔子录诗将它们合于风、雅、颂中,这并非说孔子将“赋”、“比”、“兴”三体诗重新组合到“风”、“雅”、“颂”三体诗中的各首诗里的意思,而是说它们原本就在“风”、“雅”、“颂”三体诗中的各首诗里,人们无法将其从中摘出来变成单独的诗篇加以区别。
况且郑大师已明言,这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到见解,早在《毛诗》中,就也没有标出哪些是“赋也”、“比也”,可见有其依据。
至于有人讲,郑大师既然说孔子将“赋”、“比”、“兴”合于“风”、“雅”、“颂”中,那说明在孔子未“合”之前,“赋”、“比”、“兴”三体诗是存在的——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
如果真是那样,不是还得把它们从每首诗的一章一句中摘出来吗?这样子一摘出来,现存“风”、“雅”、“颂”中的每首诗,还能够以乐歌的形式来演唱吗?不是支离玻碎了吗?若把每个“赋”、“比”、“兴”的句子从每首“风”、“雅”、“颂”的诗中摘出来另组诗篇,那“风”、“雅”、“颂”岂不是不存在了吗? 可见,孔颖达等是完全赞同郑玄等的观点的:可能是孔子把“赋”、“比”、“兴”合于“风”、“雅”、“颂”中了;即使孔子并未把前三者“合于”后三者中,那一定是它们原本就合在后三者中了。
因此,不能把前三者从后三者“摘别”出来;如果“摘别”出来,那就“乐不可歌、文不可诵”,“风”、“雅”、“颂”就不存在了。
所以,决不能承认“赋”、“比”、“兴”是三种不同体裁的诗体。 这么一分析对比,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一目了然了:孔颖达继承了郑玄的错误,把《诗经》文本中以乐调类型划分的《风》、《雅》、《颂》与《周礼·大师》中作为“诗体”的“风”、“雅”、“颂”的不同概念混淆为一了,由此造成“赋”、“比”、“兴”三种诗体被人为地加以“消灭”了。
现在要说明的是,孔子在编订《诗经》并为其“正乐”时,并不是以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身份来进行工作的,而是以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身份来做这项工作的。
所谓“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那是因为它们能“论功颂德”、“畅怀抒情”,能够“兴、观、群、怨”,“止僻防邪”,“足以塞违从正”,是看到了“《诗》之为用,其利大矣”。换言之,孔子是站在政治教化的实用功能的角度来编《诗》的,而没有下多少“为艺术而艺术”的功夫。
因此,我们看不到太多他从诗歌艺术本身来深入阐述“六诗”的言论,那是毫不足怪的;与此相类,毛亨、毛苌、卫宏、郑玄、刘焯、刘炫、孔颖达等人对《诗经》的注解,均带有“政治家办学术”性质。
因此,他们均搞不清《诗经》中的《风》、《雅》、《颂》与《周礼·大师》中所言“风”、“雅”、“颂”的区别,亦是不足为怪的。然而,他们却误导了后来身为正宗文艺理论家的钟嵘、刘勰等人。
现存《周礼》和《诗经》明确告诉我们:尽管《诗经》是《周礼》所载“礼乐”的“制度性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重要的政治教化的实用价值;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有着高超的、成系统的艺术规则、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的,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
只要跳出古人理解的误区,亦不难对其中的艺术之“谜”进行切中肯綮的剖析。
我们完全能够单独从古典诗歌艺术的角度,对《周礼》“六诗”的概念进行更加确切的阐释,并将现存《诗经》的诗歌作出大体合乎实际的体裁分类。 三、《周礼》“六诗”概念的当代阐释 及《诗经》现存“六诗”分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提出:第一,《周礼·大师》中的“六诗”概念指的是六种不同的诗歌体裁,即风体、赋体、比体、兴体、雅体、颂体。
第二,“赋”、“比”、“兴”三体诗之所以“不见于今本《诗经》”,完全是由于对经典概念的误解造成的;而事实上,在现存《诗经》文本中,是“六诗”俱全的。
如何看待现存《诗经》中的《风》、《雅》、《颂》分类?正确的解释应是:这是一个按“乐调类型”归类划分的本子。所谓《邦风》、《国风》,最早大都属于周王朝的《房中之乐》,这类“乐”是周天子在政事之余用于“房中”娱乐的,因此,集中了各邦各国的地方调子。
因为此类乐调演奏的场合不像朝堂、政事堂上那么严肃,相对比较自由,因此可以推而广之“用于乡人焉”、“用于邦国焉”,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类“乐调”的内容和形式不健康,只不过相对比较生动、活泼罢了。
因此,所谓“十五国风”就有不下于15种不同的声调类型,所以当时孔子“正乐”时只言“雅正各得其所”而不言“风”如何如何,大概各邦之“风”仍存而未乱。
所谓《雅》(包括《小雅》、《大雅》),亦即这部诗入“乐”时,大概是用“雅乐”系统的乐调配出来演唱的;所谓《大雅》、《小雅》即“大夏”、“小夏”,当有依据。
周人以“夏乐”为“正”,所谓《王夏》、《肆夏》、《纳夏》、《昭夏》以及《韶箾》、《南》、《籥》、《武》、《象》等等,说明周初确实保存了夏商以来的“正乐”系统,而《雅》中的这些诗篇,又是用这类乐舞配出来的;《颂》则均是“宗庙落成”后举行各类型庆典的“祭歌”,另有其独特的舞乐系统和特点。
因此,现存《诗经》中的《风》、《雅》、《颂》与《诗经》中作为诗歌体裁的“风”、“雅”、“颂”有艺术视角上的本质区别,混淆了二者,对《诗经》艺术成就是不能作出正确评判的。
那么,作为乐调的《风》、《雅》、《颂》与作为“诗体”的“风”、“雅”、“颂”之有根本区别,除了“外证”,有没有内证?我们认为是有的。洪湛侯先生作过一个有意义的统计,指出“《国风》中有相同篇名作品五组十二篇”,“《小雅》有相同篇名一组两篇”,“《国风》与《小雅》有相同篇名四组九篇”,“《大雅》与《小雅》有相同篇名二组四篇”,以上“四类同篇名诗共十二组二十七篇”。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第一,在这四类十二组二十七篇诗作中,同名作品较多属同类“诗体”;第二,虽然“标题”和“诗体”同类,但配上不同的内容和声调,它们就可以分属于不同的《国风》和《雅》;第三,这说明在周朝时,曲子和曲名即是与诗歌和诗名、诗体相分离的,只是当诗被选中用于演奏时,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艺术处理后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如果需要舞,还要另配。
这当然与《周礼》的记载相一致,与现存《诗经》一点也不矛盾。
那么,有了六种不同的“诗体”,就真的没有了作为艺术修辞手法的“风”、“赋”、“比”、“兴”、“雅”、“颂”了吗?当然是有的。
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将它们绝对对立起来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类似于人体与其体细胞干细胞之间的关系。如此讲来,在一种体裁的诗(如“比体”诗)中,它当然也可以使用另一种修辞手法(如“兴”这种修辞手法),甚至一首诗(如“赋体”诗)中也可以用多种(如“风”、“兴”、“比”等)修辞手法。
但是,一般来说,一种诗体正是主要由相应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构建起来的,同类艺术手法正是同体诗的灵魂,对表达该诗的主旨具有“密钥”作用和主导作用;判断一首诗它究竟属于哪一种体裁,就要从整体来审视和衡量,看其整体上主要使用了哪种修辞手法。
《毛诗》、《毛诗正义》、《诗集传》的作者,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把“体裁”与“修辞手法”对立、割裂开来,缺乏从整体上的认识和把握,忽视了二者的辩证关系,结果就出现了许多错误。
由此,我们可以对《周礼》乃至《诗经》中的“六诗”概念作出如下新阐释: 风体诗是一种以“讽刺”为主旨和主要特点的诗体,其中“讽”作“劝导”解,“刺”作“批评”解;赋体诗是一种以“叙述”为主旨和主要特点的诗体,所谓“赋陈其事而直言之”,因此这类诗多数较长,因为有“叙”、有“述”,《诗经》中这类诗不少;比体诗是一种以“比喻”为主旨和主要特点的诗体,其中有比、有喻,又有明比与暗喻等的区别,这类诗在《诗经》中多数较短;兴体诗是一种以抒发愉快或怨愤情绪为主旨和主要特色的诗体;雅体诗是一种以“赞美”为主旨和特色的诗体,有“赞”有“美”,但多不赞美已死者;颂体诗是一种以歌颂“先祖”为主旨和主要特色的诗体,多是宗庙里的“祭歌”,一般并不歌颂活着的人。
根据上述新定义,我们可用“风”、“赋”、“比”、“兴”、“雅”、“颂”六种不同诗体,对现存《诗经》中的全部诗歌作出新的体裁分类。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笔者对《诗经》研究甚为肤浅,尚不能保证对每一篇诗歌的归类都十分准确,但“学无止境”,现粗举大纲,以收“抛砖引玉”之效:风体诗83首。其中《召南》5首:《甘棠》、《殷其雷》、《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邶风》7首:《日月》、《凯风》、《雄雉》、《式微》、《旄丘》、《北风》、《新台》;《鄘风》7首:《柏舟》、《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蝃蝀》、《相鼠》、《载驰》;《卫风》1首:《芄兰》;《王风》4首:《扬之水》、《中谷有蓷》、《大车》、《丘中有麻》;《郑风》8首:《将仲子》、《大叔于田》、《清人》、《遵大路》、《褰裳》、《丰》、《子衿》、《扬之水》;《齐风》4首:《鸡鸣》、《东方未明》、《南山》、《载驱》;《魏风》3首:《葛屦》、《十亩之间》、《伐檀》;《唐风》7首:《蟋蟀》、《山有枢》、《杕杜》、《羔裘》、《鸨羽》、《有杕之杜》、《采苓》;《秦风》2首:《车邻》、《黄鸟》;《陈风》2首:《墓门》、《株林》;《曹风》1首:《候人》;《小雅》22首:《常棣》、《伐木》、《沔水》、《祈父》、《节南山》、《正月》、《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风》、《大东》、《北山》、《无将大车》、《小明》、《頍弁》、《角弓》、《菀柳》、《白华》;《大雅》8首:《文王》、《民劳》、《板》、《抑》、《桑柔》、《云汉》、《瞻卬》、《召旻》;《颂》2首:《臣工》、《敬之》。
赋体诗43首。其中《周南》1首:《葛覃》;《召南》2首:《采蘩》、《采蘋》;《邶风》1首:《谷风》;《鄘风》1首:《定之方中》;《卫风》2首:《硕人》、《氓》;《郑风》2首:《女曰鸡鸣》、《溱洧》;《齐风》2首:《还》、《著》;《魏风》1首:《陟岵》;《秦风》2首:《驷驖》、《渭阳》;《陈风》2首:《东门之枌》、《东门之杨》;《豳风》2首:《七月》、《东山》;《小雅》12首:《六月》、《采芑》、《车攻》、《吉日》、《斯干》、《无羊》、《十月之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宾之初筵》;《大雅》12首:《大明》、《绵》、《皇矣》、《灵台》、《生民》、《行苇》、《公刘》、《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颂》1首:《閟宫》。
比体诗55首。
其中《周南》8首:《关睢》、《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麟之趾》;《召南》3首:《鹊巢》、《行露》、《小星》;《邶风》2首:《终风》、《匏有苦叶》;《卫风》3首:《淇奥》、《河广》、《木瓜》;《王风》3首:《兔爰》、《采葛》、《葛藟》;《郑风》5首:《风雨》、《出其东门》、《山有扶苏》、《萚兮》、《东门之墠》;《齐风》3首:《东方之曰》、《甫田》、《敝笱》;《魏风》2首:《汾沮洳》、《硕鼠》;《唐风》2首:《无衣》、《椒聊》;《秦风》3首:《蒹葭》、《无衣》、《权舆》;《陈风》3首:《衡门》、《东门之池》、《泽陂》;《桧风》2首:《羔裘》、《隰有苌楚》;《曹风》1首:《蜉蝣》;《豳风》4首:《鸱鸮》、《伐柯》、《九罭》、《狼跋》;《小雅》10首:《鱼丽》、《南有嘉鱼》、《湛露》、《鸿雁》、《鹤鸣》、《青蝇》、《采绿》、《绵蛮》、《渐渐之石》、《何草不黄》;《大雅》1首:《荡》。
兴体诗39首。其中《周南》2首:《卷耳》、《汝坟》;《召南》1首:《草虫》;《邶风》8首:《柏舟》、《绿衣》、《燕燕》、《击鼓》、《泉水》、《北门》、《静女》、《二子乘舟》;《鄘风》1首:《桑中》;《卫风》4首:《考槃》、《竹竿》、《伯兮》、《有狐》;《王风》3首:《黍离》、《君子于役》、《君子阳阳》;《郑风》1首:《狡童》;《魏风》1首:《园有桃》;《唐风》1首:《葛生》;《秦风》2首:《小戎》、《晨风》;《陈风》3首:《宛丘》、《防有鹊巢》、《月出》;《桧风》2首:《素冠》、《匪风》;《小雅》10首:《四牡》、《采薇》、《杕杜》、《黄鸟》、《我行其野》、《蓼莪》、《四月》、《鼓钟》、《都人士》、《苕之华》。
雅体诗46首。其中《召南》3首:《羔羊》、《何彼襛矣》、《驺虞》;《邶风》1首:《简兮》;《鄘风》1首:《干旄》;《郑风》5首:《缁衣》、《叔于田》、《羔裘》、《有女同车》、《野有蔓草》;《齐风》2首:《卢令》、《猗嗟》;《唐风》2首:《扬之水》、《绸缪》;《秦风》1首:《终南》;《曹风》2首:《鸤鸠》、《下泉》;《豳风》1首:《破斧》;《小雅》20首:《鹿鸣》、《皇皇者华》、《天保》、《出车》、《南山有台》、《蓼萧》、《彤弓》、《菁菁者莪》、《庭燎》、《白驹》、《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车辖》、《鱼藻》、《采菽》、《黍苗》、《隰桑》、《瓠叶》;《大雅》7首:《棫朴》、《旱麓》、《既醉》、《凫鷖》、《假乐》、《泂酌》、《卷阿》;《颂》1首:《泮水》。
颂体诗39首。其中包括现存《诗经·颂》中除《臣工》、《敬之》、《泮水》、《閟宫》之外的全部36首诗,另外现存《大雅》中的《思齐》、《下武》、《文王有声》3首亦应属于颂体诗。
①《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第64页。②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第一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③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页。④(梁)钟嵘著、郭令原注译:《白话诗品》,岳麓书社,1997年,第9页。⑤⑥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2—13、12—13、3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三),岳麓书社,1997年,第1858—1859页。⑧(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66—67页。
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篇。⑩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页。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页。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第870、871、872、419页。
(汉)班固:《西都赋·序》,张启成、徐达等译注:《文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页。(梁)萧统:《文选序》,张启成、徐达等译注:《文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洪湛侯:《诗经学史》(下册),中华书局,2002年,第724—726页。 作者简介:郑志强,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