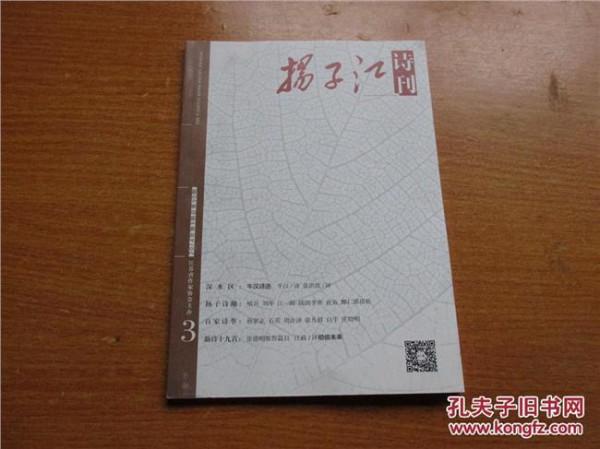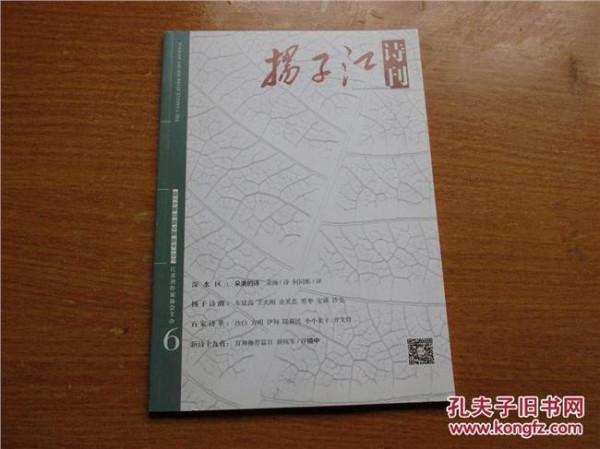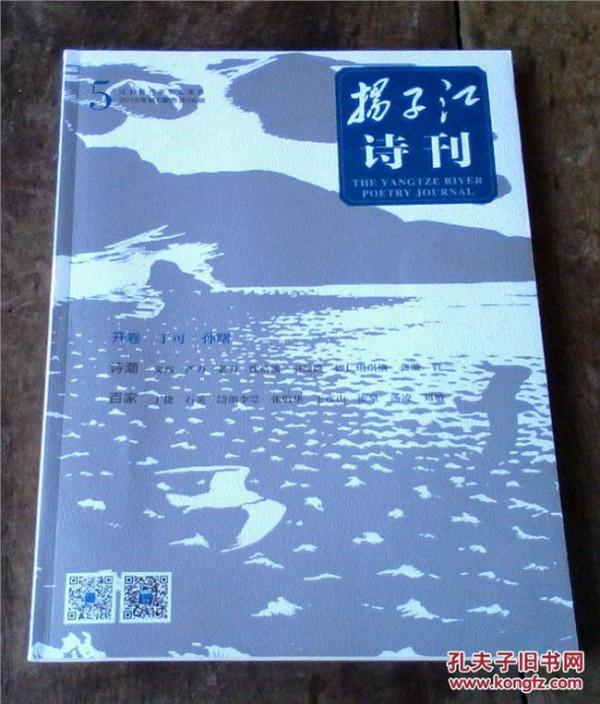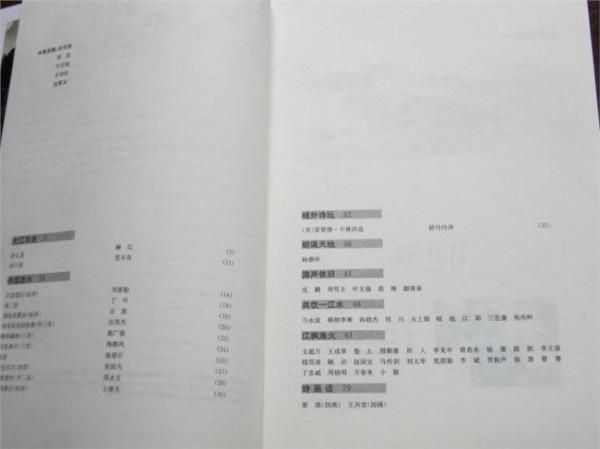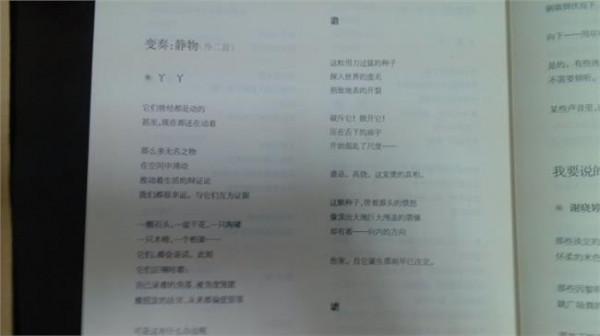雷平阳的妻子 《扬子江》诗刊关于雷平阳《春风祷》的讨论
《扬子江》诗刊关于雷平阳《春风祷》的讨论
"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 ——关于雷平阳《春风祷》的讨论
主持人:汪 政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 评论家
讨论人:何 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评论家 傅元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评论家 张宗刚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评论家 何同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讲师 评论家 育 邦 《青春》杂志执行主编 诗人 评论家 梁雪波 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 诗人 评论家 韩松刚 《扬子江评论》杂志编辑 评论家
■ 汪 政:各位,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雷平阳的作品《春风祷》。在我看来,这是当下诗坛不多见的作品,可以谈论的话题很多,长诗、叙事、地方性,可能还涉及到宗教性的内容与文体,哪位先说?
■ 何同彬:新世纪开始以来出现的"长诗热"至今没有任何衰减的征兆,反而进一步蔓延、扩张,这一现象不仅具有丰富而复杂的诗学意味,也承载着当代诗人充沛又衰微的历史想象方式。雷平阳的《春风祷》(在《云南记》中为《春风咒》)只不过是那些被遗忘的、数量惊人的鸿篇巨制的长诗中的一部,现在或未来我们会长久地回味《水绘仙侣》(柏桦)、《大秦帝国》(小海)、《凤凰》(欧阳江河)和《哭庙》(杨键)吗?欧阳江河说,我故意写长诗,对抗碎片化的生活。
但生活的碎片化本质上和诗歌的长度没有任何关系,一首二百行的长诗比一首二十行的短诗更能避免被"撕碎"吗?爱伦·坡认为长诗是不存在的,他把那些写长诗的人命名为"史诗狂",反观我们最近出现的这些长诗,有哪一部不被盛赞为"史诗"呢?但这样的史诗是博尔赫斯认为可以引发"重大事情"的、再度把叙述故事和吟诗诵词合而为一的史诗吗?我个人是一个反对写长诗的人,因为我从任何一部当下的长诗那里都能轻易地发现拼凑和过度铺张的痕迹,发现他们那些必须要经由哲学、宗教、政治等话语进行神秘解读的宏大意愿。
雷平阳的《春风祷》和他的诸如《祭父贴》、《木头记》、《昭鲁大河记》等系列长诗也不例外,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被迫把它想象为拥有主题相似性的一组诗,以维持阅读必需的专注力和持续性。
■ 何 平:这个问题确实可以讨论。《春风祷》是自由的组诗,还是结构谨严的"组诗"或者"长诗"?在当下的诗歌批评中,对诗意的挖发,甚至过度阐释很多,却往往轻忽"诗结构",这自然助长诗歌成为一种无难度的写作,或者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实用"文体。
而事实上,诗歌是需要有结构意识的。如果缺少一种内在的结构张力,是很难用"组诗"或"长诗"来命名多首集成的成组的诗或者有一定长度的诗。那么,《春风祷》在地理空间位移,一个个小叙事的切换以及精神漫游者(或者是梦游者)的"祷"中间怎样完成"诗结构"就值得我们去细细思考。
■ 育 邦:我相信,对于雷平阳而言,《春风祷》的创作并非一蹴而就,心智必然经历一场残酷的砥砺,一场只有作者自己能够品尝的弱小风暴。组织庞杂的材料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相对而言,我侧重于认为通过它们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心灵则要困难得多。
因而我也可以想见诗人在写作《春风祷》时所遭遇的困境。在如此长的篇幅中,诗人的落脚点在哪里?他首先要避开描绘一个虚无世界的暗礁,他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坚实世界缔造者的角色。诗人不紧不慢,用他的心智与能力呈现一个坚定实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实与虚幻、历史与现实、陈述与想象、现实真相与超现实跳跃,它们交织在一起,肮脏而雄奇。
这个世界可视,可感,可嗅,可歌,可泣。如果说,仅仅为了把这些东西杂糅起来,同样也没有意义,就像史蒂文斯所言的那样:"它(诗歌)纯粹的修辞方面是无价值的。作为一种矫情它是平庸无常的。"
■ 张宗刚:文以气为主。跟长篇小说、长篇散文一样,长篇诗歌首先讲究的,也是一种"气"。《春风祷》,作为拥有如此篇幅的长诗,读来诗风沉稳,语感自然,笔力沉实,气脉贯通,充满绝望的狂欢、压抑的舒展和低沉的高昂,诸多的隐喻,生成内在的张力。
雷平阳的诗歌境界,已然达到了一定段位,遣词造句熟稔如流,有时几欲熟极而溜。《春风祷》色调虽偏于黯淡阴郁,而怪力乱神,山川草木,交织成多维狂欢的奇异景致,自有一种浑沌的整体感。
■ 韩松刚:这首诗给人的第一感受除了"长"以外就是它的云南标记吧?雷平阳的诗歌仿佛背了一个结实的"云南"的壳。雷平阳曾说:"我一直身体向内收缩,像个患了自闭症的诗人,默默地生活在故乡;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
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而正是这种"向内收缩"和"缩身",促使他内在的情怀得以在云南的故土上与那里的亲人、风物水乳交融般浸润在一起,也由此具有了别样的哀愁和气质。
这种气质不是小打小闹的情绪和牢骚,不是固执的思念和情不自禁的哀伤,而是有一种大的胸怀和气魄沉潜在诗歌的内里,在理性的烛照下氤氲着云南独特的普洱茶香,从而掩盖了以往以乡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脆弱的孤独和单薄的伤感。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所有这些云南元素在《春风祷》中都能觅得踪影。
■ 育 邦:敏锐理解世界的能力使得诗人自己成为适应实现世界与诗歌之间隐秘关系的访客。在隐秘的精神层面和忧伤的气息统摄下,雷平阳复活了哀牢山、梨花坞、奠边府、佤山、雪山、基诺山、杰卓老寨、乌蒙山、湄公河,复活了它们被历史、文化与现实缠绕至深的沉重身体和日益衰老的生命。
诗人目睹这一切,深切地体认这个孤独而又即将失落的世界,勇敢地认领了那个只属于诗人方能担当的命运——像巫师一般予以迷幻般地呈现。
在这宏大的诗篇中,我们能够时时看到诗人面目模糊的背影,他的孤愤与旷达,他的冷静与忧郁。一方面,诗人移情于山川河流、大地花朵、流水往事、传统故乡;另一方面,在完成这种移情之后,诗人不可避免地深陷这些天空大地与人世间的事情之中,幽居在它们的深处。
■ 何 平:雷平阳已经被我们想象成一个"文学的云南"的建造者,这一组诗也容易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联想,因为诗中不断出现的云南"地"名。但是,我们要警惕这样的想象可能有意无意窄化诗人更深刻和辽阔的东西,哪怕诗人自己也愿意接受我们的塑造和规训。
这一组诗另一个容易让我们想象的就是雷平阳可能是一个纸上"旧"云南的复辟者,特别是诗歌一开始就出现的几句:"金沙江东岸的一座旧城/被拆了,几千年建成的故乡/说没就没了/那些被连根拔出的/寺庙、牌坊和祖屋,它们想重生/我们就为它们超度吧"。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旧城的消逝和重生,在这组诗的一开始是和"哀牢山的荒草想还魂"以及"梨花坞的桃花,是群异乡人/它们想穿红棉袄,想提红灯笼/发誓要抢在梨花的前面/轰轰烈烈地开"并置在一起的。
《春风祷》中的消逝和重生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他的写作,包括这组诗,我倒是认同他在《云南记》自序中所说的:"近几年,我常常寄身于滇南山中,生活里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比如父亲西游。
这就使得我在此期间写下的诗作,总是绕不开山水、密林、寺庙、虫鸣、父亲、墓地、疼痛和敬畏等等一些‘关键词’。它们像笔尖上活着的灵魂,自然而然,就来到了纸上,温暖或者冰冷。
它们是多了,还是少了?我没有进行测度,也没用刻意地进行文本意义上的增删,就算是一种常态和生态吧,像安顿自己的亲朋,我淡定而又真诚地,为它们准备了一个个方格子,让其住下来。
虽说一切都在纸上,却也希望纸上有片旷野。"因此,应该在"旷野"之上重新识别雷平阳在当代诗歌中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作为全球化时代空间想象中的"地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桃源梦的复现者。换句话说,"地方"的非对抗性有时候可能能够更自由地释放"地方"的文学能量。
■ 何同彬:欧阳江河认为可以用"全球化和地方性"描述的诗歌都是二、三流的诗歌,这一观点似乎有点偏执了,比如我们可以在研究福克纳或马尔克斯的时候避免地方性或地域性话语吗?像雷平阳这种执着于"小地方人的视角和言说习惯"的"没有远方的写作",或者说是精微的地方性写作,实际上在当前日益严峻的由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同一性进程中拥有极其特殊、极其重要的价值。
从《春风祷》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展开于一箭之地"的山谷、老寨、寺庙、少女、僧兵、母亲、采玉人等,在雷平阳"精神幻觉似的文字"之中,建构起一个自足而独立、充满疼痛和愉悦及虚无和想象的小角度的"云南气象",深刻地呈现了云南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和诗学景观。
而且雷平阳的这种地方性书写与全球化激化出的那些地域主义的普遍性诉求不同,他追求精确、细微和神秘的差异性,为了伸张文化差异的合法性他不惜陷入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我吟哦。
就像他引起争议的诗歌《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春风祷》只不过用另外一种看似"敌对"的方式彰显着同样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祈求:"——做一个山中的土司/有一箭之地,可以制订山规,可以/狂热信仰太阳和山水,信仰父亲和母亲……"
■ 梁雪波:实际上,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和国家的概念,"中国"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为了构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倘若过分强调文化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往往会遮蔽或抹杀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这首诗里,哀牢山、湄公河、基诺山、崇圣寺等具有历史感的地理符号连缀起一个关于云南的"边地神话",那里既有瓦蓝的天空、激荡的河流、丰饶的山岭、葱茏的草木,也有代表着异族文化神秘色彩的土司、寨主、歌谣和寺庙。
而在以往,关于边地文化的特异性描述总是以风景、习俗、服饰、歌舞、方言等碎片形式从整体中剥离出来,并被轻易地编织进民族国家的叙事经纬中。
《春风祷》显然避开了这一点,没有简单化地处理成怀旧和乡愁,而是在厚描中小心地嵌入了历史的阴影,比如,用"白骨"和"戒指"的意象来对战争苦难进行寓言化书写,对"农夫不种地/田边地角,听广播,读报纸/喊口号,赛诗词,坐地日行八万里"这一荒诞历史场景的再现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在把玩风物之外的现实关怀,即试图以一种重构故乡的方式,打捞失去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