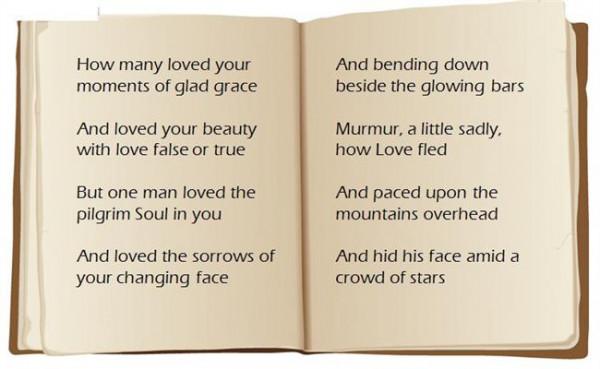叶文玲的成就 爱与信心成就的奇迹 记母亲叶文玲
2008年12月1日的凌晨,我走进浙江医院2号楼的ICU重症监护室里,生我养我的母亲,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胸口尚有微弱的起伏,如果不是定睛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旁边的心电监护仪上起伏的图形,显示出生命继续的迹象。她的头上裹着纱布的头罩,曾经的秀发已经完全剃去,露出青白色的头皮,厚厚的纱布裹在她头颅的左侧,那刚刚开过刀的地方。
我倚在病床边的墙角,带着并未完全褪去的困倦,静静地看着昏睡中的母亲,记得心中那时没有哀伤,只有一种想要把自己的呼唤传递给母亲的强烈意念:“醒过来吧,妈!”
母亲完全清醒,已是一个星期之后,在夏威夷的二姐匆匆赶回来的时候了。
那时候有很多人来探望她,只要不是睡着了,母亲总愿意和所有的人见面,说上一阵。所有的访客,都很自觉地避免打扰她的休息,交谈尽可能地简短,所以大多数时候,总是母亲感到意犹未尽。她不爱谈及自己的病情,却不忘问起那些她记挂的文朋艺友,文艺界又有什么新鲜事……
我的母亲,叶文玲,就是这样一个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喜欢谈话的人。
在嗣后长达4个多月的康复期,出于治疗的需要,她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之间,而每次,到了一家新的医院,她总是能和医生、护士很快熟悉起来。尽管由于脑部创伤后遗症的关系,她很少能利索地说出医生或护士的全名,但是每次看到自己熟悉的医生或护士走进病房,她脸上浮现出的那带着惊喜的微笑,便足以说明一切。
漫长的康复期后,母亲执意要回家,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这时,她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不再能读书写作的事实。这时的她说话往往会辞不达意,并有半侧视力受损,除此之外,她表现得与常人无异,因此,她想要回家,不想再继续被当做病人看待。
她希望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一直都是。我的母亲。
在她从医院回家之初,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些日子她还是积极地配合医嘱,每日翻检着小学生的识字卡片,在老爸的辅助下,困难地试图把每个字念出来。而每次我看到这一幕,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酸:一个终生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一个把写作视为生命唯一目的和意义的人,所能遭受的最糟糕的厄运,莫过如此。
母亲的语言功能区遭受损害,主要的表现就是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想写的字写不出来。并非她脑子里不存在那些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是将这个意思通过口说或者笔写进行表达和传递的通道,已经被切断了。就好像是一座山谷,本来有公路桥(语言)和铁路桥(文字)与外界相连,出了事故之后,两座桥的桥面已经完全断裂、崩塌、消失,再也无法输出语言文字的洪流,只有几根桥索还联在山谷两端,大量的语言文字挤在桥的一端,却只有少数能够挤过来,通过桥到达现实世界的这一端,而大部分却不得不坠入桥下的深渊……
这是我能想出的关于母亲病况的最贴近的比喻。
其实还是有偏差的,因为母亲对于语言的理解力是无碍的,但是对文字的理解力近乎荡然无存,简单地说,她能听,但不能读。
她出院一个多月后,我以为就是这样了,却没想到有一天,她把我找去,很费劲却又无比坚决地宣布,她要出书了!
她想把自己自上次8卷本文集出版以后(那是1998年)写的所有文字,结集出版,将自己的文字工作,做一个近乎完美的总结。
我本能的反应是拒绝这个决定,因为我知道,对于母亲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即使是出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她也会付出大量精力去核实、校对写过的稿子,有时候往往还会重写其中的部分段落。出版一套多达8卷本的文集,对处于这种身体状况的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艰辛,可想而知。
但我又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从小我就知道,凡是母亲下定决心做的事情,她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完成,而最终往往也一定会得到她想要的结果。即使真的由于不可抗力而无法达到目的,那她也丝毫不会气馁——因为没有时间去灰心丧气怨天尤人——她只会精神抖擞地继续新的工作。
母亲是个直性子、急性子、倔性子,她认定了的事,就要马上办,还要干得快干得好,要有效率,也要有效果:写常书鸿的时候,她三去敦煌、飞赴法国探访常老旧日踪迹、去北京、山东走访常老相熟好友……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到红十字会当义工,以最快速度赶写文章、写诗并到募捐集会现场朗诵……老友谢晋去世,她含泪忍痛,一夜赶写了两篇纪念文字……她一向不辞辛劳,更是争分夺秒:诸如“慢慢来”、“悠着点儿”这一类的词汇,从来不会出现在她的字典里。
她真的就是这样,一向如此。我的母亲。
所以当这新一套《叶文玲文集》(9-16卷)出版的时候,很多人会惊讶,很多人会疑惑:“叶文玲不是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吗?怎么还能出书?竟然还是八卷本300多万字的文集?!……”但是了解她的人,一点也不会奇怪。
我和老爸也丝毫不会奇怪。不仅仅是我们最早知道她的打算,而更因为我们目睹了她在之前之后的一系列努力:在去年的那个夏季,她所打的许多个电话,无数次困难而费力地与人沟通;在青岛足不出户地与老爸一起逐篇核对文稿,没有电子文档的文章就把书或报纸杂志翻出来,寄到北京的编辑部去;与编辑共同设计每一集的主题与所包含的文稿,甚至对封面装帧的设计也反复再三地讨论……
对于成名作家来说,这些本不必亲力亲为;对于驾轻就熟的作家来说,这些本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对于我母亲这样一个连完整地说一段话、念一段文章都不可能做到的病人来说,是何等耗费心力,是何等痛苦交织……医生在她出院时曾再三嘱告:要多休息,绝对不能劳累!做任何事持续时间不可超过半个小时,特别是使用电脑——但她一旦投入自己的文学事业,这些便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有位老戏剧家这样说:“叶文玲的康复,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奇迹。又整编出文集,是地道的‘叶文玲现象’!”
作为她的儿子、大学时代读过工科、至今仍在各种身份表格的“职业”一栏写着“工程师”的我,对“奇迹”这个词,一向是有所保留的。从她生病的那天起,我就认定了一个事实——她肯定会康复,除此之外别无可能;我始终认为,迟早有一天,她会完好如初地站在大家面前,微笑着,一如往常。
在我妈妈想来,也是一样。
如果说,这漫长的一年半时间里真有什么称得上是奇迹的,那奇迹的创造者必定属于那些给她开刀、为她护理的医生和护士,属于日夜陪伴、为她分享一切的老爸,属于那些为她操劳担忧、忙前跑后的亲朋好友,属于那些对她关怀无微不至的领导同事,但最多的,无疑属于母亲自己,是她对生活对文学的由衷热爱,和对自己生命对事业的无比信心,才造就了这一个小小奇迹的诞生!
那么,奇迹还是有的,只要有执著的爱与信心,便能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