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关于对话 张公者对话白谦慎——关于“伪书法”的对话
张公者:您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以下简称《娟娟发屋》)一书中指出,清初的傅山把非名家的书刻也作为取法的对象,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某些汉代刻石的书手或刻工"似不读载籍之人";傅山还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观点。到了晚清的康有为,更是鼓吹"魏碑无不佳者"。傅山、康有为的观点对于提倡质朴书风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作用一直影响至今。
白谦慎:对碑学的实践与观念发展历史,我的书有极为简略的勾勒,但我没有对其实践做价值判断。是否会有负面后果,我想见仁见智,喜欢的认为是开放,不喜欢的认为是胡来,完全看人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判断它。
张公者:我谈的不只是"立场"上的问题。将那些缺少法度的"不成体统"的、"丑陋"的碑字作为经典去学习,本身是存在问题的(这方面问题,我在后面还会向您请教)。取法碑字,我并不反对,相反是赞成的,我本人也曾在碑学上下过功夫,问题是取法的方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大谈碑学,但我觉得他并没有按照自己提出的理论去进行学习与书写,他是用"帖法"写碑。
白谦慎:康有为参加过科举考试。准备科举,不可能不碰帖学。今人学书法,一开始就从碑学入手的并不多,即使有,通常选择《张玄墓志》之类比较规整的碑刻,很少有人会上来就学《爨宝子碑》之类的石刻。写行书更是要从帖学入手。所以,自从有了碑学后,碑和帖就一直是在相互交融的。康有为很有意思,喜欢把话说得很大,我想这里有一个修辞策略的问题,"语不惊人死不休"。实践上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张公者:康有为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他的理论是"害人"的理论。学习书法,开始与结束(最后的方法)都不能取法碑。如您所说,即便开始就学碑,也是选取诸如《张玄墓志》之类的近于帖法甚或是用帖法书写刻制的碑。
事物开始与结束往往是一致的,是通会的。魏碑作为学习的中途可以汲取营养,可以增强骨力。这里说的"碑"主要是北魏时期的,汉碑不完全归于其中?汉碑大多数是相对严谨的,更符合书法典范而可取法。
白谦慎:最后的方法能否一定不能取法北碑,我没有仔细思考过。
张公者:我们是否可以将汉碑或魏碑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书法家书丹者,"有法"可言,可直接作为大众化的取法范本;一类是"不读载籍之人"的完全以记录内容为主题的刻石,它们只能作为具有一定审美能力与功力的书法家的借鉴资料。
我们不排除在这些民间化的书写刻石中有一些是暗合了书法审美趣味的"作品",而这些个别"精彩"的字只是巧合,并非常态。我们看到北魏时期诸多造像记在字的结构上是很"丑陋"的。这种造像记因其历史和苍朴的特征,具有了某种美感,亦因其为刻石,在线质上有力量感。
白谦慎:我在《娟娟发屋》里表述了这样的看法:对古代的文字遗迹,不要一概而论。要仔细区分哪些是书家或职业书手书丹后刊刻的,哪些是没有书法训练的无名氏随手刻划的。分得不细致的话,很多问题就不能很好的解决。
张公者:对于某种缺少法度的书写,只有对书法有深刻研究者、技法过关者才有提示的作用。在创新方面,也往往是一些不成熟、不完善的作品会给我们以启发,创作出新的风格,往往是对不成熟书写的完善。
白谦慎:上面谈的都是创作的问题。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娟娟发屋》的主旨就是引言的第一句:"本书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书法的经典?一种本不属于经典的文字书写在何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书法的经典?"我关心的是,那些"不完善"的文字遗迹怎么就变成了经典?有些文字在它们被写或刻出来的那个时代,并不被当时的人们(包括刻写者自己)认为是书法,今天却进入了各种书法的辞典、全集之类的书籍。
用来赞美它们的语言,和用来赞美名家作品的语言没什么差别。
? 张公者:审美趣味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谈创作的时空性,像梵高的创作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接受欣赏他的作品是在所作年代之后,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古代那些"不完善"的字迹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成为经典,与名作一起入书法辞典,这不是审美趣味改变的问题。
我们的一些编辑者、倡导者不应该将能够启发创作灵感的这些书迹说成经典。这只有两种情况导致于此:一种是"唬人",一种是审美病态。
白谦慎:是否应该的问题或许可以搁置一边,事实上是有些不完善的字迹已经成为了经典。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出发,探讨这其中有哪些历史、社会、文化、审美、心理、体制的原因。我本人颇能欣赏古代那些随手书写刻划的东西,但当代一些百姓们随手写的东西也很有意思。
我常反思:为什么我会变得欣赏这些字迹的呢?有时会觉得,艺术走到这步,它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一些批评家们都在思考所谓艺术终结的问题了。我在《娟娟发屋》第十二章"王小二的故事"中提到:西方一些当代艺术家正在努力打破艺术和生活(非艺术)的界限。
这不是虚构,这是西方当代艺术面临的一个困境,想打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破体制的束缚,但就是打不破。我和徐冰也曾提起过类似的问题。他读过《娟娟发屋》,认为提出了一些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
张公者:您在《娟娟发屋》中对"民间书法"这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多的讨论。"民间书法"—此提法本身缺少学术性,或许因为研究者的"研究"而使其具有了"研究性",其实也是研究者自身所添加的,称其为"民间书写"似较为准确。
白谦慎:我主要是对沃兴华先生和马啸先生使用的"民间书法"概念提出质疑。他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有两个问题:一是试图用它囊括的东西太多,对一些历史现象的概括不够准确。二是把一些古代初学者、甚至不怎么认识字的人随手书写或刻划的文字,也作为书法。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古代的文字遗迹都可以算是书法?如果不是的话,哪些不算书法呢?
张公者:有些文字书写是不能成为书法的。我们不妨这样推理:假如把那些初学者、不认识字的人随手书写或刻划的文字称为书法的话,那么所有我们见到的文字差不多都可称为书法作品了,包括"娟娟发屋"、"公厕"……由此再推:所有"书法作品"的书写者就是书法家了—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用手写出汉字—无论是谁,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书法家了—推理的结果多么可笑!
白谦慎:这就是碑学理论在当代展开后出现的悖论。最近有人说,民间书法是古代职业书手的作品,将民间书法等同于今天马路上那些胡涂乱抹的招牌,是将人们引入误区。如果这一说法是针对《娟娟发屋》的话,我想,抱这种看法的人,没有仔细读过我的书,因为我讨论"娟娟发屋"招牌这类书写时,用的都是"字迹"、"书迹"这些词,而不是"书法"。
对古代一些不是书法家写刻的文字,我称它们为文字遗迹,而不是随便地称它们为书法。书法也是文字遗迹的一部分,但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字遗迹,不都是当时的人们所认同的书法。
对每一种类型的字,都应该做具体的分析。早有学者指出,北魏的碑刻存在着几种情况:写刻皆精,写精刻劣,写劣刻精,写刻皆劣。北魏造像记里有大量很粗糙的东西,如著名的《魏文朗碑》的造像记,就极为粗糙,不可能是训练有素的人写刻的,它所显示出来的书写熟练程度,是低于《娟娟发屋》的。这算不算是"民间书法"呢?在沃兴华先生的书里都算?
即使是职业书手,也有一个熟练不熟练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些关于敦煌书法的书中,包括了一个叫令狐归儿的儿童练习抄经的东西,从字迹和他本人的题记来看,他是个初学者,可是他的职业就是写经,他是这个行业里的初学者。这部分人的字迹怎么算?未央宫骨签上的字迹怎么算?刑徒墓志怎么算?刻写者算是有专业的书写技能吗?果真比写"娟娟发屋"招牌的那个人的书写程度高吗?这些都是问题。
《娟娟发屋》引用的大部分粗糙的北魏造像记和敦煌发现的随手写的歪歪倒倒的文字遗迹,也是沃兴华先生和马啸先生的著作中选用的,是他们极力推崇的"民间书法"。沃兴华先生在《民间书法研究》中,引用了一件敦煌写得歪歪扭扭的字,说那张字有"神境"。可是,我的书里引用的武汉陈兮小朋友的字,不同样有"神境"吗?为什么把古代的一些字迹捧得很高,对我们身边同样的字迹却置若罔闻?
张公者:不是"神境",是"神经"。我不是指沃兴华先生,沃先生是当代书家中有思想为数不多的"学者化"书家。我对沃先生本人是很尊重的。说是"神经",是沃先生根据自己审美趣味在取法吸收时产?的"神经冲动反应"。
"把古代的字迹捧得很高,对我们身边同样的字迹却置若罔闻"—这是心理问题。当然时光会给字迹披上古茂、沧桑的外表,使其具有历史感,但这些都是表象。今天仍有人把纸做旧、仿古,更是不可思议。做得越旧,内涵越空。本来还可看的字,这样一"古",便假了……
今天书法界缺少的是深邃思考。一些书法理论研究者较好地在研究古代的书迹与理论著作,但同样是在归纳整理古人的东西,难以见到具有深邃思想的论述,提不出问题。对当代书法的研究多是吹捧文字,吹?文字也是用古人的话语。
理论书籍与文章比比皆是,却少有《书谱》、《艺概》、宗白华式的文章。或说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故弄玄虚。当代书论界缺少思考者。美术界同样如此,难以见到诸如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式的文章,此文章是一篇抵万篇。
白谦慎:真正具有原创力的作品永远会比较少。不过很多书法史的成果看似平淡,却很有价值。这就像许多考古队,终年在做田野挖掘,他们在考古报告中细致地记录下发现的每一件物品。没有这些枯燥的报告,也就不会有张光直那样的学者。《娟娟发屋》就吸取了不少书法史研究的具体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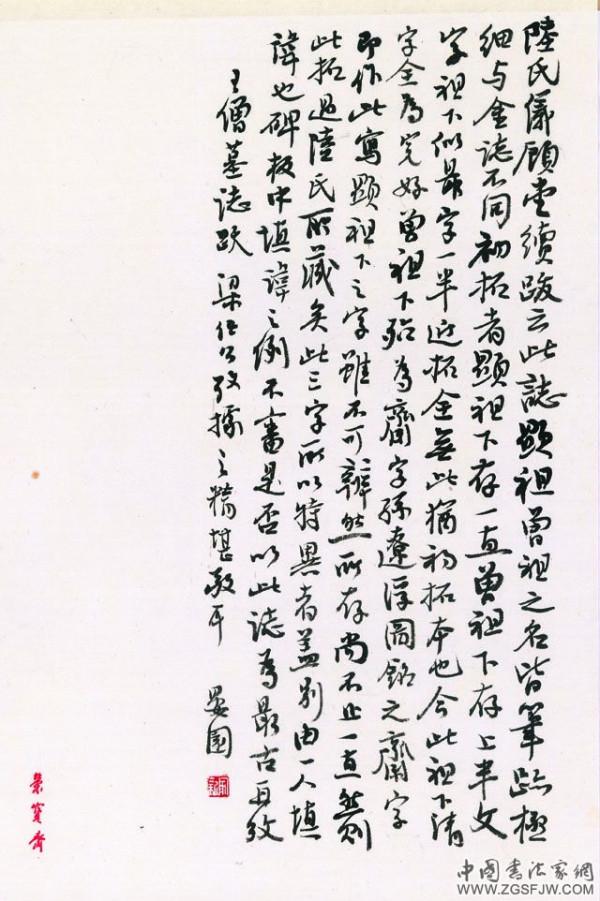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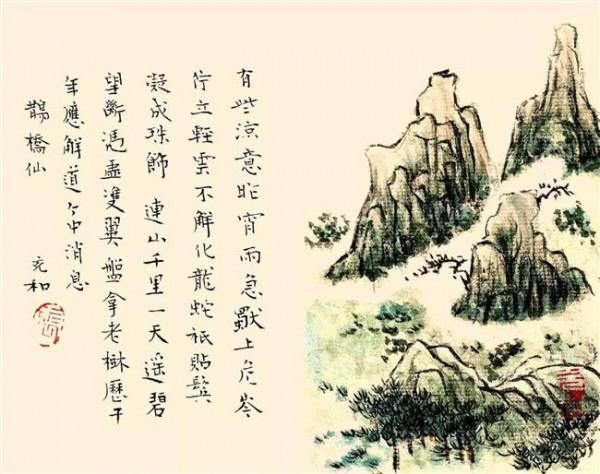


![>白栋材简历 [白恩培张慧清]白恩培老婆张慧清照片 白恩培简历背景资料](https://pic.bilezu.com/upload/1/54/1544dc7598a012f6007d5cbcb253f27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