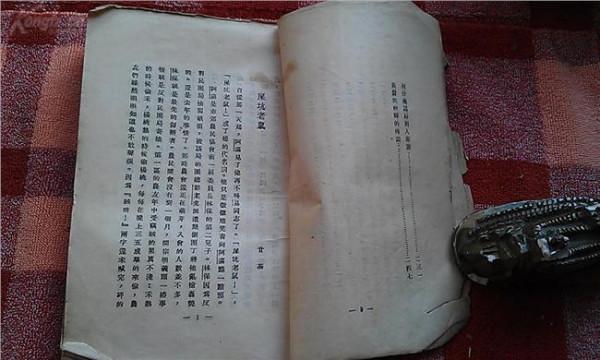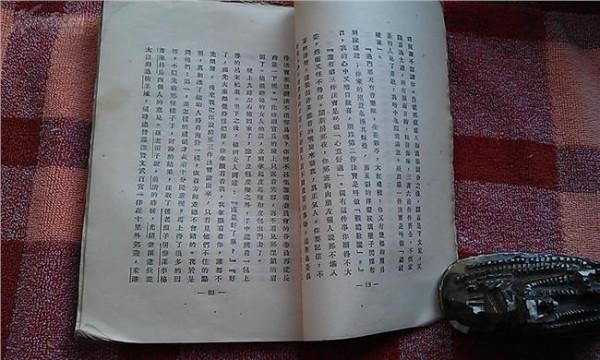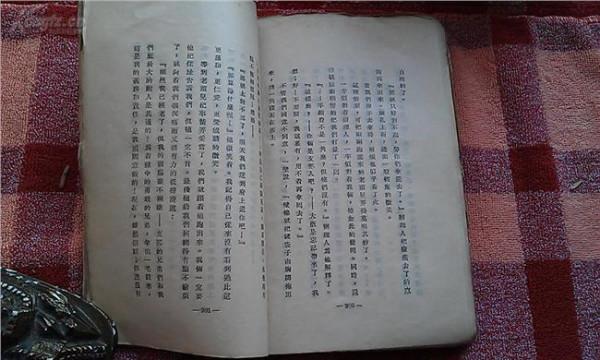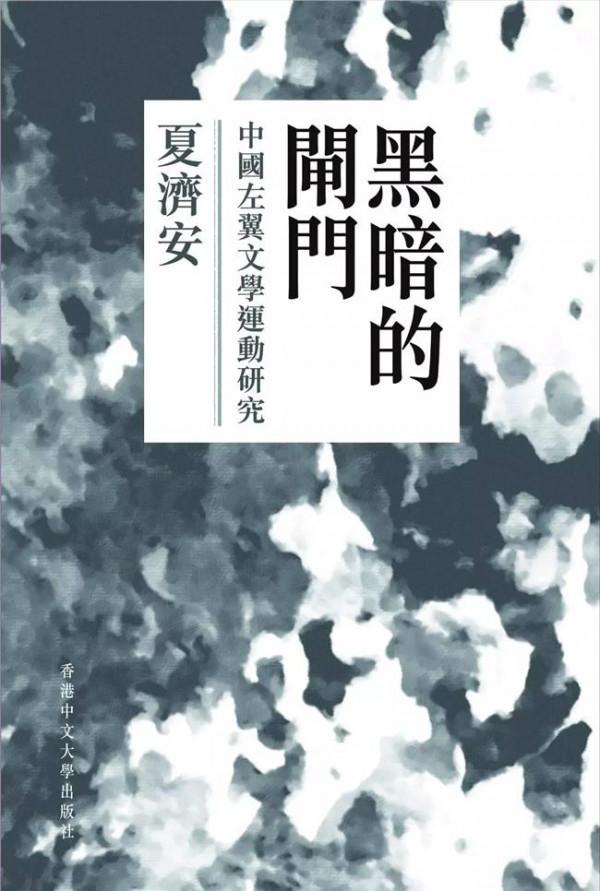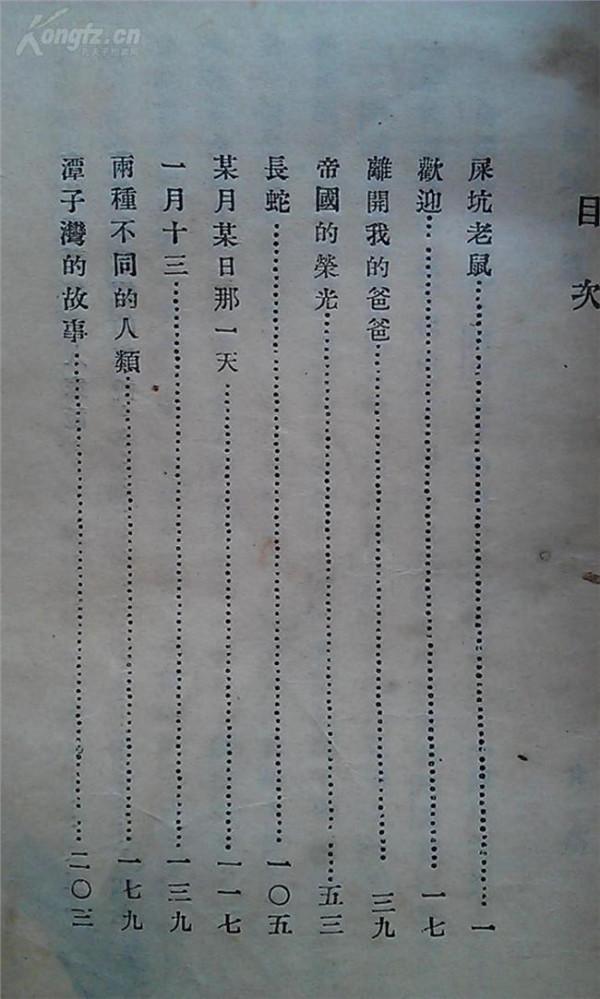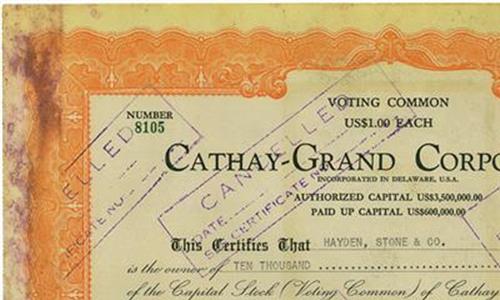蒋光慈文集 蒋光慈:最早一位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之死
作品遭禁,诗人受到通缉 秋天,吴似鸿去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住读,每星期天回家一次。虽然,诗人因此少了爱人的照顾,可对他更好地写成《咆哮的土地》未必就是坏事。写作上,蒋光慈很有些癖好,构思时,他要求绝对的安静,任何一点干扰都受不了。
写作时,他从来都不打草稿,在他,只要写错了一个字,往往就会使整篇文字流产,所以,他总是在完全构思好了,再“一字不掉、一字不改、一气呵成”地写。 11月5日,《咆哮的土地》脱稿。
这是蒋光慈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在他艺术成就上屡遭蔑视与非难之后,文学史上获得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 “蒋光慈的作品,一般地说,在艺术表现上是比较粗糙的……《田野的风》(《咆哮的土地》)是蒋光慈……最好的作品。
”(刘绶松《中国新文化史初稿》)。“《咆哮的土地》是蒋光慈开始趋于成熟的一部作品……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大进展,宣泄式的叫喊已减少,更多是客观细致的描写。”(《中国现代文学史》) 该书将在现代书局出版的预告在报纸上刊登了。
正当诗人自信地眺望着未来,文学界对诗人的远大前程充满着乐观估计时,《咆哮的土地》遭到查封。紧接着,蒋光慈的几乎所有著作也都被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宣传阶级斗争煽惑暴动”等罪名通令查禁。
1930、1931年之交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1931年1月17日,左联五作家在东方旅社被捕,包括同住在万宜坊的胡也频,“和我们单隔着一条弄堂,走几步就到了。”几天后,一个很冷的晚上,一辆巡捕车开到了蒋光慈的家门口。
蒋光慈的悲惨岁月从此开始了。 诗人穷了 作品遭禁后,与各个书局结算版税,总共是一千多元。以蒋光慈的版税虽多,可在用钱上,向来大方惯了。据亚东书局的人说:“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吃、吃、吃、大家吃!
’”(《蒋光回忆录》) 对有困难的朋友,他常常就是五十、一百地救济。还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朋友的夫人说家里经济困难,向他要了一百块钱,可结果呢?这位夫人用它买了一件皮大衣,穿出去大出风头。
蒋光慈知道后也只是笑笑。 下面这个故事颇能反映金钱上蒋光慈的为人。一次,一个同志刚出狱,没衣服穿,阿英问光慈有没有衣服。蒋光慈二话没说打开衣橱,便把他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上所穿的那件西服送给了他。
当阿英发现口袋里还有二十块钱,蒋光慈马上说,“那好,二块钱也送给他用。” 另外,蒋光慈还要往安徽老家寄钱,所以,这些年来,他是一点积蓄都没有的。
现在,生活的全部指望都在这一千多元上了。 他们先在自来火街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后又搬到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间弄堂楼面房子里,最后才在裕德里住下。由于当时是仓促的亡命,什么东西都丢在了万宜坊,刚到虹口时,家具都由房东提供,七拼八凑地应付着。
阿英来看他们,见到这副狼狈相,说外人看了,会产生疑问的,他们这才买了一块便宜的台布铺在桌子上。“但是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有了台布也还是掩盖不了寒酸相。” 为了省钱,吴似鸿已不再上学。
左联五烈士被害后的一天,蒋光慈在街上突然被暗探盯上了,最后不顾一切,从正在跑动着的汽车窗口里跳出,才得以逃脱。以后,蒋光慈只好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又没心思写作,精神越来越苦闷,终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剩的钱仅够三个月使用。
就在这时,吴似鸿发现自己也已染上了肺病。在这之前,为了生活的缘故和吴似鸿的前途,蒋光慈与吴似鸿已分居。现在,也只能让刚回来的吴似鸿去杭州养病,留蒋光慈一个人在上海,请了一个女佣陈妈来照料他。
“现在,只有陈妈算是我最亲切的人了” 春天的西湖格外让人沉醉。吴似鸿在湖畔广化寺租了一间小房子,那里,还住着许多艺专的学生,“我在那里一点都不感到寂寞”。
“春假期间,很多上海的学生到杭州来玩,也有上海美专的同学,他们邀我一同去游西湖,还教我骑马,一起散步,我的休养生活很丰富。” 突然,吴似鸿收到蒋光慈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有陈妈算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读到这样的句子,就是再迟钝的人,也不可能不体察到其中所含的辛酸。这是无可奈何的牢骚与哀求啊! 吴似鸿回到上海后,才知道陈妈原来待蒋光慈一点都不好,就连买药都是蒋光慈自己拄着拐杖上街去买的。 6月的一天下午,蒋光慈的肚子疼痛难忍。
他的精神崩溃了,卧在床上,不能自已地狂呼起来。 吴似鸿找到亚东书局老板汪孟邹,把蒋光慈的病情告诉了他。汪孟邹一直很关心蒋光慈的身体,“他十分喜爱光慈,把他当作子侄看待”,交给了吴似鸿50元钱,并关照一定要住到市中心的大医院去,“那里人多,不容易暴露”。
这样蒋光慈被送进了同仁医院。他的入院登记姓名为陈资川,住三等病房,住院费是每天三毛。吴似鸿以表妹的身份陪伴他。
“人间所有的痛苦,都在我身上呀” 蒋光慈不仅有肺病,肺结核第二期,在医院里,还查出了肠结。在当时,肠结核是一种绝症。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病,以前,蒋光慈不知道,只是将它当作胃病来治疗。 现在,等死的光慈只有饱受痛苦,或依靠注射吗啡走完这生命的最后路程了。
有时实在痛苦极了,蒋光慈就呼喊道:“啊!痛苦啊!” 吴似鸿问他:“你怎样痛苦呢?” 他喊道:“人间所有的痛苦,都在我身上呀!” 以前很多的朋友,现在大多不来了。
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钱杏邨也难得露面。蒋光慈对来看他的“太阳社”同人杨村人说:“我要光明啊,我要太阳!” 8月初,蒋光慈知道自己没希望了,要求医生准许他服用安眠药自杀。 8月30日上午九,朋友李尚贤死了。
下午,蒋光慈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地说:“死了吗?”上午,当杨村人告诉他杨贤在日本死了,蒋光慈同样惊讶地问:死了吗?” “他微笑着。”在蒋光慈死去的当天晚上,杨村人这样写道:“他笑的什么,我想不出来。
或者心想死后有个伴吧。” 将近傍晚时,蒋光慈由极端的痛苦进入到了生命的狂喜界之中。 一向不起来的他突然要求坐起,医生叫护士拿来一个床架,支在他的背后。蒋光慈上半身靠着床架,用一块白被单围在前面,露出宽大的肩膀。
整个脸看上去就像个武士,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亮得像两颗电珠,发出奇异的光彩,直射前方,大笑起来…… 第二天清晨六点钟,蒋光慈死了,享年30岁,死时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当天以蒋资川的名字葬于江湾公墓,所定的棺材比早一天死去的李尚贤还要早到。
墓号为七七七,没有墓碑。虽然仍不能用蒋光慈,但总算恢复了他的蒋姓本姓。 蒋光慈原名蒋恒,18岁时,自号蒋侠生,“我所以自号‘侠生’,将来一定做个侠客杀尽这些贪官污吏”。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愤想当和尚,改为“侠僧”,“我当和尚,也还是做个侠客杀人”。1922年第一次署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鲁迅则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蒋光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