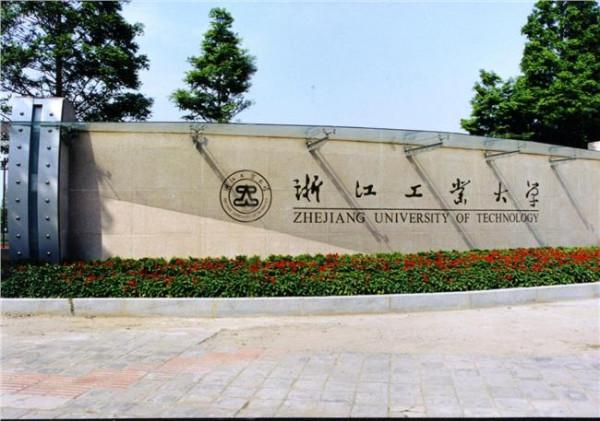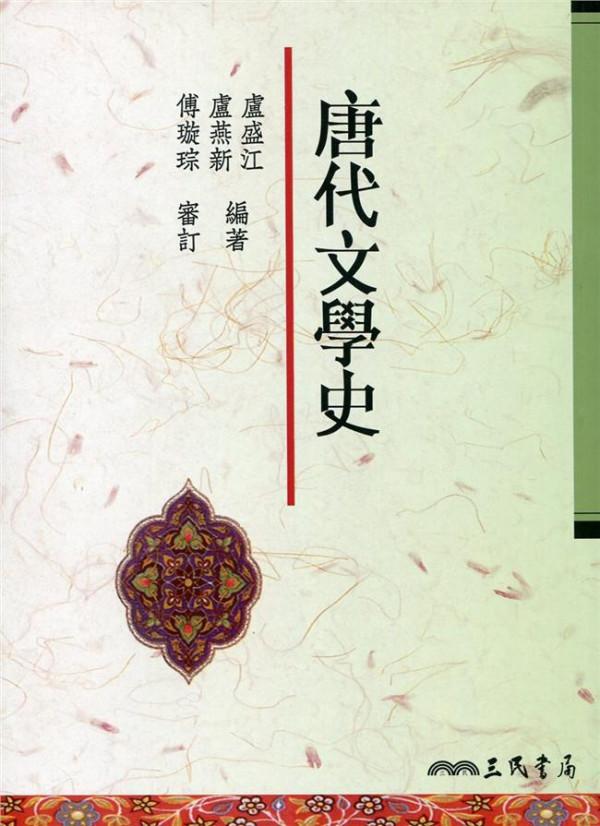傅璇琮为唐代文学 傅璇琮:《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序
去冬今春,我分别在北京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刊物上读到过陈友冰先生的两篇专文,即关於近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以及台湾学界唐代文学研究述论。现在我有幸在正式出版前通阅全书,不期有两种心情,一是感谢,二是钦敬,油然而生。我想这不单是大陆学者,就是台湾学者,也会与我有同感的。
所谓感谢,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正是处於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对新世纪学术研究来说,信息量将是促进发展、提高品位的重要因素,谁在这方面作得富有成效,谁就将居於先行者之列。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唐代文学研究,由於种种客观原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海峡两岸信息互不相通,极为隔膜,对学术研究十分不利。
现在通过陈友冰先生的这部专著,我们海峡两岸的学者,都能对对方的学术行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眼光豁然开朗,胸襟顿然宽畅。没有陈友冰先生这几年的沉潜操作,这种境界我们是达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学人一种传统的铭感之情。
所谓钦敬,有两层意思。一是陈友冰先生这样做,为研究者提供查获资料的方便,这实是一种奉献。现在大陆学者中有一种趋向,就是即使搞唐代一朝代文学的,专业领域也越来越细,搞诗的不关心文、赋,更不问及传奇小说,作初盛唐的不关心中晚唐,因此关於唐代文学研究整体进展情况,就不很清楚。
我想,不少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就可以通过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和利用较多和有用的知识资料,从而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我曾经提到过,我们一些前辈学者,常常是自己动手编制过资料书和工具书。
如陈援庵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有深厚基础和精湛修养的史学家,他撰写过多种著作,但也编过好几部工具书,如《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释氏疑年录》。台湾老一辈学者如严耕望先先编著有《唐仆尚丞郎表》,现在的罗联添先生编有《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续编。这些切实有用之书,实际上是浸融着一种可敬的学术奉献精神的,确使人钦佩。
我所说的钦敬之情另一层意思,是陈友冰先生的识力。本书不是一般的学术报导,实际上是一种学术通论。如记述大陆五十年的研究进程,无论是1949至1965年期间,以及“文革”後,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创新时期,在提供客观的大量的资料之余,总要加以评论,对台湾的几个时期,也是如此。
特别是第三章《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充分肯定两岸学者的成就和各自的优势,就在比较中显示彼此的消长,而在具体评述中又适当指出两岸在某些领域各有所不足。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世界上的事业是要靠一种热情才能做成的,但我们研究历史,一种较高的层次,即哲学历史,就要有“理性”,他明确地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北京:三联书店王造进时译本,1956年)。
这倒能启人思索。陈友冰生是大陆安徽学者,现在担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有一定行政职务,近几年他又到台湾作学术访问,结识台湾南北各地的不少学者,交情不浅。
但他仍能对两岸彼此的学术作出自己的评论,这就不仅需有热情,更要有学术上的一种“理性”。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对古今学术史,“应具了解之同情”。就是说,了解作为同情的前提,同情又作为了解的趋向,由此就可以达成一种超越於狭隘功利是非的通识。
通过本书的阅读,两岸学者确可达到“同情的了解”,就是说,既彼此了解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又增进彼此的交流与情谊。陈友冰先生这样做,其意义已经超越於一本几百页的书了。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其总体成就确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对这一有特色的学术领域,作一种学术史的探索,陈友冰先生此书确是一部创新之作。我们研究学术史,不能只局限於古代,在新世纪全球化发展的新环境,应当把视野拓展到现当代,这样才能使我们更贴近社会,建设一个有科学含义的现代学科。
关於本书的内容,我就不详作介绍,读者通阅之後,所得一定比我还多。我这里想再谈谈一些个人感想。
台湾学者同行,我最早熟识的是罗联添先生和杨承祖先生。十年前我曾有一文介绍罗先生的《韩愈研究》及《唐代文学论集》,刊於1992年的《中国典籍与文化》创刊号。罗先生後来嘱其高足撰文,介绍我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刊於台湾《汉学研究》上,自此就开始了我们深切的学术交流。
八十年代中期,我邀约二十几位唐代文学研究同行作《唐才子传校笺》,《唐才子传》卷四王季友传,其中说:“家贫卖屐,好事者多携酒就之。”後世多以此作为王季友的事迹。
其实这是本於杜甫为王季友所写的《可叹》诗“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杨承祖先生曾有《杜诗用事後人误为史实例》一文(刊於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3年),文中指出杜诗这里并非写实,是暗用谢承《後汉书·刘勤传》。
我曾有机会读到此文,觉得所考新奇而又可信,就举以告作此传笺证的山西大学储仲君教授。按照通例,我们作笺证凡引用现代成果的应注明出处,但限於当时情况,未注明。后我於1990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见到杨先生,向他谈起此事,他听了甚为欣然,此后就开始了我们切磋学问的交谊。
1999年下半年,我应新竹清华大学之邀,去该校中文系教学一学期,同时又至台北、台中、台南等地大学、研究机构讲学,因此认识的学者友人更多,除与我年龄相若的如汪中、阮廷瑜、罗宗涛、王寿南等几位教授外,还有差不多二十几位中青年学界杰出人才。
这样,我对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学风有具体亲切的了解。陈友冰先生书中谈及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的特色和优长,其中有“海外资料比较丰富,学术资讯比较灵通”,我确有同感。我感到台湾文史学界对大陆的学术成果是很关切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他们的论文中总要引录不少大陆的专著与论文。
我在教课中,有时出题让学生作一些专题报告,他(她)们所交的读书小结,首先是列出与题目有关的大陆方面的成果,真使我惊异。
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具体成果却了解得很不够。如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写有《韦应物系年考证》,刊於《文史》第五辑(1979年5月),现从陈友冰先生书中,得知罗联添先生於1969年已发表有《韦应物事迹系年》。
又如我在1982年底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1984年出版,此书主要从文化背景,通过科举考试,探讨唐代士人的生活与心态,以及文学风气,但对考试文体却涉及不多。现得知台湾王梦鸥先生有《晚唐举业与诗赋格样》《东方杂志》,1983年16卷9期),罗联添先生有《唐进土科试诗赋的开始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85年第17期),张正体先生有《唐代科举制度与诗赋体制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7年20卷1期)。
这对进一步了解唐代科举考试及文体沿革就很有参考价值。
我有一个想法,前五十年,大部分时间由於情况壅隔,彼此不通,对研究确有不利一面。但事情也有另一面的,即由於上述情况,对台湾来说,却形成、保持自己独有的治学风尚,这倒是很值得思考。总的说来,台湾的治学风尚,似乎与传统学风更接近一些,这对我们上年岁的人来说,似乎更有一种亲切感。
陈友冰先生书中所说的台湾学术著作“选题细密,能小中见大”,以及台湾学者对诗歌格律颇有研究,且能写出古诗美文,似均与此有关。进入新世纪,两岸学术交流将进一步发展,我相信,彼此必能更好发扬各自优势与特有的治学风尚,携手共进。
陈友冰先生在第四章《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与前瞻》中,对唐代文学学科建设提出很有见解的建议,我很赞同。我以为,特别是现在,我们更应进一步扩展视野,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把海峡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
以唐代文学来说,我们应研究唐诗、唐文是怎样传播出去的,特别是古代的日本、朝鲜,在接受唐代诗文後对本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东亚及欧美各国从前几个世纪直到现在,是怎样来研究唐代文学的。这对於我们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关协调、相接轨的一条途径。我相信,本书将是这一行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