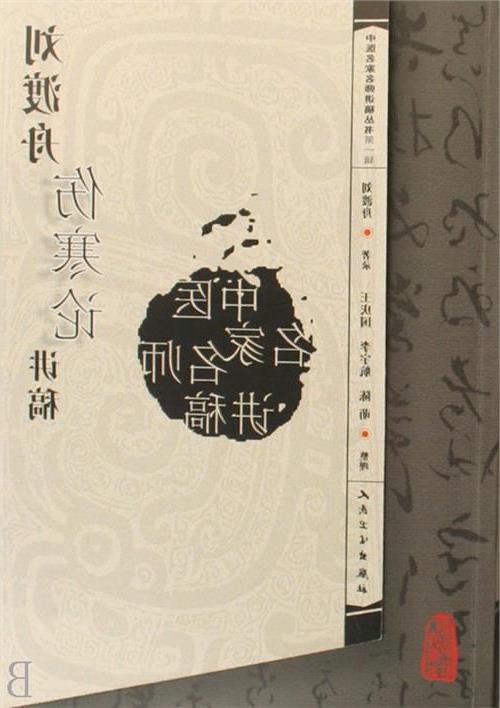深度重识董卿:眼泪是很宝贵的 但眼泪不是唯一的
董卿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音乐响起,舞台后方的一扇门缓缓打开,董卿站在那扇门的后面,抬头微笑,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董卿走向了舞台中央。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初见面时欢喜的遇见。‘幸会,今晚你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这段话是《朗读者》节目第一期以“遇见”为主题的节目开场语。董卿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李云迪在一旁为她钢琴伴奏。这是《朗读者》音乐总监姚谦的创意。在他看来,董卿说话自带情感旋律,最不干扰她又能最好地支撑她的就只有钢琴了。
《朗读者》舞台上的董卿和春晚舞台上的董卿不太一样。她不再身穿华服,也不再把发髻高高竖起,她穿着一身浅粉色套装,搭配白色的丝质围巾。她所讲的那些话也不再是导演给她的主持人文稿,她开始讲她心里的话。这一次,她的身份是主持人兼制作人。
自2005年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至今,董卿已经连续主持了12届春晚。而对于她本人,人们似乎并不了解。2017年,随着《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两档综艺的陆续热播,主持人董卿也随之走红。在“央视一姐”的头衔之外,她又被赋予了“才女”“女神”和“央视网红主持人”等新的标签。
“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董卿啊。”很多人开始感叹,从事主持行业2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15年,站上春晚舞台12年之后,董卿开始被大众二次发现和认识。
采访地点在央视老台附近的一家茶楼,那天上午,董卿刚审了一遍即将播出的一期《朗读者》节目,下午她要见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商量朗读亭(《朗读者》节目的线下活动,为普通人提供的朗读设备)即将进驻清华的事情。“朗读亭摆在哪里,要拍些什么,拍到的内容节目怎么用等。”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外套,黑色裤子,脚上是一双舒适的平底鞋。头发被她用墨镜拨到了脑后,没有化妆,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前一天晚上,她还在为接下来要参加节目录制的嘉宾人选发愁,还有五期节目要录,她和团队需要从几百个人中最终选出30人。“可能初选就选出两百个人,然后再精选出60人。60人的名单不是我们想要的都能来,再从60个里面选,可能最终契合我们的40个人。”董卿说,最后一期可能会有更多的返场嘉宾,他们正在策划和沟通。
做了制作人后,董卿坦言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她有一个习惯,手机从不带进卧室,她的卧室里没有电子产品,只有纸质书籍。可最近这个多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她需要通过手机和很多人保持联系,独处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这让她有点苦恼。
《朗读者》节目所有嘉宾的朗读文本都需要董卿一一过目,工作人员通常会把文稿打印出来拿给她,她说自己看稿子没法看电子版的,那样的话她一个字也记不住。她必须得看到白纸黑字,在上面写写画画,那样让她觉得踏实。这是她二十多年前刚开始做主持人时就养成的习惯,改不过来了。
“以我的价值观来说,这也许是你一生当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对了,忍不住要告诉你,丹麦有一个三万人的小城市,它每年有六十个作家节,你可以带着小组去拍点东西。那里的酒吧都在读,到处是听的人,就像看歌剧,看电影。他们生活里有一顿饭,是耳朵的饭。”作家毕飞宇在《朗读者》播出后给董卿发来短信。
这样的赞美董卿最近收到了很多。而在节目策划阶段,对于《朗读者》,除了支持,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个东西太有文化了,太高冷了。”前期开策会时,有人这样说。“我们要对观众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董卿随即回了这句。《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刘欣对这个场景记忆深刻。“你跟所有人妥协,你得到的东西绝对不是你想要的,必须是在最有压力的时候咬紧牙关,出来的东西才是你想要的。”和董卿合作后,刘欣发现董卿是一个努力又较劲的人。
2016年3月份,董卿第一次跟刘欣提起《朗读者》的节目创意,当时只是一个初步想法,还不明确。不过刘欣记得,“高而不冷”是董卿一直强调的观点。作家麦家在《朗读者》节目上读了一封他写给儿子的信,随后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很快,阅读量到了五十万,这远远超出了以往他所发文章一万的最高阅读量。“那封信是有文学价值的,教一个孩子怎么融入社会,我们提供了一个所有人融入的端口,就是父子情。”刘欣说。“我们的定位是文化情感节目,它不是简单的朗读,它其实是人生故事通过朗读的再次抒发,是情感的表达。”《朗读者》另一位总导演田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它是综艺节目,但它不娱乐;它是文化节目,但它不沉闷;它以情感为表达载体,但它很励志。即使落泪,也是有力量的。”在央视综艺频道总监郎昆看来,这是董卿的高明之处。
节目播出后引发的热度超出了董卿的预料。她预期的受众群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让她没想到的是90后和00后成了《朗读者》的主力观众。《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的两天内,自媒体上与之相关的超十万阅读量的文章已经数不过来了,“通常大型季播节目,自媒体上能有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就已经很不错了。”田梅说。第一次节目嘉宾濮存昕所读的本文《宗月大师》出自《老舍散文》,节目播出后,这本书上了微博热搜榜单。有些此前拒绝过节目组邀约的嘉宾如今也改变心意了。
而超出董卿预期的这一切和郎昆的预期完全吻合。“这个节目得益于很多方面,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董卿,这就相当于《中国诗词大会》,它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董卿,这个你必须承认。” 郎昆和董卿相识20年了,他曾担任2005年春晚总导演,那年也是他的一通电话,董卿站上了春晚的舞台。“董卿不是一个简单的主持人,她实际上是一个电视人,一个传媒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她只不过是以主持这个方式来切入。”
《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刘欣在央视工作十年了。2016年3月,董卿为《朗读者》组建团队时,最早找到了他。第一次见面,听董卿讲完节目创意后,刘欣就有点激动,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制片主任,三个人当时就开始“头脑风暴”。
“当《我是歌手》里出现一个李健,一个赵雷,大家都疯了一样地喜欢。当高音你听了太多了,声嘶力竭的喊,不是说不好,但当只有那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正常的文化形态一定是多元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只有一类肯定是不正常的。”刘欣说,《朗读者》就是为观众提供一小块拼图,让观众在里面得到情感的释放。
郎昆觉得董卿是敏锐的,她及时抓住了朗读复苏的潮头。而《朗读者》也正符合了中央电视台文化示范的目标。
节目前期策划阶段,董卿请来很多人,圈里的圈外的,有名的没名的。她有一个厚厚的名单,同行白岩松、作家刘震云和导演陆川都在她的名单里,她说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见谁就说,她需要在反复的阐述中理清自己的思路。这期间,郎昆带着董卿去全国各地做节目推广,面对企业、媒体和观众代表,董卿讲了十多次。大概到了2016年底,“为谁读,谁来读,读什么,怎么读。”董卿把这个线梳理得很清晰了,郎昆说那时候他就预料到了,董卿会赢。
在郎昆的印象里,董卿对自己从不放松,“大到春晚,小到日常栏目,有的主持人忙了或累了之后会对付,董卿从来不对付,非常奇怪这个人。”董卿经常来郎昆的办公室,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今天貌似解决了,回家琢磨琢磨觉得不对又回来重新跟你谈,一件事没弄对,她都跟你没完。”
田梅之前跟董卿合作过《开学第一课》,董卿会把当事人留在舞台上先面对面前采,为第二天的正式采访做准备。到了《朗读者》,通常是节目已经到后期制作了,一个小时的采访只能呈现六七分钟,董卿会拿着导演的速记一句一句自己划。从策划开始到现在,累计了几百篇的读库,每一篇董卿都看过。她和导演组一起为嘉宾选读本,办公室有时候会陷入沉默,“没辙了,永远被否定。”董卿说,“观众看完这段采访再听完这段朗读觉得完整了,或者说过瘾了,那才是电视制作的一个方法。”
《朗读者》录影前,董卿还是会焦虑。不是紧张,是做了制作人后被太多事情牵绊的焦虑。晚上八点,大家继续排练,她一定准点从现场离开,当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她需要用这段时间把第二天要录的节目再细细梳理一遍。
“要么在台上主持,要么在台下为台上的主持做准备。”这是董卿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筹备《朗读者》这一年里,台下的工作她通常是和团队一起完成的。而此前她唯一的身份是主持人,台下的工作她都自己在家里完成,没有人知道她都做了哪些功课。她经常在书房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一天都不离开那把椅子。
春晚直播之前,她一个人待在书房,想象着全国观众就在她的面前,“中国中央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她开始大声练习,“那音量之大,估计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早于全国观众听到了我的串联词。”董卿开玩笑说。“这些话在我嘴巴里滚了上百遍,上台才有那个底气。”玩笑过后,董卿说。
2004年底,距离2005年春晚不到一个月,董卿接到了时任春晚总导演郎昆的电话,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当年春晚主持人。董卿曾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回忆,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她刚搬新家,正在扫地,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谢谢郎导。”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她开始拿着扫帚在屋里转圈。“已经累瘫了,但那一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搬一次家。”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那一年,董卿搭档李咏,周涛搭档朱军,组成了春晚新的主持阵容;董卿一身红色礼服,第一个开口说话。她记得那年他们四个人是站在升降台上,“哗的一下,升上来了,哗的一下,走到台前了。”如今董卿回忆,她当时心里就一个声音,“我来了。”
这是董卿调到央视文艺频道的第二年,来央视的第四年。董卿是1994年进入主持行业的,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陪朋友考试,自己却意外被录取。带着新人的热情和新鲜感,她又做主持又做编导,她形容这是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两年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1996年央视春晚在上海开设了分会场,当时董卿负责场务工作,那是她和春晚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郎昆和董卿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那个时候。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去上海东方电视台出差,董卿还是一个小女孩,去电视台门口接他。八年之后,2004年,央视开办音乐频道,举办了一个直播音乐会,董卿是那场音乐会的主持人。郎昆也是在那个时候觉得董卿可以登上更大的舞台。
当年恰逢倪萍退出春晚,“必须有人接上去,而且这个人不是临时接一两年,她一站可能就是十年甚至十五年。”如今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当年选董卿,是有一点冒险,但又充满期待,“就觉得董卿行。”
也是这个时候,董卿找到了主持人的职业满足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优点会被无限放大,给了我特别大的动力。我特别清晰地知道了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谁,我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还可以拓宽我的边界。”
她主持《欢乐中国行》,在一个城市只待一天,其实哪儿也去不了,但她需要在台上做到“口吐莲花”,让观众感觉到她哪儿都去了。从入住酒店开始,她先是翻酒店的旅游小册子,然后看当地提供给她的素材,再加上上网查资料。“哎呀,你对我们这儿真的太了解了。”听到当地人这样的回馈,董卿觉得她完成了她的工作。
观众开始习惯了晚会中的董卿,就如同她自己也习惯了这样的自己。
到了2012年,在董卿来央视整十年的时间节点上,她觉得该是时候改变了。“卿姐,我们有台晚会,你来主持一下。” 周围的事情还在良性运转,提到晚会,大家顺理成章就想到了董卿。可董卿发现自己没那么期待这样的舞台了。她形容自己以前上台跟打鸡血一样,无论台下发生什么,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只要让她拿起麦克风,对着镜头,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她就会兴奋到忘记所有事情。
2012年开始,她很难再有那样的兴奋感了,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徘徊。
2013年,她主持谈话节目《我上春晚了》,录到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她和嘉宾都感到疲惫,她感觉到节目状态不理想。回到家是已经是晚上12点了,她坐在沙发旁的地毯上,把刚刚的节目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我要是换种问法,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一句话,会不会好一些呢?”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你可以去睡了,下次会更好的。”她对自己说。
困惑还在持续。一年后,她选择暂时离开,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再回来的时候,她开始了《朗读者》的筹备。
“你为什么要做《朗读者》?你做主持人驾轻就熟,所谓的行业地位也摆在那了。”周围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来最忠实的观众——她的父母。父母的出发点很单纯,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觉得女儿没必要在40多岁的年龄再去做一件如此耗费心力的事情。“我心里挺难过的,我从浙江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他们从未有过半句的怀疑或阻拦。”董卿说。
“我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董卿这样告诉周围的人,她知道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了。
董卿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如今,父亲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当年的同窗,不少新闻从业者。《朗读者》播出之后,董卿经常会在父亲的朋友圈看到鼓励她的留言。
董卿泪点很低。有天晚上她翻开《朗读者》嘉宾斯琴高娃的读本,想到了作家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书,她花了半个小时翻看了书里的几个章节,“哎呀就不行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天夜里她熬到四点睡觉,第二天录制,九点她起床化妆,化妆师吓坏了,“脸没法看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
“如果这个人物是想打动情点,但我丁点反应都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她审片的时候这样跟大家说。在《朗读者》的舞台上,徐静蕾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徐静蕾在台上哭了,董卿在台下也听哭了。
这是一个反感煽情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人们似乎对于这些动情的段落很认同。“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我们不能说,哎呦,哭了,节目就成了。”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采访麦家时,麦家说了很多他跟父亲的故事,“那个裂度特别大,一个孩子几十年不跟他的父亲说话,之后他每年都要坐在父亲的坟前跟父亲讲话,把十几年没对父亲说的话对着泥土说出来。”而经过后期剪辑,最终节目中呈现出的“催泪点”只是录制当天的百分之三十。董卿很清楚,在感性之外,她是电视制作人,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她需要从参与者的角色切换到局外人的角色。
演员赵文瑄录制《朗读者》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董卿,印象比较深的是董卿和刘谦搭档的魔术节目。录制当天,他第一次见董卿,他跟董卿聊大咪(他的猫)带给他的改变,“不知道怎么搞得,就哽咽了。”他跟《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以前参加电视节目,也不是没有主持人想要‘勾引’我谈及伤感话题,我从来没有就范过啊。”他说自己总是刻意回避太过汹涌的感情流露,那天当董卿坐在他对面时,他自愿打开了自己的情感阀门。
《朗读者》的音乐总监姚谦留意到了董卿在《朗读者》中细微的眼神变化,“喜欢文艺的人很容易在与别人交流时流露真性情。”姚谦跟董卿接触后,发现她跟春晚上得体大气的形象有点出入。“她对文字很敏感。”姚谦说。
《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田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私底下开玩笑说,董卿对面的那把椅子有神奇的魔力,坐在上面的人,总会敞开心扉去讲述。在郎昆看来,嘉宾之所以愿意对董卿打开心扉,源于董卿对他们的尊重。“她把对事业的尊重平移到了对嘉宾的尊重。”郎昆说,“ 董卿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做不到的,现在为什么能,年代感已经到了。”
跟嘉宾聊天时,董卿总是习惯性地身子往前倾。为了让她的脸看起来更好看一些,通常这个时候,灯光老师就会举起大纸板,上面写着“坐回去”, “有时候说得好不好听,比脸好不好看更重要。”董卿心想。
郎昆看《朗读者》,看董卿采访徐静蕾,当时提到奶奶,徐静蕾说不下去了。看到这儿,郎昆有点紧张,他特别怕董卿继续追问。董卿当时什么也没说,徐静蕾缓了一下接着讲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多余,都没心没肺。”他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这一幕让他自然联想到了倪萍。当年他把倪萍从青岛带到中央电视台,就是看中了倪萍“和嘉宾同步喜怒哀乐愁惊恐忧”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董卿和倪萍极其相似。
董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访谈节目会是她的终极舞台。她希望跟人们有心灵的交互。“如果你没办法体会他人,体会自己,没办法认知他人,认知自己,那么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