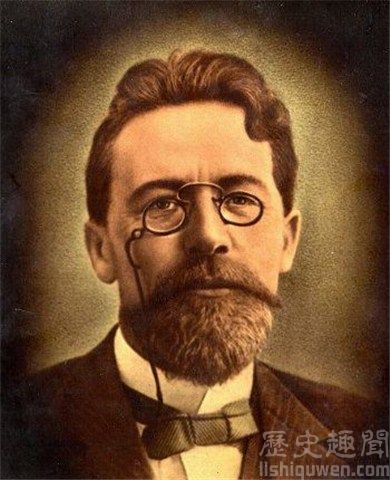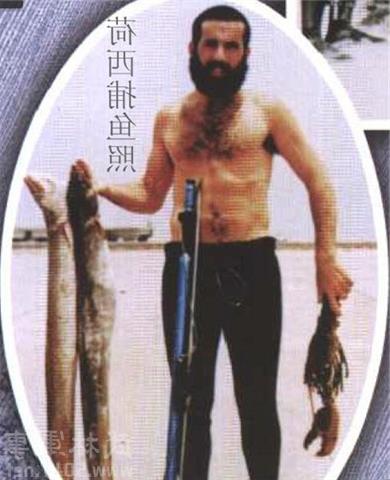如何评价左小祖咒 怎么评价左小祖咒?
左小祖咒是我个人很欣赏的摇滚歌手。之前资讯匮乏,只知道他在南京卖过打卡CD。以为他是南京人,他的口音很怪异,所以有点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建湖人,建湖是盐城的一个县,离的也很近。算是我的老乡。左小祖咒生于船工家庭,本名叫吴红巾,你要是熟悉建湖,会觉得这个名字就很建湖。

说来盐城出过许多很牛的人,其中文化人就不少。比如骂曹操的陈琳,比如抱着小皇帝投河的陆秀夫,比如新中国时候的“二乔”——胡乔木和乔建华。如今,做官也不少,尤其盐城的北三县:滨海,阜宁,响水。以前穷,留不住人。

都要拼命读书,留在繁华的城市中,日后出人头地。出名的大官有仇和,有王荣。有一年全省评选藏书家庭,盐城有人得了第一。台湾的郝柏村也是盐城人。以前算是蒋匪,如今回来一趟,政府替他修祖宅,建公路,算是荣归。此节则是闲话。

我听摇滚很多年,那年忽然出了两支很怪异的乐队,一支叫NO,一支叫苍蝇。苍蝇乐队的乐手大半都是日本人,据说技术奇佳。主唱丰江舟,好多年不听说的名字了。苍蝇乐队唱的歌词很脏,围绕这茅房,苍蝇,屎尿屁什么的。音乐则充满了所谓的实验性,也就是大段的吉他噪音,喧嚣含混淹没在效果器里的歌唱。
对我来说,听到就是猎奇,至于好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不听苍蝇,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听摇滚。 另一支就是左小祖咒担任主唱的NO乐队。在一张拼盘唱片中,听到他的《阿诗玛》,全篇左小祖咒捏着嗓子尖叫着唱完。当然不算动听。
唱片文案中介绍这支乐队,特别说艾青的儿子艾未未表扬左小祖咒的诗写的好,至于和他老子写的一样好,还是超过他老子什么的,我就记不清楚了。顺便说一句,我不喜欢艾青的诗,虽然有几句话常会拿来用用。
但左小祖咒写的东西,确实不错,虽然我也看不大懂,但觉得这人的措辞很直接,比拟很生猛。日后看些资料,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背景,才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理解。比如《让我再见一次大夫》里的那句“把我从福尔马林的标本瓶里捞起来……要找回我的左股、左腿、左肋、左手、左肺、右派的爹”。
比如《走失的主人》:我是逃遁又追逐在自由王国的一碗宫爆鸡丁,被无数的先辈们烧烤在黑暗的宴桌上舞蹈。比如《关河令》里“把你的三项插头插在我口里,亲爱的你能感到我的心跳加速。”中国的诗歌写作在当代几乎是一个笑话。但在许多摇滚歌词中,找到尊严。
NO乐队里,还有一个乐手叫做夜千,应该早没有什么人关注了。与左小祖咒分开后,他出了一支单曲,叫《嗜睡症》,词曲很棒。再后来,似乎转做幕后。那时候常常有人问他们什么时候重组NO,我看过一点当时的访谈。左小祖咒说夜千这人技术很好,也老劝他练吉他。但左小祖咒觉得练这个没有意思。现在想来,左小祖咒还是很有远见,中国的音乐不缺技术,就缺想法。
夜千后来搞不出名堂,而左小祖咒风生水起。 据说左小祖咒的写第一首歌叫做《莫非》,莫非是他第一个女朋友的名字。最后的一句歌词是“这美好的一天,在结着果的桃树下我边吃边哭泣地瘫在你墓前。”那时候左小祖咒还在混画家村,一次演出中,最后喊了几十声“莫非”。——当时的一篇报道如是说道。比起后来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小莉》来说,当然要深刻,也沉痛许多。尤其对听他半天《阿诗玛》的我来说,当时听,不亚于天籁。
我记得在桂林的时候,买大门乐队的唱片,听左小祖咒评价杰米莫里森,说老头唱的真棒。那会儿我忽然发现,左小祖咒的唱法和莫里森神似。近似述说的唱法,当然,也继续保持他的荒腔走板。不习惯的人的觉得他唱的全篇都是走调。事实上,他就是走调。只是走得很好玩。
第一次喝咖啡肯定觉得苦的受不了,没有糖水好喝。喝多几次,咖啡还是苦,但又忍不住要喝,但糖水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所谓药性这玩意,就是越听越重的。我听完苍蝇,听完NO,下面就直接听音速青年,听灰野敬二。买市场上出现的每一张奇形怪状的CD。试听一段,如果平滑如油,心顿时一沉。心想自己这回是俗气了。
那时间的人生就是一种不断的纠结之中,要往最少数人的品位中靠近,要特立独行。害怕所有过于美好的东西,包括悦耳动听,因为美好不够真实。当然,这些奇怪的爱好也只是私下的趣味。出门在外,还是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卡拉OK里唱歌,照样只唱刘德华的《忘情水》。
愤怒是一种学习。时间是最好的引导,于是愤怒的学着如何无动于衷。 为什么忽然想起说左小祖咒,我也不知道。最近他的音乐越来越好听。他最近唱所有的歌都压着嗓子低吟,即便时不时的走调,也是别有味道。有人批评他食髓知味,玩的确实有点过了。
有一段时间他去做节目。说话疯疯癫癫。以致我终于认定理性的人根本不会写他那样的歌词。他本是一个城市游民,据说某年一个化工厂爆炸,警察还会把他从出租屋里给提溜出来作为嫌疑犯关几天。这段经历,触动他写了一本小说。
他那时候混在画家群里,动不动搞点行为艺术什么的,比如跑到北京近郊的无名山上每个艺术家干一件事情。其中有个人撒了泡尿。最后一群有男有女脱光了叠在一起,拍个张照片起名《为无名山峰增加一米》。再后来,他将一群猪叠在一起,作为纪念,当然也能说是向往事致敬。
他的所谓艺术,就是荒腔走板。近代的中国表面充斥着所谓正统意识。但事实上,最实在的内核还是背叛的态度。一本正经的人再成功也是被笑话的。要是的玩世不恭,而且要的是实惠全拿下的玩世不恭。 左小祖咒那会做唱片,价格卖的奇高。到底卖了多少估计没人清楚了。
“要让艺术家富裕起来”。
再然后,他忽然有点搞起公知那套了。他在微博上针对任何公共话题发声。写歌纪念大地震死去的孩子。让钱云会的父亲唱了一首《钱歌》,那个悲伤的老父亲用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浙江方言半吟半唱半说。故事的背景在那里,所以听起来我们都很沉重。
再后来他的朋友艾未未出了事情。现在想想,艾未未出事的岁月还是一个不错的岁月。人们用各种方法帮艾未未补所谓的欠税。艾未未则做了一张漂亮的欠条送给每个帮助他的人。人们相互取暖,以戏谑以及艺术的方式抗议。而被抗议的对象,则多少有点羞羞答答不知所措,以致最终袖手旁观。
再然后,抱歉我忘了具体是前是后,就是左小祖咒丈人家的强拆事件。我当时对此很有感触,在当时,一个所谓名人应该用尽的办法,来进行卓有成效的维权。即便是我,也充满强烈的不适感,我承认,有点嫉妒的成分。日后我家遭遇拆迁,那种无力给人强大的挫折感。谁叫胖子当时粉丝少,当然混到现在也没几个。
所以我痛定思痛,我努力,我要加粉。 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清醒的有点不地道。所以我当时还是跟朋友讲,一个艺术家还是不该靠现实太近。 当你有太多感触的时候,你就会轻易的表达。表达多了,必然导致你艺术的注水。好像我最怕写的就是时评,这玩意写着写着就会上瘾,而且好写,一挥而就。点击又高,捧场的人也多。以致忽略了很多时候必要的观察和思考。某天回过头看,毫无积累,更无作品,只剩一堆屁事。
和菜头那篇有点臭名昭著的文中,说道林语堂和鲁迅的区别。他说有些东西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有些东西能留下来。说真的,我以前也有类似的看法,即便今天也不是太改。我读诗的时候,最不喜欢那些所谓革命诗人。我最多只读卞之琳的《断章》读郭沫若的《女神》,我对他们后来的作品嗤之以鼻。
诗人,我只爱徐志摩爱戴望舒。爱纯粹的东西,爱和时代一点边不沾的东西。抗日的时候,所有的作家都去写抗日作品,为民族疾呼。张爱玲却写她的小情小调。于是傅雷就劝她多少做点姿态吧。张爱玲回答出名乘早。很要命,今天我还是要看张爱玲,却不大想读《傅雷家书》。
也罢,就一直跑题下去吧。我其实已经很久不认真听音乐了,音乐只是写作读书时候的背景。是空间的填充物,是对外界噪音的隔离。但我再也不关注谁在唱歌,他在唱些什么。所以回忆起过去听到的音乐人,忽然想起那段岁月在音乐中的思考与幻想,有点怅然起来。 晚上烤好叉烧,喝了一点酒,然后去洗把澡,擦个结结实实的背。然后回家,泡杯白茶,百无聊奈,便对着这空白的时间絮絮叨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