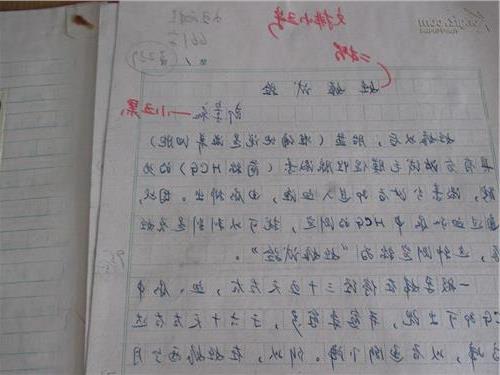郝景芳北京折叠 郝景芳:在小说中折叠北京 在现实中抚平折痕
去年夏天,郝景芳到湖北的两个国家级贫困县—鹤峰、长阳考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的运作效果。该项目由她所供职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07年发起。
都市中的“激荡三十年”在这里回声寥寥。尽管很多家庭并非一无所有,但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常识缺乏就像贫困代际传递的一座桥梁。在郝景芳看来,比起儿童身体成长所需的营养,大脑与心理良好发展必备的养分—父母、老师与孩子的语言、情感互动同样关键,甚至更加重要。这是比物质更难改变的不平等,“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靠砸钱就补得上来的。”
回京之后,那些在父母离去的空屋子中游荡的孩子们的身影不断盘桓在郝景芳的脑海中,她在自己的公众号与博客中写下几个思索已久的有关改善贫困儿童现状的愿望,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发展为“童行书院”项目的种子想法:
“如果我有很多钱,我想建度假村,建五星级、堪比Club Med(注:全球知名的法国亲子度假品牌)的度假村,建在这些少有人来的美丽的山里,有儿童运动场、图书室、游乐项目,旅游旺季供城里的家庭带孩子度假,淡季就让孩子们免费读书。”
彼时,她还未获得雨果奖。她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承担基金会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课题、参与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公益项目,坐地铁穿过匆忙的城市打卡上下班,在两岁的女儿还未醒来的清晨抓紧时间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晴妈说”写作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学、婴幼儿脑科学的文章。
“可是我没有很多钱,可能也不会有。”在同一篇文章中,她紧接着写道:“于是就在这样无结果的幻想中生存,为了做不到的事,做不放弃的事。”
落笔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瞬即,各路采访、活动、演讲邀约纷至沓来。
郝景芳拒绝把自己置于这不期而至的热闹中,她不想让一部完成于2012年的小说打乱现在的生活轨迹。
奥迪也给她发出了活动邀约,郝景芳照例回复“不参加商业活动”。对方锲而不舍,连着发了几封邮件,最后一封写道,“公益梦想也可以支持”。郝景芳不太敢信,反问:“公益也可以吗?”最终,奥迪与她敲定了合作事宜—提供100万元支持她的公益创业。
“原来出名也是有些好处的。”郝景芳第一次觉得。
脑海中、笔尖下那个以旅行度假做公益教育的种子想法得以生根发芽,郝景芳开始与好友—中科院儿童教育专业博士西西为“童行书院”奔走联络。从内在逻辑上,这个项目和《北京折叠》是一致的,都是郝景芳对困惑良久的不平等问题所做的实践。
头脑实验
《北京折叠》带给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像科幻。郝景芳的本科与研究生都在清华大学读天体物理,但一般科幻的核心要素—炫目的前沿科技、宏大的宇宙设定等并非她对科幻创作的追求。
科幻是有关可能性的文学,郝景芳喜欢运用这种可能性的空间,对她困惑已久的不平等与社会制度问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头脑实验:将现实中某一个略显荒谬的单一因素推向极致,推导它最终可能形成的局面,并希望这种“实验”结果像一束光一样,照向现实中一些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地方。在《北京折叠》中,她将自己感受到的“不平等”推向了一个极致。
日渐拥挤的未来北京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将时间与空间切割为三个部分:大地的一面是住着500万上层精英的第一空间,他们拥有完整的24小时;另一面是住着2500万中产阶层的第二空间和容纳了5000万底层人群的第三空间,他们分别使用一天中的16小时白天和8小时夜晚。昼夜之间空间翻转,根据出身与阶级,不同的人们在其中轮流苏醒,交替生活。
主人公老刀五十多岁,是一位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为了帮女儿筹措幼儿园学费,铤而走险帮第二空间的一个研究生给他在第一空间实习时认识的上层人家女孩送信。
小说没有惊心动魄与生死离别,甚至有一丝温情意味:老刀被从下层奋斗到上层的好心人出手相救,最后终于有惊无险地返回第三空间。后知后觉的震撼隐藏于其残酷的底色:看似已经被压迫至最底层的第三空间层民众,实际上原本可以被足够发达的机器人彻底取代,他们在8小时的黑夜中处理垃圾的命运,已是第一空间决策者们“怜悯”的结果。他们甚至不具备被剥削的价值。
这一切对郝景芳来说并不陌生。2011年夏天,在读研究生的她找了个高大上的实习单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班时她时不时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望着仿佛闪着光的国贸地带,目睹精英与决策者们谈笑之间就可能影响许多人的命运;下了班回到“第三空间”—海淀清河,小区外随处可见摇摇欲坠的棚户、横七竖八的小摊,空洞灰暗的烂尾建筑张着嘴无声地呐喊。
四季变换,棚户和小摊的主人们带着他们无处归依的孩子来了又去,像习惯了漂泊的吉普赛人;或者,他们将孩子留在家乡,自己抱着改善生活的愿望不知归期地游荡在首都边缘。其下一代的命运似乎已经昭然纸上—现实的引力是如此沉重,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信仰,对于匍匐前行的个体是不可望更不可即的奢侈之物。
从某种程度上说,郝景芳就像她另一部小说《流浪玛厄斯》里那群少年中的一个。他们出生在规则严明、一切共享的世界,长大在行为肆意、完全交易的另一个世界,回到“故乡”之后却遭遇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2012年,郝景芳花3天时间写出了《北京折叠》。
看见那座城市
郝景芳极少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提及《北京折叠》。雨果奖只是另一个耀眼的存在,它的光亮照不进那个实际存在、却形同隐形的第三空间。它只是她众多写作计划中一部长篇的序幕,而她笔下所述的一切在现实世界具有高度相似的投影—在同样的时刻,甚至在同一个地点,不同的人们也在经历着截然不同的城市,那些折痕已清晰可见。
郝景芳对不平等问题困扰已久。在她看来,中国两千年的王朝经济史几乎就是一部与不平等抗衡斗争的历史。大部分朝代都以均分田地、限兼并抑豪强的尝试开始,但这种努力维持的局面早晚会被兼并浪潮席卷,之后调整税制以适应现实,实际等于承认了贫富分化,而这种对经济活力的抑制最后又导致停滞不前的小农经济。
向全世界看去,不平等问题也依然存在,北欧童话般的冰雪世界中似乎有一些幸运儿生活在永远的春意中,而炙热的非洲大地上仍有无数人困苦于饥饿、贫穷与疾病的寒冬。
郝景芳想知道,这种不平等是不是人类的一种趋势性的内在规律,就像气体分子自然均匀分布于空间,通过一时的外力施加作用可能呈现某种特定分布规律,但撤掉外力后很快恢复原状,而人们只能靠极为有限的努力来尽可能弥补不平等之间的差距。
早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念本科时,她就曾试图用一些物理学上的分布律去拟合美国收入分配曲线。后来她发现,用一个数学函数去做这个拟合并不难,但这背后说明着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则是这件事更为关键的部分。她开始关注不平等问题在制度上、政策上的可解性。
2014年,郝景芳博士毕业,没有选择出国,没有成为国贸白领,她去到了一个半官方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主要工作为承办会议、开展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相关的公益项目,以及承接政府、企业委托的经济、社会与治理领域课题,最终成果是政策建议,提交到委托方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郝景芳参与的研究课题很多,包括城镇化战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国崛起战略研究、一带一路对外发展研究等等。她的工作勤勉出色。同事张荆观察到,不少同事跟自己一样,喜欢有事没事找郝景芳聊天,“她不会让你觉得她的优秀和她的知识是一道门槛,虽然它们确实是一道门槛。她会鼓励你去不断地尝试、坚持、积累,然后达到你的目标。”
尽管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金会的许多努力仍只是杯水车薪,但这份“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工作让郝景芳非常喜欢,“哪怕只是一点点持续不断的努力,积累到很多年也有改变的可能性。”
《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与马可·波罗探讨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乐土还是地狱,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之口说道:
“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地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郝景芳选择了第二种—看见,然后行动。
拒绝贩卖悲惨
郝景芳描写了许多制度,觉得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她写,也只是为了证明它们的不完美。不平等问题像是人类史上的一头恶龙,每一个前去征服它的少年都葬身其腹或最后自己长出了鳞片取而代之。
在这样的终极悲观下,郝景芳反而越加信奉个体努力的意义,她希望在折叠、分化和隔离的另一端做一些努力—融合。
大三时,郝景芳到西部地区支教过一段时间。一年多后,她接到其中一个学生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女孩给一户人家当保姆,她告诉郝景芳,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和女孩的父母沟通后,郝景芳把她接出来,在自己的亲戚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送她回家。女孩回到学校读了幼教专业,毕业后当了老师。几年前女孩结婚,郝景芳受邀参加,“还是那么点儿小孩呢,就已经是高中班主任了,”她感叹。
郝景芳不愿意强调自己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看着女孩为自己勇敢争取来的幸福生活,她想到了那些默默承受命运的孩子。“我更心疼那些没求助的孩子,我觉得她们现在可能真的还在大城市做小保姆,我想到她们心里更难受一些。”
这些经历让郝景芳如今开展童行书院项目时,特别强调公益的可持续性。童行书院是一个以“旅行 公益”为核心的社会企业,目标包括自己造血输出公益,免于在募捐压力下产生“贩卖悲惨”之举。“童行要努力挣出做公益的钱。挣钱和独立,有时候也是道德。”
童行书院选址风景优美的贫困地区,目前已确定贵州省紫云县和兴义市楼纳村、河北省张家口崇礼三个点。其模式是以当地现成的或新建的度假村为场地,在节假日等旅游旺季对城市家庭开展亲子旅行课程,通过旅游项目赢利;在平日里,书院则变为当地儿童免费接受课外教育的基地,并向周边的学校输送书本、课程等教育资源。旅游项目的收入用于支付公益项目派驻在当地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及日常开支。
在童行书院驻站教师招聘贴中,郝景芳阐述了童行书院的公益理念,“我们对公益的理解是尊重和互通有无。我们拒绝俯视的慈善和虚假的自我褒扬,因此我们更需要你对自我与他人有笃定的理念。”
招聘贴发出十天内,郝景芳和西西收到了170多封邮件。在郝景芳看来,来信中一些闪着光的文字片段所透露出的灵魂,甚至比简历上那些醒目的学校与单位名称所代表的经历更为珍贵。
“中止纸上谈兵的做法就是亲自走到自然中去,像个孩子一样蹲下来看世界。视角低一些,就会带着敬畏和尊重。对有形之自然,对无形之教育,都应该是这样的道理。”
“十年前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希望现在更加成熟的自己,更知道想要什么的自己,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三十岁的自己,一次新的机会。”
写下这些段落的人都顺利通过了视频面试,入围见面会。郝景芳发现,“他们人如其文,笃定、淡静、有自我认知,同时内心还有隐含着的希望。”最终, 9位驻站教师、3位全职员工加入了原本只有郝景芳和西西两人的团队。他们中有航空飞行工程师,有杂志编辑,有心理咨询师,大多工作经验丰富,一多半有孩子,甚至有的人会带上另一半与孩子一起驻站。
童行书院亲子旅行与公益的根基,其实是严肃的教育事业。西西表示,她和郝景芳都很认同的一个理念是,教育这件事从本质属性来说就是公益,因此,驻站教师被要求不仅仅会讲课,更要对心理发展、自我成长、科学艺术等有自己的理解与追求,这样才有可能将其融在旅行与教育中,将儿童的早期发展引向更加开阔的天地。也因此,郝景芳非常重视驻站前为期六个月的深度培训。
培训于三月份开展,所有的课程都是郝景芳与西西一一去联系的,专门为童行书院定制,由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或机构负责,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博士陈忻、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赵昱鲲分别负责教授的两门理论必修课—发展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除了四门理论必修课与两门实践必修课—美术入门与自然探索之外,还有八门选修课,由中央美院、北师大天文系、国家话剧院、大宝老师博物学校等机构开展,涉及儿童涂鸦、儿童编程、戏剧与艺术等,每个老师需要选修2-3门,修满规定学分后,才可以正式进驻童行书院站点。
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童行书院已经完成了三个驻点选址、十四门培训课程的设计定制、十二名全职人员招聘。一切都在前行,快得让郝景芳“难以置信”,尽管在朋友们看来,她一向以惊人的时间管理能力著称。西西说,郝景芳是少数的那种不焦虑、不拧巴的人,她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不会多花时间停在原地纠结后果。
郝景芳珍惜这由雨果奖而来的东风—若想多做些什么去对愈加固化的阶级施加哪怕一点点影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她的心中没有无力感。在她看来,与不平等问题做斗争就像西西弗斯被诸神惩罚永远推石头—也许不平等现象就像大石头一定会向山下滚去一样自然,好不容易向平等的山顶靠近一点,稍一松手又回去了。
一个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能起到多大作用?“可是人还是在这样一遍一遍滚石头的过程中,只能相信意义就在这其中。”郝景芳很喜欢加缪,因为加缪理解西西弗斯,“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