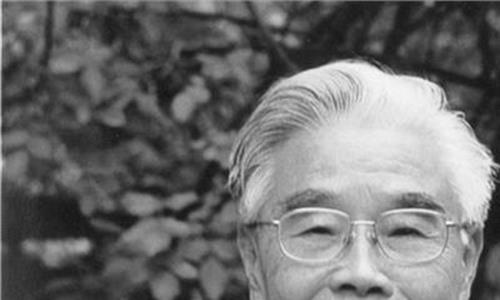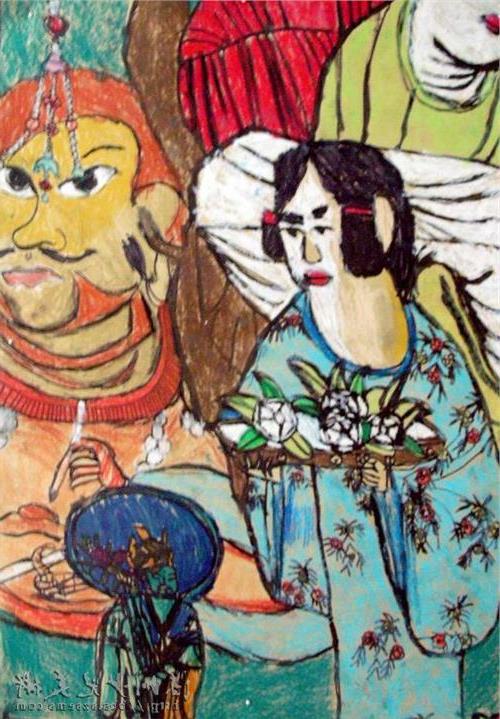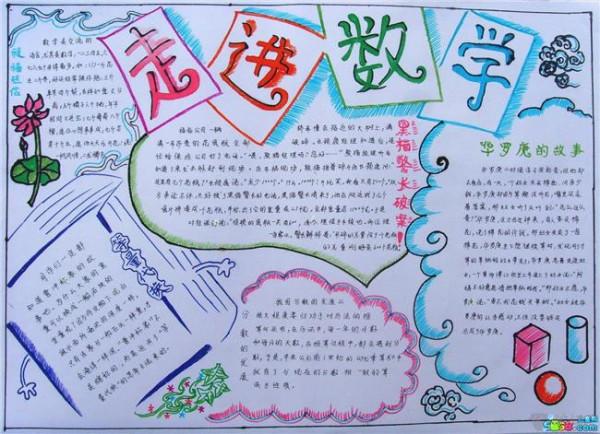张世英日记 张世英忆西南联大二三事(一)
传说中的西南联大,因为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映,最近被许多读者、媒体关注。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紧跟热点,持续热销。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的张世英先生,去感受那段炽热得令人难忘的岁月。

初进西南联大
1941年秋,我和一位同时考取联大经济系的中学老同学陈才昌同坐一辆“黄鱼车”(抗战时期来往于缅甸和昆明、重庆之间载运战时物资的封闭型大卡车,司机私自拉乘客从中赚钱,把乘客“闷”在车厢里,人称“闷黄鱼”),途经贵阳,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昆明。山路崎岖艰险,虽非蜀道,却比蜀道更“难于上青天”。我们两个人一路上尽发感慨:“大学之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西南联大的校址位于昆明城西边缘,校园前门,一块大横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个大字,赫然而立,令我俩肃然起敬。我俩笑着说:“总算经过大学之道,走进了大学之门!”
联大校舍本部是一排排的人字形茅草房,办公处、教室和老生宿舍都在本部,唯独一年级新生宿舍是附近昆华中学的校舍,两层楼洋房,居住条件比老生好得多,我们对联大的第一感觉是“不欺生”。

从中学到大学,就像乡下人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花样多,什么都新鲜,都神秘。这系、那系,这样的课程、那样的课程且不说,新生谈论最多的是:他昨天见到大名鼎鼎的冯友兰,满脸大胡子;我今天见到数学天才华罗庚,一跛一瘸;忽而看见一位穿长袍长袖的教授模样,就猜想可能是北大的;忽而又见到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模样,就猜想可能是清华的。总之,眼花缭乱,充满了敬仰之情,心里以考入这样的大学而自豪。

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进校不久,就碰上由联大学生带头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从经济学著名教授陈岱孙讲授的《经济学概论》课程上刚刚学到的名词)。
在西南联大,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北大旧交,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
还记得有一次(时间已记不清)孔祥熙到昆明,据说原想到西南联大做一次讲演,但又不敢,改到云南大学,云大与联大只一道破土墙之隔,西南联大的同学闻讯后,成群结队,蜂拥而至,先占领了云南大学大讲堂最前面的地盘,大讲堂没有座位,学生们都是站立着的。
孔祥熙尚未露面,一片怒吼声已经震撼了全场,他的侍从黄仁霖把手指插在口内,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想借此压场,同学们更加愤怒,高喊“流氓,流氓”!
孔祥熙出场了,一站到台中间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姓孔,孔子的后人呀!我也是个教师,当过小学教员,还兼校工,摇过铃,让学生上课……”显然是想用这些话来打动我们,引他为同类,以赢得同情。同学们看他这气短的模样,总算放过了他。这惊心动魄而又带有戏剧性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这样的场面恐怕也只有在西南联大才能见到啊!
李广田先生要我用白话文写作
我念西南联大一年级时最感兴趣的是“大一国文”课。“大一国文”共分26个班,接英文字母排列顺序,我那个班的老师是文学家李广田先生。李先生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在给我们讲“大一国文”时就有些名气。
他讲课语言生动,爱与同学交谈。“大一国文”的课本中选有王国维《人间词话》,“三种境界说”给我印象极深。“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李先生讲解三种境界的内涵之后,留下作业,要我们思考,自己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境界,并写篇短文交给李先生评阅。
李先生在看了全班作业之后,似乎在班上边笑边介绍,说了这样几句:大部分同学都主要是谈“第二境”的经历,或因恋爱而“为伊消得人憔悴”,或因考大学开夜车而“衣带渐宽终不悔”,大多没有谈“第一境”和“第三境”的经历。
李先生特意表扬了我,说我谈的“第三境”还“有点意思”,那就是在解决了一道几何难题之后所得到的快乐,就好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很高兴李先生给了我表扬,但现在想来,只有“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才有“第三境”,我何人也?哪来此境?至于“第一境”,李先生在总评时似乎没有对同学们的作业作什么介绍,我对此亦无印象。
依照我现在的回顾,对于一个刚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学生来说,大学特别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我面前所展现的那丰富多彩、无限广阔的前景,实在令我迷惘,也令我向往。我尽情地观望,无穷地选择,我在初进西南联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才真是处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里。
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写文言文),这是西南联大的特殊规定,我不习惯,问李先生是否可以写文言文,李先生说:“应该改一改了。”没有多作解释。李先生出的作文题是“人与枯骨的对话”,我写的内容主要是寄托自己的大同理想。
李先生在文末批写了一句评语:“有妙想自有妙文。”给了我92分。我有点得意,后来投稿到昆明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很快就发表了,时间大约在1943年或1944年。
60多年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篇文章,便要我女婿赵誉泳(武汉电台文艺部主任)通过关系在武昌某博物馆里费了几天的功夫,终于找到了这张报纸。由于当时是抗战时期,报纸的质量很低劣,从这一面可以透视到另一面,有些字迹已难以辨认,甚至破成空洞,无字迹可寻。
现将原文抄录如下,以见我由文言文转向用白话写作的轨迹,亦或可由此文窥见一点那个时代的社会世故和人情。抄录时,带有猜想似的作了不少补遗的工作,还略微做了点修改。
听刘文典讲《红楼梦》
西南联大校门前的一侧,是校本部的内墙,也是同学们最爱聚集的热闹区,各式各样的海报和小广告都贴在这里,联大的几次民主运动也都从这里发端。我刚入联大念一年级时,有一天,从这里路过,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在一起谈说着,一打听,原来是刘文典当晚在昆北食堂讲《红楼梦》。
找海报,真有其事,也不过是两三尺见方的一张破红纸。海报不起眼,却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离讲前还有半个多小时,昆北食堂挤满了听众,时间越来越近,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只好换地方,连换两次,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露天大院,安顿了下来。
听众焦急地、也静静地等待刘先生出场。一等两等还不见刘先生的身影。有人说:刘文典可能抽大烟还没有下床。有人问:刘文典是不是被蒋介石传召去了?(当时,西南联大很多人都知道刘文典抽大烟和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敢于顶撞蒋介石的逸事)。
超过预定开讲时间半个多小时,刘文典总算姗姗而来,嘴里叼着一支纸烟,吞云吐雾,好一会儿一言不发。大家席地而坐,鸦雀无声,静候刘先生开口。
我的化学老师著名教授严先生就坐在我身旁,我小声问他:“严先生,您怎么也来听《红楼梦》呀?”答曰:“我学化学的,怎么就不能来听点《红楼梦》呀?”问得我哑口无言,又觉得他的话很值得玩味。
好不容易刘文典开了口,第一句话:“啊啊啊!你们各位都是林黛玉、贾宝玉呀?”全场哈哈大笑。严先生早已等得不耐烦,便应声回答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的,都是大混蛋、小混蛋!”其实,他是为了泄愤,骂刘文典的,他的声音很小,估计没有什么人听见。
刘文典接着说的第二句话是:“我要讲的,都是别人没有讲过的;别人讲过的,我一概不讲。”我当时只是个一年级新生,丝毫没有觉得他狂妄自大,恃才傲物,只有一片崇敬之心。今天看来,刘文典此话,也值得我们这些学人学习。
刘文典不紧不慢地讲了很长时间,具体内容都不记得了,好像只是就某个词句做详细的考证,对于我个人来讲,当然更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东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到《红楼梦》里某些诗词时,便兴致勃勃地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地吟诵一番,说道:“写文章也要讲究音韵,讲究节奏,否则,语言干瘪,算什么文章!
”(大意)我当时已感到刘文典的讲演本身就富有诗的意境:他讲演时,往往闭目沉思良久,一言不发,只见他在烟雾中摇摇晃晃,却没有一个人退场。他讲演结束时已经是深夜,还有人围着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我初入西南联大,仅从刘文典的这次讲演活动里,就已深深体会到,这里的确是一所春风化雨、弦诵不绝的学术殿堂。
文章节选自中华书局版《张世英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