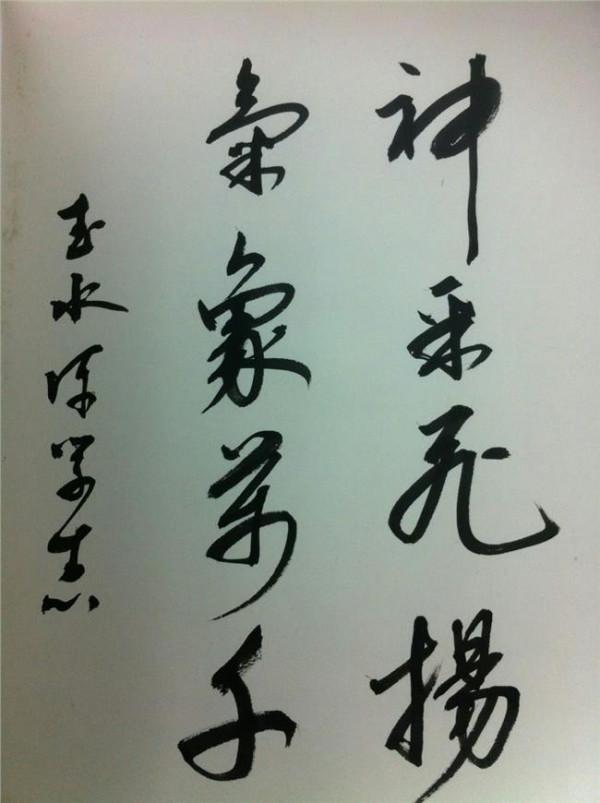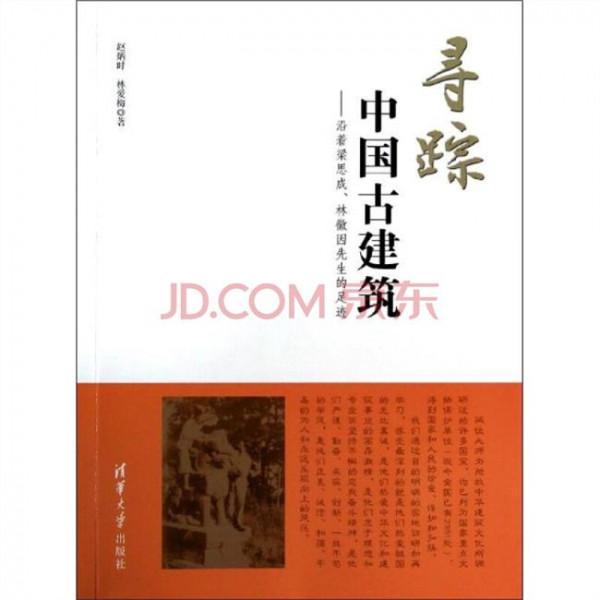王岳川是季羡林的学生 王岳川:《季羡林在东方文论和中国美学上的贡献》(下)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受到了朱光潜先生等著名教授的美学启蒙。后来,他对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评价也很高。在中西美学的陶冶中,季羡林认识到,中西方各有各的审美趣味、审美积淀和审美历史,但对于中国重视品的美学思想,是一种高尚情怀的审美显现,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高迈的美学价值。
其一,回答美学研究转型与中国文论 “失语”问题
季羡林在当代美术界全盘向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挪用拿来甚至的时候,注意到中国古代美术文化的辉煌和输出。他在《中国美术之西传》中明确写道:“随着中国哲学思想之西传,中国美术也传入欧洲。……据说梵高也学过中国泼墨画。
除了绘画之外,中国用具也流行欧洲。轿顶围的质料与颜色,受到中国影响。中国扇子、镜子传入欧洲。十七世纪后半,法国能制绸。中国瓷器西传,更不在话下。同时中国瓷器也受到西洋影响。”。[29]季羡林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非常关注,面对西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流派和大量术语,如果中国学者不根据本土文化发展和艺术土壤,找到自己的文论话语,而仅仅用一些与文学创作格格不入的术语和理论来炫耀一世,当对中国的文学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这国际文艺理论论坛上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难道我们中国真正没有话可说吗?难道国际文艺理论的讲坛上这些时生时灭的理论就真高不可攀吗?难道我们中国的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就真正蠢到噤若寒蝉吗?”[30]季羡林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
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擘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31]我认为,21世纪中国文化复兴将对人类产生更大的影响,未来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
当今,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
在这一个充满变化的格局中,中国文论失语现象是暂时的,中国学者有责任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就美学研究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季羡林在《美学的根本转型》一文中认为,中国近代美学主要受到西方美学影响,美学家在西方美学的范畴里兜圈子,难以出新。作为感性学的西方美学,基本上只限于眼和耳,研究眼视之美与耳听之美,而忽略了鼻、舌、身三个方面。
从“美”的词源出发,中国美学大可不必紧紧跟随西方美学模仿抄袭,而是必须以我为主,从审美实践出发,把生理与心理感受的美融于一体,寻找建立新的美学体系之路。[32]可以说,季羡林的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反对唯西方的马首是瞻,其实说到底,审美内在本性就提升人的活生生的感性,张扬美善的精神,鞭笞丑恶的东西。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美学理论问题在于:各种美学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西方美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这个平台似乎使我们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
在我看来,只能把西方美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我们的本士资源。现实是,我们的美学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
我们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我想强调的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应该走出拿来主义模式,走向文化输出。[33]
季羡林认为:“美学”这一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西方美学家只讲两官,即眼与耳。中国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从词源学上来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
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34]季羡林看到了美学研究的误区和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提出美学必须转型。必须触及一些带根本性的美学问题——当代中国美学必须彻底转型,这在西化严重的世纪末,无疑具有整聋发聩的效应。
季羡林认为,中国人面对一件艺术品,或耳听一段音乐,“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或音乐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了不知多少抽象的名词,令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
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烂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
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35]季羡林清醒而乐观地指出,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语”,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
“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36]
对季羡林的看法,我十分认同。我认为西方仅仅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中国文论和美学发展中的追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
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我们必须认识到,中西文论不仅是文化场域不同,文化根基不同,而且今天社会发展格局不同,文学创作的美学价值观不同,不能完全照搬拿来甚至挪用抄袭。
我们应该反省,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提升博扩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如何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让西方人以欣赏而不是猎奇的眼光发现东方?如何在“文化对话”中重新找到中国文论和美学身份,实现自主式创新?如何在后现代社会解决人类所遭遇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有可能通过方法的不断催新,进而达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创新,在国内语境中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在国际语境中从拿来主义主义走向输出主义,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从话语盲视走向精神自觉。
其二 中国文论界如何看待现代西方文论
季羡林指出:“当前世界一些国家的五花八门的新理论,什么结构主义,什么心理分析,什么新批评派,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接受美学,等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呢?第一,我们要认真研究,加以分析。如果有精华的话就加以吸收,一概拒绝是不对的。
第二,我们也不能一概接受,拜倒在它们的脚下”。[37]总之,西方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作为被误读的“东方”的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思考的毋宁是:在后价值后良知时代,中国学者有没有能力、资格和水平对世界未来提出自己的文化问题和全球性文化发展问题?
季羡林无疑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他引用汤因比的话:“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38]藉此,季羡林主张:“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球已经快踢到东方文化的场地上来了。东方的综合可以济西方分析之穷,这就是我的信念。
”[39]“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西方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现在这个世纪末可能就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40]季羡林的观点大胆而有独到见解,实为知识分子良知做出的大文化趋势判断。
毋庸置疑,在新世纪应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重塑中国文化形象,挖掘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全球文化普世化中的中国立场,即知识分子的学问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对本民族的文化负有传承责任和价值担当,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彰显东方文化身份。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获得的标志,大国文化崛起是在同世界和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实现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已成为新世纪的主题和文化战略。
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时代困境中,中国知识分子要以“天下”为大局,以学术为“公器”,在中西对话中坚持“本位话语”立场,对西方神话般的“普世价值”增补差异性思维角度,向整个世界呈现“东方智慧的文化重量”,批判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重铸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文化,担负发现东方与重建世界文化精神生态的历史使命。
其三 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季羡林先生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学史受政治影响太大,问题太多,应该下决心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纂写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样的重压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41]在诊治现状提出问题以后,季羡林认为,有人认为文学作品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政治标准中有“人民性”,另一个标准叫做“艺术性”。“翻看近四五十年来所出版的几部部头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或者有类似名称的书,我们不难发现,论述一个作家作品的政治性或思想性时,往往不惜工本,连篇累牍地侃侃而谈,主要是根据政治教条,包括从原苏联贩来的洋教条在内,论述这位作家的思想性,有时候难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
而一旦谈到艺术性,则缩手缩脚”。[42]面对这一二元对立,季羡林认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艺术性应该放到第一位,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为读者所接受。”[43]因此,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必须把艺术性摆在前面。中国文学史必须改写。
季羡林认为,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神韵”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概念。无论是谈诗、论画,还是评品书法,都离不开它。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在评品顾恺之的画时,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
” 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
神韵一词,除了应用于文章、艺术等方面外,也用来评论人物。所以要特别注意中西方不同的语言特征,凸显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就中国文艺理论而论,源远流长,极富特色,但是使用的术语却有点不易捉摸。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气”字;刘勰的“道”与“神”,还有“风骨”;钟嵘《诗品》的“滋味”,“文已尽而意有余”;唐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宋严羽《沧浪诗话》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清王渔洋的“神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子才的“性灵说”,直至王国维的“境界”、“隔与不隔”等,皆说明神韵不在言而在意。
实践着自己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季羡林通过写散文和创作书法,展示自己的文艺理论思想的可行性。他的散文和书法可谓大美——强调境界大、视野大、眼光大、气魄大,在某种意义上内容横跨经、史、子、集。
他通过笔、学养、眼光做到大手笔书写,规避了小趣味。“气”是浩然之气,孔颜气象之气。大气盘旋之“气”充沛于天地。季先生一身清气,遗世独立,有浩然之气。“象”是孔颜气象之“忧道不忧贫”,是汉唐气象的辉煌大气。
季羡林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以多元化的开放眼光看待当前的文化纷争和文艺理论问题,或批判、或弘扬、或反思、或建构,充满睿智和诗性的语言比比皆是,既显现了论者大气而灵动的诗性品格,又新人耳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精神指征和理论穿透力。
在美学研究转型与中国文论失语问题上,在中国文论界如何看待现代西方文论上,在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等问题上,季羡林捭阖纵横,在恢宏的学术视野下探讨了当代中国文论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不仅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沿性,而且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和理想主义光辉。
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理论,坚持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强调“西化”必将让位于“东化”的看法,以及在东方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立,中国文论和美学研究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
进而面对全球化弊端,他提出解决的途径是生态文化观点——“天人合一”。我认为,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
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我们必得沿着季羡林思考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中国文论和美学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文化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东方文化创新和审美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
















![《季羡林散文选集》(季羡林)扫描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9/18/918367e46d1b3ee17e3cd7a87cf17551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