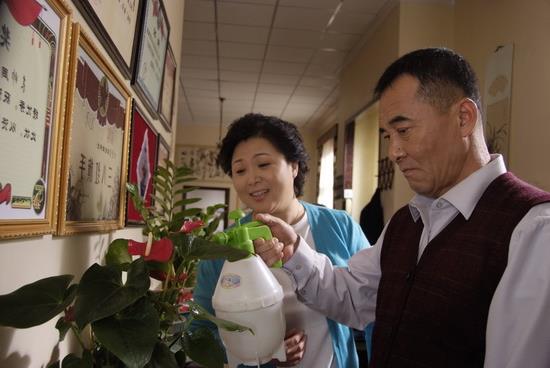吕瑞英丈夫 吕瑞英 悠然独行 笑靥灿烂(组图)
这段令外人好奇、揣测了多年的往事,在吕瑞英看来其实非常简单——“华东”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和提升的空间,而去芳华就成了头肩旦,在变成“老大”的同时,她也失去了向别人学习的方向。
向往学习和进步的吕瑞英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得到了充分的滋养和成长,她积极地学文化、学音乐,不管喜欢不喜欢,只要觉得有用,她都去学,而且都学得挺快、挺好。回顾那个阳光明媚的1950年代,她感喟道:“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学习和工作,能够整天在舞台上实践,真的是很幸福的!比起现在的青年演员,我是一个幸运儿!”

21岁那年,吕瑞英创作并首演了影响至今的代表作《打金枝》,创造了一个越剧舞台绝无仅有的“骄傲公主”形象,《打金枝》后来成为国家元首观看得最多的越剧作品,周总理、陈毅元帅、陈丕显等国家领导人都能熟背该剧。就在同一年,吕瑞英在《西厢记》中扮演了红娘,从此获得了“活红娘”的雅号。

1960年代,她那极富个性的吕派艺术逐渐成形。吕派一改越剧普遍具有的哀怨情调,洋溢着清新明朗、昂扬向上的气质,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也是时代的赠予。
没戏唱了,当了派出所所长
相比今日的低调时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吕瑞英风光无限:一代越剧流派的缔造者,舞台上的中流砥柱,拥有无数狂热观众和追随者的明星演员。然而,时代和命运给予她们的,不仅是在大好艺术年华的拦腰一剑,更有很多遗憾终生的错失。在那个越剧电影创造无数奇迹的年代,吕瑞英没有能用影像留下自己的舞台艺术,成为最让人唏嘘的憾事。

1960年代初,吕瑞英赴港演出,她的两部代表作《打金枝》、《三看御妹》被香港影星夏梦看中,当时的中央领导为了支持香港进步电影厂,亲自拍板,决定免费并永久性地出让这两部戏电影的拍摄版权。吕瑞英从此无缘把自己“亲生”的这两部代表作搬上银幕。

几年后,吕瑞英主演的两部越剧电影《天山雪莲》和《西厢记》筹拍。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就只《西厢记》等着另一位主演尹桂芳的档期。可就在这等待的一个月间,“文革”爆发了。时隔近40年,别人眼中的遗恨,吕瑞英却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调侃带过:“当时真是大姐没等来,倒等来了"文革"呵。”
电影没拍成,戏也唱不成了。“文革”期间,吕瑞英随在军队任职的丈夫举家迁往广东。在雷州半岛当上了机场派出所的所长。对于一个从小到大练着兰花指长大的越剧演员来说,这真是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岗位。但吕瑞英却兴致盎然地干了起来:“当时我们有专门的指导员和老领导带着我干,小到偷鸡摸狗,大到敌特案件,我都管。
”说起这些,吕瑞英脸上竟泛起得意的神情,禁不住哈哈笑道:“现在让我去查个小偷、办个小案子,我还是可以查出点线索的。”
离开了拥有鲜花和掌声的舞台,吕瑞英并没有像很多演员那样落寞沉沦,她选择有滋有味地生活着,即使在“靠边站”的日子,生平第一次剖带鱼让她手忙脚乱,她也觉得新鲜有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吕瑞英说自己并没有太多遗憾,“我的性格就是面对现实。”或许,正因为骨子里藏着通透和豁达,逆境也好,坦途也罢,她都宠辱不惊地过来了。
大家叫我“吕大”
“我觉得我的院长没有做好。”说起自己仅仅只有四年的院长生涯,吕瑞英很斩钉截铁地下了定论。当年在上海名噪一时的越友酒家,曾经引起议论纷纷的上海越剧院冠名事件,都让吕瑞英一度陷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吕瑞英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也多了一份沉静的思考:“我觉得我的性格还是太好胜了,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如果当时能够柔和点的话,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面壁思过,觉得还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吕瑞英是上海越剧院的第二任院长。1980年代中叶,当第一任院长袁雪芬即将卸任之际,为了寻觅至关重要的继任人选,上级领导部门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意调查。最后,本不在备选之列的吕瑞英却成为得票最多的人选。当时,吕瑞英正投身男女合演,接连创作了《十一郎》、《桃李梅》、《凄凉辽宫月》、《花中君子》等多部新戏,并提携了日后成为“越剧王子”的赵志刚在内的一批男演员。
在剧院里,她的人缘颇佳,大家都喜欢昵称她为“吕大”。
然而,众望所归走马上任的“吕大”才干了半年多,就发现每个月都要举债度日。“那时候也就是短缺几万块钱周转,于是每月6日发工资,上个月的十几日我们就要去问别的剧团或者银行借钱。”就在这样的处境下,一个机会却突然来了。“有一天剧院舞美队的人来和我说,梅龙镇酒家即将装修,很想借个场地暂时经营半年。”
吕瑞英马上想到了汾阳路上越剧院的排练厅,曾经是白先勇旧居的一栋花园洋房。她当机立断地决定把场地提供给梅龙镇,两家合作经营,越剧院收取70%的营业收入。
但凡有点年纪的人几乎都知道,“越友酒家”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滩最有名的酒家之一。即使现在算起账本,吕瑞英依然一清二楚。“当时,我们剧院一个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是1.6万元,但越友酒家在短短半年里,就起码给越剧院带来了6万元收入,院里的工资不用再借,我们也解决了很多离开演出岗位的职工工作。
后来梅龙镇装修好,我们就继续独立经营,最多的一年,有百把万元的收入。”尽管,“越友”的收益有目共睹,但“新院长不专心搞艺术,却去搞三产”的做法,依然让一些人不甚理解。
发工资的钱有了,但是投入艺术创作的资金还是严重不足,虽然各种异议不绝于耳,吕瑞英却不为所动,继续着她搞创收的热情。一则“广州白云制药厂养活一个足球队”的广播新闻触动了她的神经:“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企业可以养活足球队,为什么就不能养活我们一个剧团?”吕瑞英很快找到了当时的上海家用化学品厂,提出越剧院为对方“露美”品牌化妆品提供广告服务,厂方当即为院方提供一年40万元的赞助。
这件“上海文化赞助第一案”差点因为种种原因而中途夭折,最终在吕瑞英不折不挠的坚持下,上海越剧院与“露美”签署了冠名协议,把一团、三团更名为上海越剧院“露美一团”、“露美三团”。
在吕瑞英任内,还诞生了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引进了罗怀臻、郭小男、李莉等一批日后成为一线编导的青年创作人才。
吕瑞英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改革家”,她搞创新的驱动力其实很简单,“我真的是因为想要搞艺术,才想要先搞钞票。”捉襟见肘的日子让一个剧院无暇顾及创作,这在今天看来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在当年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苦衷。而20年前那些备受争议的创举,在今天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吕瑞英的院长生涯很快就戛然而止,甚至提早办理了退休手续。她提早离开的原因,只是因为她走的路,确实比别人超前了一点。
哪怕我的吕派断子绝孙,我也绝不后悔
吕瑞英的特立独行远不止在她院长的任内,在艺术上,她始终有不同寻常的想法。采访的时候,吕瑞英突然冒出了一句举座皆惊的话:“现在有很多人唱吕派,但请不要叫她们吕派弟子,我不收学生,所以最多只能叫她们吕派爱好者。
”看着大家瞠目结舌,她解释说:“我一直觉得所谓老师,责任重大。这些中青年演员,我没有花过许多心思教过他们,"老师"这个词我真的担当不起。我和她们的交流实在很少,所以一直很有歉意,这次搞专场也是想弥补一下。”
事实上,为了动员吕瑞英搞专场,身边的人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她坚持专场要对剧种有建设性,除了与学习吕派的演员有一些艺术切磋,也要留下一些折子戏。因此,她亲自出马,挑选了合适的剧目和合适的演员,整天和那些“吕派爱好者”泡在排练厅,指导她们,“挑剔”她们。
吕瑞英戏路宽广,表演自然贴切,人称“千面人”。吕派的声腔更以“一戏一腔”著称,作曲家何占豪称她是“创作型演员”:“她不刻意塑造流派特色,而是从人物出发,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这种创作精神与西方的歌剧是不谋而合的。
”由于吕派唱腔始终处于变化中,没有特别的规律可循,因此越剧界素有“吕瑞英好听不好学”之说,很多人劝她多使用一些标志性唱腔,让人好认、好记、好学。吕瑞英却不以为然,她更执著于塑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戏曲的唱腔就是人物的情绪表达,每个人说话方式不一样,唱出来怎么可能一样?我不愿意为了追求流派特色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哪怕因此让这个流派断子绝孙,我也绝不后悔。”
不求流派闻达的吕瑞英自然不会有门户之见,她一直主张学吕派的青年演员更多地领会她的创作精神和艺术追求,而非单纯的模仿,她甚至鼓励她们同时学习其他流派。“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学、什么都看,虽然我不收徒弟,但青年演员在艺术上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只要我能解答的、能帮助的,我总归尽量地解答、帮助。”在她的支持下,上越的小一辈吕派花旦都能演些其他流派的戏。
然而,吕瑞英并没想到,吕派如今是学习者最多的越剧旦角流派之一。她独具个性的艺术追求和人格魅力,赢得了众多年轻的追随者。越剧界新一代的领军人物茅威涛就是她的仰慕者。“我实在很欣赏吕老师的表演,亦感激她对我改革创新的鼎力支持。
”茅威涛说,她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和吕老师一起合演一次《花中君子》,“当年,我看老师演《花中君子》,她在台上如泣如诉,我在台下哭湿了一块又一块纸巾。”时隔多年,茅威涛终于得到机会和吕瑞英在排练场“搭档”了一次,“那天吕老师为永梅示范"传书",和我对了几段戏,我霎时就被她倾倒了。”
◎ 心事
越剧需要一个接班团队
生活中的吕瑞英并没有艺术上和工作中那样多的坚持,更多是随和亲切。尽管已经76岁了,可大家最喜欢形容她的一个词依然是“可爱”。和她搭档多年的陈少春说,吕瑞英舞台上的甜美来自于内心。而年轻人则喜欢亲切地称她“瑞英老师”,说起她的“可爱事迹”更是不胜枚举:“排练结束后,她会和我们一起打80分。
”“有一次排练间隙,有一个同学和瑞英老师不知怎么讨论起身高来,她硬说她长得高,于是就当场脱鞋测身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虽然不再频繁地过问剧院事务,但吕瑞英始终在关注着越剧的发展,忧心从不曾少:“我以前也觉得年轻演员不用心,但现在开始渐渐理解她们。现在的氛围和过去不一样,年轻演员很苦闷。现在演个戏还要靠演员自己去拉资金,这实在不是办法,简直就是拿着金饭碗在讨饭。很多人说现在戏的质量在走下坡路,可是,如果没有生活保障,戏的质量怎么可能有保障?”
而最让吕瑞英揪心的还是越剧的接班队伍:“我一直觉得以前上海青话的模式是真正造就演员的模式,大家是一个团队,主角配角大家轮着演,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共同成长,既有个人风格,又有综合实力。而现在,我们的年轻演员却被打散分到各团,没有作为一个团队来进行整体培养,接班人的培养不应该是单独的、个体的。
”吕瑞英说罢长叹一声:“其实现在每个剧团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对传统的继承,不应该只局限于剧目和艺术,也应该体现在对于人才的培养上。我曾经是一个受惠者,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受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