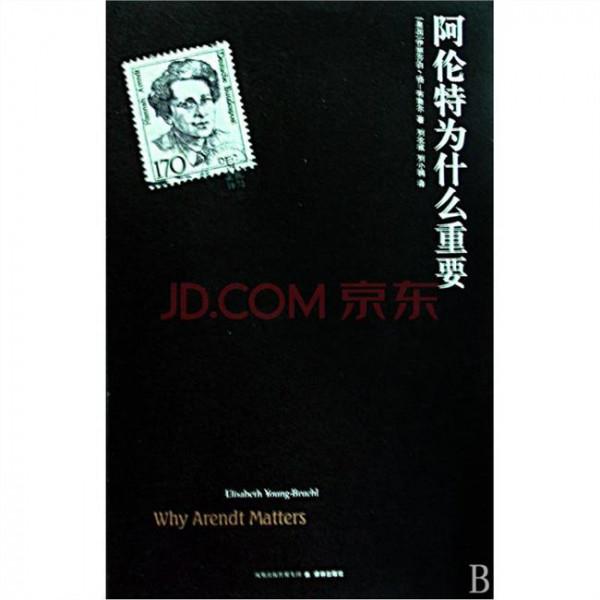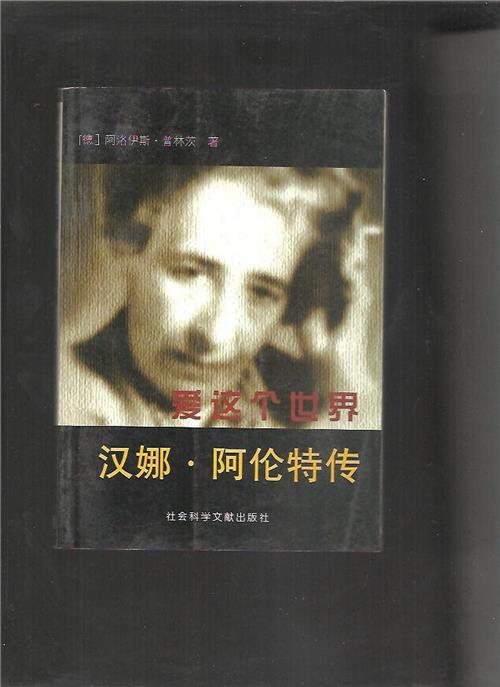阿伦特劳尔 哲学与政治:阿伦特与施特劳斯的隐匿对话
【作者简介】郑维伟,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 苏格拉底之死彰显出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如何在政治共同体中为哲学生活的正当性辩护成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施特劳斯认为,大众与精英的区分出于自然,不可变更。为免除专制政体下的各种迫害,哲学家必须以俗白教诲方式迎合大众,真理则只能以隐微教诲形式传播给少数哲学精英,这构成了施特劳斯独特的“读写政治学”。
阿伦特认为,以读写政治学来化解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是不充分的。大众意见并非天然敌对真理,其中蕴含着真理的因素,大众也并不天然仇视哲学家。
事实真理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现代世界对事实真理与政治生活的真正威胁来自有组织谎言与国家形象制造。他们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最终在实践上是为了迂回地批评海德格尔参与纳粹。
在施特劳斯看来,海德格尔把本该在哲学精英之间秘传的真理兜售给纳粹当局,一定会失败。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混淆了隐藏在私人领域的哲学思考和公共领域中的实践智慧,最终失败实属必然。阿伦特与施特劳斯的隐匿对话,不仅尝试回答哲学与政治的基本关系问题,也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
【关 键 词】读写政治学/公私领域/事实真理/有组织谎言
伟大的思想家不仅有伟大的著作传世,还会深刻地影响卓越的思想家。无疑,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即如是。卡尔·洛维特(Karl Lwith)、汉斯·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等20世纪卓越的思想者,在成长中都曾受惠于海德格尔。阿伦特在海德格尔80寿辰时写道:“海德格尔的思,这种思决定性地规定了本世纪的精神面貌。这种思的深度和强度有一种只有海德格尔本人才能承受的钻研着的负重。”①施特劳斯承认“我们时代唯一的大思想家是海德格尔”,②“尽管韦伯(Max Weber)当时被我视为科学与学术的精神之化身,若与海德格尔相比,韦伯只不过是一名孤儿。”③
思想家生活在世界中,而重大的事件常常会使其思与行赤裸裸地摆在自己的学生、朋友及同胞面前,接受他们的审视、怀疑与批判。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不清不白,使许多学生与朋友敬而远之。就生活和思想经历言,几乎没有比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更相像的了,他们都是生长在德国的犹太人,因纳粹兴起而被驱逐,流落巴黎,最后定居美国,甚至在同一所大学任教。不过,他们在各自著作中几乎从未提起对方,这也颇令人惊奇。④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却时时感受得到两人之间的无声对话。
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背景,使他们对海德格尔短暂的政治参与做了迂回而深刻的分析。海德格尔与纳粹是柏拉图与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关系的现代翻版,还是其思想的逻辑展开?哲学与政治是不可调和的吗?哲学家作为思想王国的成员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必然产生冲突吗?如果是,又如何化解呢?这构成哲学史上独特的海德格尔论辩(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诸多学人驻足于斯,沉吟于是。⑤而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的反思,开启了深入思考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思想道路,刻下醒目的路标。⑥
一、苏格拉底之死与政治哲学的起源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Socrates)的基本教诲。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而毕生在追求知识。知识不同于意见,知识是对整体的把握和确证,意见仅是知识在众人面前显现出来的假象。惟追求知识者,才配享幸福。尽管他承认自己未必掌握知识,但说其配享德福生活则大致不谬。然而,雅典城邦却判处其死刑。是城邦过于邪恶、法官愚钝和民众无知,还是苏格拉底确实触犯了城邦禁忌而引来杀身之祸?
苏格拉底被控以两项罪名:亵渎城邦的神并引入新神,及毒害青年。对前者,苏格拉底解释说,为遵从德尔菲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他却自认为无知,而神又不会说谎,那必定有比其更有智慧的人。于是,他遍访城邦中的政客、诗人、工匠,结果发现虽然他们自认为、人们通常也认为其很有智慧,其实他们很无知。苏格拉底之所以有智慧,正是因为他自知无知。然而,苏格拉底因遵从神谕而得罪了那些无知的人们,他们出于愤怒、偏见和忌妒而意欲杀死他,“要是给我定罪的话,这是定罪的原因;原因并不是梅雷多,也不是安虞多,而是众人的偏见和妒忌(黑体为笔者所加)。”⑦至于毒害青年的指控,他指出:如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苏格拉底果真毒害青年,那么这些青年及其家长断不会支持苏格拉底了。
面对指控,苏格拉底适度申辩,他相信“讲理是审判官的美德,以实道实是说话人的本分”。他说:“雅典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口气,还能动弹,我决不会放弃哲学,决不停止对你们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黑体为笔者所加),以我惯常的方式说:‘高贵的公民啊,你是雅典的公民,这里是最伟大的城邦,最以智慧和力量闻名,如果你关心获取钱财,只斤斤于名声和尊荣,既不关心,也不想到智慧、真理和自己的灵魂,你不感到羞耻吗?’”⑧换言之,苏格拉底为自己的生死辩护,实质上就是为哲学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存亡辩护。
然而,城邦公民还是判处了他死刑,言语的力量失效,哲学生活岌岌可危。苏格拉底没有放弃作为哲学家的尊严,向法官求情开恩,也没有厚颜无耻投其所好地讲法官们爱听的话,“你们喜欢听我哭哭啼啼,说和做一些我认为不配我去干的事情……我并不认为我在危险之中应当去做那不配自由人做的事,现在也不懊悔自己作了那样一个申辩,倒是宁愿作了那种申辩而死,不愿作出另一种申辩而生。
”⑨
哲学家不停地质疑大众的意见,期望将他们带到真理和幸福之路。可是,大众并不买账,为捍卫意见世界,他们果断地处死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大众指控苏格拉底引入新神,不是没有道理的。城邦的神是意见,苏格拉底引入的神是真理,很多意见是经不起刨根究底式的追问的。
要维护城邦生活,必须保持意见世界的相对稳定,为此必须杀死真理,杀死讲述真理的哲人。苏格拉底的命运在他探究真理并向大众讲述时,就已注定。毒害青年的指控也与此相关,青年作为新生力量负有更新城邦并使之持续下去的重任,为此必须对青年进行政治社会化,使之接受城邦意见和习俗。
跟随苏格拉底探询真理,或许有利于个人幸福,却不利于城邦安危,颠覆性地探究和质疑会挖空城邦的根基。
毒害青年与引入新神,本质相同。因此,苏格拉底之死道出了以追求真理为事业的哲学家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基本处境,也成为政治哲学思考的起点。哲人如何在城邦中过活,如何从政治上为哲学生活辩护,便成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